孙大雨出狱 严祖佑:教授风骨——狱友孙大雨
作者严祖佑,生於1943年,1961年考入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1964年9月26日因“反革命集团”案被捕,同年秋曾在上海师范学院和上海邮电俱乐部二处,公开举办该“集团”的“罪行”展览会。1966年被处劳动教养,1972年被判处期徒刑十五年,1980年获平反。曾做过营业员、中学教师、报社记者。2003年退休。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主任记者。
(一九七零年三月,我在安徽军天湖农场被重新逮捕,住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关押在八号楼。八号楼又称病号楼——在上海市监狱的编制序列中,称为八中队。其中关押的的犯人,大都是狱内其他中队送来治疗的慢性病患者,以及从监狱医院出院后还需继续治疗者。四月中旬起,我被编入“未决组”——组内大都是原关押在市内各看守所尚未判决的罪犯。这些人患病后,当时也由监狱医院负责治疗。)
明天就是“五·一”劳动节。
狱中,一年有四大节:“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即农历过年)。如果在劳改营,再加上一个中秋。对囚犯而言,过节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开荤,吃肉。犯人们把猪肉称作“老表”,其确切意义不明,总之是十分亲切的意思。
那些在监狱中住了一、二十年的老犯人,有一句顺口溜:“吃官司有三盼:理发,洗澡,吃老表。”不过,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话。那时,每个月还允许家属给狱中囚犯送一定量的食物,狱中食品尚不算十分匮乏。到了“文革”期间,为彻底清除囚犯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狱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严禁送入任何食品。于是,理发洗澡之类与口腹无关之事,便远远地退到后面。“吃老表”,自然成了犯人朝思幕想的至盼。
下午二时,掌握犯阿维在监房对面的窗口前说了声:“大家出来活动活动”。于是,每一扇铁门中懒洋洋走出了三个人,在本小组范围的走廊内,缓慢地兜起圈子。
狱中,犯人小组长的官称是“掌握犯”,这是因为犯人都属于“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理所当然不能享受带“长”字的称呼。于是就起了这么个不伦不类的名称。同时,每层楼还有一至二名“事务犯”——大组长,整幢楼还有数名“总事务犯”。
窗外,阳光明媚。这一排监室是朝北的,因此,到了下午,就会有一抹西斜的阳光射进来,照在每一个走到窗前的囚犯的脸上,那一缕缕皱纹,就更加明显地凸现出来,原来因少见阳光的灰白的面孔,又增添了一层缺血的淡黄色。
每个人走过窗前,都会情不自禁地转过头,深深呼吸几下。广阔蓝天下的空气,真是太好闻了。特别是在过节之前。记得前几年,关在看守所的时候,每到过节前几天,往往可以听到院子里杀猪时,猪的叫声。尽管那叫声异常凄厉,但进入犯人的耳朵,却觉得特别舒服。监狱内听不到这诱人的声音,但在空气中,仍然似乎可以闻到若有若无的肉香。这样,兜圈子的人的心情,仿佛也变得好了起来。
脚下,走了一圈又一圈。纷繁的思绪,刺得我的头越来越痛。
走廊尽头,传来一阵尖锐的哨子声,一个沙哑的声音在喊:“开水来了!”
很快,随着沓沓脚步声,一列劳役鱼贯而入。两人一档,一前一后,抬着一个大水桶,每隔几间监室放下一个。
开水,在监狱内是被叫做“无米稀饭”的。许多人都端起缸子,大口大口喝了起来。我则用它的热度,治疗我在农场落下的风湿痛。我很快脱下上衣,把滚烫的水缸烙在赤裸的背上。火热的灼痛感,迅速在我背部的皮肤和肌肉上传递开来,同样伴随着一种刺骨的快感。
这时,阿维来到我们口,他看了一眼趴在地上的我,皱着眉嘘了一口气。
阿维今年二十五岁,也是反革命犯,被判了七年刑。细长个子,瓜子脸,一说话就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有一种少女的媚态。据说,两年前他刚入狱不久,就曾揭发过一起狱内著名的“反革命集团”案,立了大功。因此这一年多来,他都痴痴地等待着每一个节日,期盼狱中在节日前后召开的“宽严大会”,向往着能得到减刑的宽大待遇。
自从我来到这个组,阿维对我还不错,即使在其他犯人必须关在小监室的时候,我也可以和他一起,在本组七个监室门口的走廊之间跑来跑去。
这时,劳役犯商周匆匆走来,用略带神秘的口吻对阿维说:“孙大雨来了。”
“是吗,他来了就热闹了。”阿维也顿时兴奋起来。
岁月流逝,今天的人们,对孙大雨这个名字,也许已经相当陌生了。但在上世纪中叶,凡是读过一点书,经常看看报纸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孙大雨的。他的出名,不仅因为他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教授。更因为在“反右”运动中,他又是中国右派分子中,特别负有盛名的一位。
在这场被称作“引蛇出洞”的运动中,孙大雨是唯一由最高领导御笔亲点,逮捕法办的右派分子。只要翻翻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就可以发现,在该卷所有指名道姓的右派分子中,孙大雨是被点名最多的一个。可见当时的最高领袖对他的注意程度。
孙大雨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院。三十年代初归国,历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教授。他在三十年代,加入梁实秋、徐志摩等人倡导的文学团体“新月社”。出过诗集,又致力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和翻译。对于他的学术成就,当时圈内人士曾有评价,说是中国一共只有一个半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算是一个,其他加起来只能算半个。
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孙大雨远赴陪都重庆,一面教书,一面从事抗日。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和国民党当局政见不合,他和新月社旧友闻一多等人,一起参与倡办了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代后期,又担任了左派的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魏特曼将军来中国调处国共两党纷争,孙大雨以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主席身份递交声明。力言国民党已丧失中国民心,希望美国政府不要再给予支持。然而,一九五零年初,上海大学教授联合会在当局指示下改组,孙大雨被免去了主席职务,在五十年代的“民主改革运动”中,孙大雨更成了被批判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和所谓“旧社会”过来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同,这些年来,孙大雨不仅没有通过不间断的“自我批判”,求得“新社会”的容纳。他对于强加给自己的“批判”,始终是不服,甚至对抗的。别人指责他“反动”,他就骂别人是“反革命”。五十年代前期,他曾到处对人说,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是“反革命”,几乎酿成大祸。巧的是潘汉年后来居然真的成了”反革命”,孙大雨就逢人便说自己有先见之明。
一九五七年鸣放的时候,在一次会议上孙大雨又说,当年曾批判过他的史良、陈望道、苏步青、杨西光、陈其五等几位是“反革命”。结果是过了一段日子,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孙大雨如此谈整风”。接下来“反右”开始,全国报刊“批判右派分子孙大雨”的文章铺天盖地。
在最高当局授意下,那几位被他骂作“反革命”的先生,联名向法院控告孙大雨“诬告”,孙大雨就此被判了六年徒刑。六十年代,他刑满释放,蛰居上海市南市区昼锦路旧宅。“文革”中,在劫难逃,在遭受红卫兵批斗时,不堪凌辱,奋起以老拳还击,又被抓了起来。
监狱里的日子太无聊了。因此听到有这么一位名流加入自己的小组,就象在乏味的生活中添加了一些调味品,好几名囚犯都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兴奋。
隔壁房间的应某,听到孙大雨的名字,马上伸过头来问,是孙大雨么,让他同我一个房间好了,我来监督他。他生的病和我一样,都是肺结核。我和他在医院,还有一面之缘呢。
应某原是市工业局一名科长。“文革”刚开始,他就拉起了一个“造反队”,和另一个“造反队”争权。结果他的“造反队”被砸烂了,又查出他和一名女同事有过婚外情,就被按上“反革命腐化”的罪名,抓进了看守所。到八号监后,他同“反改造分子”斗争是最积极的。数年后,他被判刑七年,在专事接收新判决入狱罪犯的提篮桥监狱六号楼,当上了显赫一时的“黑板报组”掌握犯,我曾目睹他的风采。
听到孙大雨三个字,有一股血往我脑门上冲。
十天前,曾和我同室,现已病愈返回看守所的叶某对我说起,孙大雨在上海第一看守所和他同室。同室的还有一位江苏海门人,二十八、九岁,姓张,是孙大雨朋友的儿子。此人把自己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孙大雨,孙大雨却向看守警员告发了张某,致使张某被铐上了反铐,足足有半个月之久。
我从种种迹象断定,张某就是我的朋友和同案张方晦,自从我知道我们的案子已经被列入上海市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管会下发的,供全市范围讨论的要案案例中后,案中名列首位的方晦,在我心目中就已经成了“故人”了。而为人父执的孙大雨,竟然在方晦可能“不久人世”之际,还使他受到上铐的痛苦,不由我想起来就深痛恶绝。
仅仅过了几分钟,孙大雨就由事务犯陪同,来到我们的小组。孙大雨人如其名,身高马大,头大、手大、脚大。但由于长年关押,瘦得脱了形,这“大”就变成了“长”。一米八十以上的身子弯弯曲曲,像一株枯干的老树。细长的手臂,细长的腿,青筋盘结,像树身上伸出的枝丫交错的树枝。
硕长的马脸,长鼻子,长牙大嘴。他上身穿一件棉袄,下身只穿一条短村裤,晃动着两条光光的小腿,手里捧着一只脸盆,摇摇摆摆地走了进来。看到他这副滑稽的样子,好几个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进了小监室,应某就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吻,冷笑着说,孙大雨,你堂堂的大学教授,怎么弄成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天还这么凉,光着两条腿,是不是想病上加病,给政府添麻烦呀?
孙大雨连连摇头,决无此事,决无此事,实在是因为棉裤洗掉了。
原来,他一个月前在看守所发病吐血。看守警将他送到医院急诊。当时正是春天,他怕冷,还穿着棉袄棉裤,里面就一套衬衣,当天便住了院。他几次请求,将留在看守所的替换衣物送来,都无人理会。他年老体弱,小便时常有残留的尿液遗在裤裆里,一个月下来,浑身发臭。今天上午,狱中护士小姐查房时,被熏得受不住,就强令他把外裤脱下来洗掉。刚刚浸湿就通知出院了。
劳役商周来登记饭账了。他走到监时门口,叫了声:孙大雨!
孙大雨正低头理东西,听叫,猛地直跳了起来,毕挺立正站好,手一松,短裤刷地掉在地上——他的裤带早在看守所就被收去了(防止自杀),只能用手拎着——晃悠着赤裸的下身,松松垮垮地吊了下来。他瞪大眼睛,惊恐地朝商周望着。
商周一吓,连连朝后退着,喂喂,你不要这样,我也是犯人,担当不起的。
我的罪重,我的罪重。孙大雨一面拎裤子,一面连声说。
商周问,你晚饭吃多少?
孙大雨呆了呆,喜出望外地:怎么,这里吃饭,是由着自己要吃多少就多少?
商周又气又好笑:老头子,想得美。
他告诉孙大雨,狱内犯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早餐二市两稀饭(一百克),午餐晚餐各三市两干饭。有病吃不下,减少是可以的,想加是不可能的。
“那当然是三两”孙大雨回答得很快。
开饭了。我刚吃了几口,阿维过来朝我眨眨眼:“去看孙大雨吃饭。”
孙大雨手捧着铁皮饭格,坐在监室门口。陈米饭的上面,照例盖了一层无油的鸡毛菜,在饭格的一角,有四、五粒蚕豆大小的鸡骨头。鸡骨头是红烧的,鸡骨头附近,有几块菜皮上还沾了一些绛色的油花。孙大雨心满意足地望着这几块鸡骨头。
这几块鸡骨头是“营养餐”,孙大雨患的是肺结核,按规定可以享受一份营养餐。那时,狱中营养餐的规格,是每天中午可享受一份加餐,价值为人民币五分(当时物价,五百克猪肉大约人民币八角)。
孙大雨吃饭的姿势很奇特。他每吃一口饭,都要把头仰得很高,闭上眼,然后不停地咀嚼。他用力地嚼着,尽量把饭菜停留在嘴里,不咽下去,仿佛要把所有的滋味都嚼出来。他一口连着一口,最后轮到那几块鸡骨头了。孙大雨把其中一块放进嘴里,右下颚一阵剧烈的抖动,连带后颚也飞快地颤动起来,随着咯咯的声音,连骨头带肉都被咬得粉碎,咽到肚子里去了。
阿维看得呆了:“真有你的。这么硬的骨头,居然都嚼碎吃下去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
孙大雨笑得比哭还难看:“我牙齿好。六十四岁了,一只牙齿都还没有掉。上个星期,医院里吃咸鸭蛋,我也是这么连壳带蛋一起嚼碎了,吃下去的。这都是钙质,补的。”
吃完鸡骨头,孙大雨一次又一次用开水冲刷着饭格,然后一滴不漏都喝了下去。应某翻起了白眼:“孙大雨,你这是什么意思。刚吃完饭,把这么多冷开水吃到肚里,你要找病呀。”
孙大雨指指饭格:“饭,里面还有饭。”
应某一把抢过他的饭格:“已经精光滴滑,好当镜子照了,还有屁的剩饭。”
孙大雨喃喃地:“总还有一点饭的分子吧。”
晚饭后,应某和孙大雨一直叽哩咕噜地吵着。
孙大雨想把湿棉裤晾在铁门的栏杆上。应某不准,说有规定,铁门上只准挂毛巾,其他一律不准放。孙大雨人瘦,坐在光地板上屁股痛。他身无长物,打算拿刚才狱方借给他的,那条臭烘烘的破被子垫在身下。应某也不准,说是政府借给晚上睡觉盖的,不是当座垫的,如此不爱护公物,可见思想反动。……
按监狱惯例,五月一、二、三这三天,为了确保“安全过节”,除了事务犯、劳役犯、掌握犯以外,其余囚犯的房间一律不开,停止一切活动。二十四小时关在小监室内闭门思过。
阿维传达狱警指示,节日期间,每个人都要结合“大好形势”,联系自己的“犯罪危害性”,至少写一篇思想汇报,节后统一上交。
五月四日,吃过早饭后,事务犯通知,全楼面放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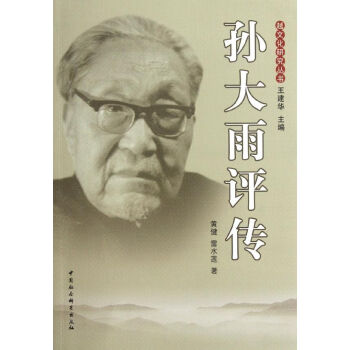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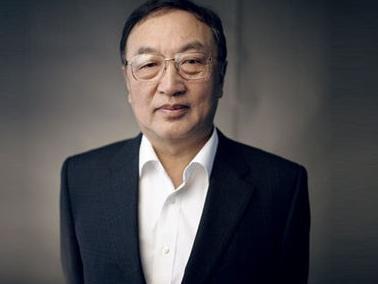




![>武汉大学孙来斌 孙来斌[武汉大学珞珈特聘教授]](https://pic.bilezu.com/upload/1/a4/1a433a5b595881d71d509c3fd7ebb69a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