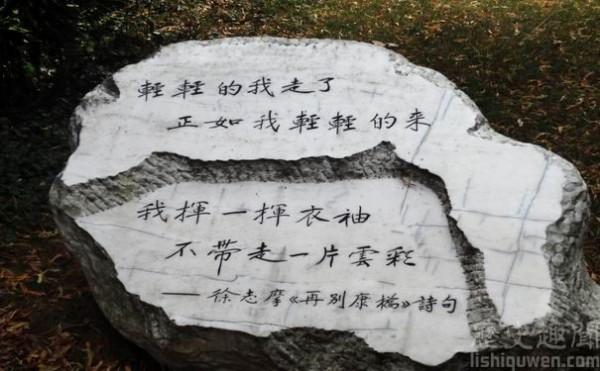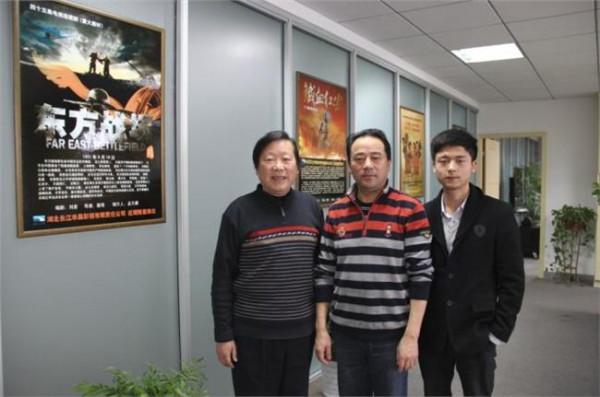徐晓作家 吕家乡:徐晓诗歌的艺术得失
最近我读了90后的校园女诗人徐晓的诗集《局外人》(卓尔书店,2014),感到欣喜,也有些不满足和更高期待。艺术面前人人平等。在文学艺术天地里,老中青少,士农工商,都要接受同等的鉴赏和评判,不可能厚此薄彼,严甲宽乙。限于精力,我这里仅对很少几首诗坦率地谈点感觉。
先看《大雪之夜》:"大雪封山,夜晚守口如瓶/ 我是否该烫一壶好酒/ 等你。在江湖之远/ 一定要醉 免得说离别// 半个月亮爬上来. 微亮/ 接近入世的灯盏/ 你卸甲归来/ 把喜悦盛在掌心// 我们无需把沉默唤醒/ 一言不发, 在内心留下一块空地/ 悄悄把来路隐藏// 这世界 只剩下我们的山河"
这是归来者"你"和等候者"我"二人的一段生活场景。从"江湖之远"的措辞,可见两人是在江湖拼搏的伴侣。大雪封山之夜,到处寂静无声,等候者却有"我是否该烫一壶好酒等你"的想法,可见他们是有约定、或有惯例的,照例今夜应该回来相聚,只是今夜大雪封山,情况特殊,所以"我"有些犹豫。
到了"半个月亮爬上来"的下半夜,果然"你"如约回来了。"卸甲"二字富有暗示性,可见"你"是一个江湖上勇武的打拼者。虽然经过"大雪封山"的艰苦跋涉,却不显得疲惫,而是在握手时感到"把喜悦盛在掌心"。
不同寻常的是,两个知己欢聚,而且尽兴痛饮,却保持着一贯的"沉默"习惯,彼此"一言不发" 。为什么呢?为的是"在内心留下一块空地/ 悄悄把来路隐藏"。
就是说,彼此的来路(经历)一直是相互隐藏,互不了解也不求了解的。如此亲密的知己,却如此相对沉默,又如此相互"把来路隐藏"。那么,相互的信任是怎样建立的呢?相互的情谊是怎样持续的呢?彼此的肺腑是怎样交流的呢?(仅仅靠"把喜悦盛在掌心"的握手吗?)哪里有这样的"心照不宣"呢?难道是害怕隔墙有耳吗?读者期待着结语能够解答。
结语是"这世界,只剩下我们的山河"。这就是说,一方面,除了大自然的山河,我们在世界上已一无所有;另一方面,觉得我们毕竟还有"我们的山河"。这结语固然可以让读者了解诗中主人公"我们"生存状态的艰困,及其精神状态的旷达和清醒,但并不能解答上述的阅读困惑。
这首诗让我们联想到"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但诗中的情境不同,这里没有犬吠,而是"夜晚守口如瓶";让我们联想到"相见时难别亦难",但诗中表现的情绪不同,这里是相见时流露的"喜悦",和毫不缠绵的对于离情别绪的控制和预防:"一定要醉,免得说离别";让我们联想到"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但这诗里呈现的却是迥不相同的另一种知己团聚的场面:相互"一言不发"。
这首诗歌的确富有原创性。可惜这种原创性的抒写并没有构成对应某种人生境遇的诗歌境界,因而不能产生陌生又亲切的耐人品味的魅力,倒是让人越琢磨越觉得费解。
就细节来说,"一壶好酒"而不是"一壶老酒",显得生活富裕,似乎不利于表现江湖打拼的艰苦。"把喜悦盛在掌心",相见仅仅握手,这似乎减少了彼此关系的亲密程度;即使两人不是夫妻,这样来之不易的欢聚也是会更加激动的。
再看《以白云为枕》:"一个垂暮的老人,枕着白云/ 收割炊烟,把一生时间/ 用麻绳捆扎// 那轮凄迷的落日,颔首挺胸/ 在特定的日子里,归于沉寂/ 走失的羊群,还没回来/ 其实世上所有的人,都没有回来// 太黑了,月亮弯起了腰/ 那姿势,多么耀眼而孤独 "
对牧羊老人的正面描写就是前三行。这三行能不能竖起一个丰满的富有诗意的牧羊老人形象呢?我看不能。"枕着白云",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他远离人群的孤独和高洁;"收割炊烟"(我的领会是说他收割柴草,然后燃起炊烟,自炊自食),让我们体会到他的艰苦;"把一生时间 / 用麻绳捆扎",大概是说老人一生的生活内容可以概括为"用麻绳捆扎",例如用麻绳栓羊,用麻绳捆扎柴草,用麻绳捆扎在腰间,所有的财物都用麻绳捆扎起来(连个箱子也没有),等等,这细节强调的是老人整个"一生"生活的单调、贫困、勤劳。
诗中看不到老人和家人的关系,和村人的关系,和羊群、和山川草木的交流,更看不到他漫长的一生中时代变迁对他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的影响……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写老人去世的情景,这些抒写都要以第一节对老人形象的抒写为基础。
由于第一节没能够竖起老人丰满可感的生动形象,下面的渲染就失去了依托。"那轮凄迷的落日……归于沉寂",既是老人去世的衬托,也是老人去世的写照。
老人去世的时候,他所倾注心血、放牧照看的羊群竟无动于衷,世上所有的人也都各自奔忙,无动于衷。真是"太黑了"(太冷漠无情了),只有月亮向逝世的老人弯腰致敬,"那姿势,多么耀眼而孤独",可见月亮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感召力,即使星星也没有效法。
老人不仅在社会生活中是局外人,似乎在宇宙中也没有多少亲切的伙伴。不知诗人的这种体会能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反正我自己很难受到触动。
我觉得这种冷酷的环境渲染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是硬性强加的。一贯温顺善良的羊群怎么会对牧羊老人的去世无动于衷呢?老人放牧的羊群是分属于一个个户主的,这些户主怎么会全都对牧羊老人的去世无动于衷呢?即便只为了自己的几只羊今后的放牧问题也不会无动于衷吧?
最后再看看《局外人》:"石头的一生都在与石头打交道/ 石头姓石 石头住在石头村/ 石头出生在由石头垒成的小屋里/ 石头长在由石头堆成的小山上// 石头来到城里搬运一袋袋石头/ 沉重的石头压在石头的肩上压弯了石头的腰// 瞧,这些可恨的石头 不断地攫取着石头年轻的生命/ 石头躺在有石头加工而成的水泥路上/ 一根肋骨孤独地与他并排而卧// 石头村的石头那一把热忱的钥匙 却打不开石头城的心事/ 石头村里石头年迈的老母亲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 等着一个并不完整的石头 回家"
这里写的是一个农民工的悲惨命运。他名叫石头,这名字暗示了父母对他的态度:既希望他活得结实健壮,又不把他看得多么珍贵,不过视同石头。如果说他自幼生长所在的石头屋、石头村突出的是穷困和贫乏,那么他后来进入的石头城突出的则是冷漠和残酷。
"石头来到城里搬运一袋袋石头"帮助城市建设,不但没能摆脱贫困,养家糊口,反而不久竟重伤致残,不得不回到石头村,由年迈的老母亲来照顾他。诗人对石头悲惨命运的抒写的确是真实的,是能够打动读者的;但是仅仅写出这样的轮廓并没有超出一则简单报道的内容,读者期待读到诗人独特的体会和发现。
为此当然重视这样的诗句:"石头村的石头那一把热忱的钥匙 却打不开石头城的心事",这是诗人对石头悲剧命运成因的体会。
就是说,来自石头村的石头自幼生活在闭塞的山村,缺乏对城市的了解,缺乏城市生活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眼界情趣,虽然他来到城市,参与建设城市,却和城市相互隔膜,他是城市生活的局外人。这体会是恰切的。这种体会有待展开和深化,从而才能够使这首诗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启发性。可惜作者却浅尝辄止,让读者不能不感到遗憾。
我试图进入作者的创作心态,觉得徐晓在诗作的孕育、酝酿过程中,似乎没有处理好灵感和构思的关系。"灵感是诗的受孕"。(艾青语)简单地说,所谓灵感就是诗人受到某种东西的触动,把相关的平时胸中的积累(材料积累和思想情感积累)唤醒,不由地(不是刻意地)进入联想和想象状态,由此及彼,由浅入深,于是,落花的遭遇和林黛玉自己的遭遇融合(《葬花词》);一沟死水和死水般的社会风貌交汇(闻一多:《死水》);号兵的命运成了一切早醒者的命运的写照(艾青:《吹号者》);橡树和木棉树之间的关系成了男女情侣之间关系的象征(舒婷:《致橡树》)……诗人笔下,句句扣紧此物此事,同时又让人联想到许许多多的彼物彼事。
这样的诗歌精品当然不能没有构思的作用,但构思总是要在灵感的基础上运作,这样写成的诗才会既灵动活泼又丰满深刻,既真切自然又精巧华美。如果构思先行,甚至以构思代替灵感,就可能造成理念化,诗歌的形象体系和思想感情内涵之间就往往不那么严丝合缝。
正是由于灵感的作用(主要是不由自主的联想和想象的作用),"实情"才能够升华为"诗情","实事"才能够升华为"诗事"。徐晓的不少诗歌都属于事态结构,是写"事儿"的,都需要一个由"实事"升华为"诗事"的过程,其间既需要灵感的闪耀和照射,也需要以灵感为基础的构思的运用。
这两方面徐晓都有待加强。拿上面提到的几首诗来说,每一首诗的酝酿过程中,作者是受到了怎样的事儿触动的呢?不由地激活了平时胸中的哪一些积累呢?是不是进入了浮想联翩的内心活跃状态呢?是否达到了由此及彼、亦甲亦乙的意象生成和意象组合的境界呢?是不是存在着以理念填补生活实感积累的不足,以技巧掩盖积愫的空缺的现象呢?细细考究一番,是颇有可以加强和改进之处的。
至于《燃煤记》(刊于《西部》2016年第7期)对那个孝敬父母的少女的抒写,显然只有"一就是一""此就是此"的效果,没有多少艺术辐射力,其酝酿和创作过程中灵感和构思的欠缺,更是一目了然的了。
我是依据自己的阅读习惯和诗歌观念来评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仅供参考。可能跟徐晓的艺术追求和诗作实绩并不符合,甚至南辕北辙,那就只有抱歉了。
以上这篇评论稿是在一个研讨会期间写的。这个研讨会的主旨是提倡评论者和创作者平等、健康、友好地交流。为了贯彻研讨会的精神,我把评论稿给徐晓看了。她和我交谈了一次,又给我写来了一信。她谦逊地表示接受我的意见,关于我评说的几首诗,她也如实说明了她的创作意图。
我发现她的原意和我的理解有些是接近的,有些则颇有差异,例如《大雪之夜》这首诗,我以为写的是归来者"你"和等候者"我"二人的一段生活场景,而在她的原意中"你"和"我"并不是两个人,只是自我的分化;诗中的场景也不是生活场景,只是作者自我的内心图景。
她说:我想表达一种自我的理想化的状态,在一个大雪封山的夜晚,万籁俱寂,我等的"你"终于来了,这个"你",是那个经历了一程风雨再次回来的"我",是蜕变的"我"、成功的"我",两人相见,喜不自胜,连月亮也来助兴。
但我们并不需要多么宏大的见面仪式,仅仅是沉默就够了,因为各自知晓彼此的来路,也就不必相问这些年各自过得怎样。
因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你""我"不分,所以心照不宣是自然的,因此当我们以沉默相对时,这世界,在我们面前,只剩下了壮阔的山河,这个"山河"并不是现实世界里的山河,而是经历了在人世间的淘洗后我们所拥有的那份从容而悠然的心境。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创作意图和阅读领会之间的差异和错位呢?也许是创作者力不从心,创作意图没有圆满实现;也许是阅读和评论者不够细心,文本的意蕴没有充分领会。对此,创作者和评论者要分别自省自强。但除此之外,也有第三种可能:这种创作意图和阅读领会之间的差异和错位属于正常情况。
读者对文本的阅读不仅仅是对作者意图的追踪和复原,也是一种以读者自己的生活阅历和内心体验为基础的再创造,因此一千个读者心中就会有一千个不完全相同的哈姆雷特。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李健吾对卞之琳诗作的一些阐释使卞之琳本人也受到了教益,另有一些阐释则为卞之琳所拒,于是引起了李健吾和卞之琳之间的反复讨论。在讨论中,李健吾进一步发挥了文学批评就是"灵魂企图与灵魂接触"的观点。
后来朱自清和卞之琳之间也有类似的讨论。这是现代解诗学酝酿过程中的佳话。面对着徐晓的来信,我想到前辈的范例和佳话,进一步受到启示:创作者和评说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相互阿谀奉承或苛责对方而为自己护短,而要坚守各自的主体尊严,相互尊重,友好交流,在平心静气的切磋中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