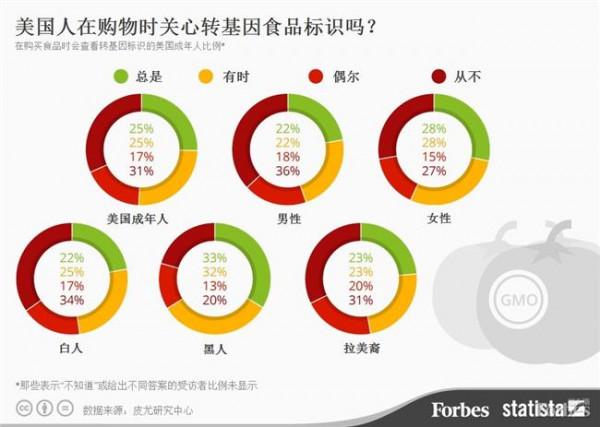张忠谋台湾工研院 台湾工研院院长李钟熙:科技台湾的瞭望者
台湾高科技产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制造的“台积电”神话,让中国大陆产、学、研各界对其母体——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简称工研院),生出无数想象,顶礼膜拜之情延续至今。 1973-2009年,工研院走过的36年,完整经历了两次全球性的石油危机、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最近的全球金融风暴。
所幸的是,在这漫长的36年中,工研院的成长见证了台湾经济从一个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经济体,向一个深刻影响和推动全球科技链条的“科技岛”的转变。
这在个蝶变过程中,工研院不仅诞生了台积电、联合电子等一堆台湾早期高科技知名企业,与此同时,它还对台湾经济的发动机——台湾中小科技企业的成长,起到了最为关键的“导航”作用。 工研院模式,对于渴望建构中国自主创新体系的大陆产业界、学界的典范意义是什么?金融风暴中,作为高科技哨兵的台湾工研院,能否像逃离前几次全球危机那样,成功抽逃?两岸合作最为关键的CEFA(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呼之欲出之际,工研院在想什么? 2009年11月6日,借着由台湾《远见》杂志社主办之“第七届全球华人领袖高峰会”的间隙,自2003年接任工研院院长之职至今的李钟熙博士接受了本报近两小时独家专访,他对科技产业如何既“华人的”、又“世界的”的理解,对非盈利研发机构如何务实地深入产业,又必须抽离现实的辩证理解,令人印象深刻。
“我是工研院NO.1的Sales” 《21世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都对台湾地区的“工研院模式”充满了好奇心和学习动力,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工研院模式?它与美国、欧洲等地的研究机构有何不同? 李钟熙:工研院的规划和战略,每个阶段都是不一样的,很难说清楚什么是工研院模式,如果拿过去讲,台湾地区过去很多的中小企业与工研院关系密切,这是工研院模式特点。
很难把我们的模式直接与美国、欧洲的研究机构比较,无论哪种模式,关键是他们能不能够经得起市场的考验,市场的考验才能证明什么是最好的模式,照别人的模式做不一定有用。
《21世纪》:工研院每年都会公布自己的财报,2008年你们收入的50%来自官方部门的专项经费,另外50%则来自于向民间和产业界输出服务,请简要介绍一下工研院的运作? 李钟熙:你其实是在问怎么经营工研院吧?我们是把官方、产业界,甚至于跨国企业都当作客户。
我们的收入,不管是做研究也好,技术转移也好,这些收入都是建立在某一些项目上;此外我们还要控制成本,收入与成本间的差距就是我们的盈余,这一点,我们和普通公司一样。
《21世纪》:这意味着你同时兼具了职业经理人和学者等多方面的角色? 李钟熙:当然!院长只是一个学者是不行的,工研院下面各所的所长也如此,我们同时也是Sales,我是工研院NO.
1的Sales。我们要去官方跟他们争取经费,同时也要去企业、学术界去行销。 《21世纪》:以中国大陆为例,通常来说,官方下达的研究经费是很难监控的,工研院来自官方的50%经费怎么获得,又怎么管理呢? 李钟熙:其实我们没有来自官方的资金。
官方也是我们的客户,资金是通过专项的研究项目的竞争申请获得,虽然是来自官方,但就像建筑公司承包官方的马路、造桥一样,我们是在招标后受他们的委托做这个项目,官方没有直接给我们一分钱。
这对我们来说比较辛苦,压力比较大。不过,这也成为我们研究机构不要和外界脱离的动力——这是优点。当然它的缺点是,官方支持的这些项目,如果自由度能够高一点,那我们可以更冒风险做一些未来性的东西。
《21世纪》:那么这部分官方项目的竞得由哪些官方部门来决定?工研院与官方的合作关系如何建立和监管? 李钟熙:我们对口的部门是台湾“经济部”,因为我们做的研究主要是为了经济,它是我们最大的客户。
科研项目立项“经济部”决定比较多一点,但是大的方向“国科会”也会参与。 《21世纪》:如果工研院要像企业一样“行销”自己,又如何保障您所强调的做“未来”的事情? 李钟熙:因为我们没有股东,我们是一个非营利机构,所以盈余的部分不会分到股东的手上去,会留在工研院内部转投资,所以我们的盈余越好,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有比较多的经费做未来的事情,给同仁更好的奖金、更好的研发环境。
虽然我们是非营利机构,但还是要企业化经营,两者间的关系是——经营得越好,才能更有能力支持一些更未来、更长远的事情,这个机构才会越来越好。
否则就像一个官方机构,有多少钱花多少钱,花完就算了,做得好、做得差也看不出来。
我们这里做得好,奖金会比较多,研究员有很好的发明、专利,可获得明显收入增多——这个机制是很重要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就要考虑我们做什么东西,人家愿意买单。 另外,我们要考虑到成本的控制,不是研究人员的薪水越高越好,如果不能发挥功能,我们要请他们走人,不能够是铁饭碗,那就变成官方机构了。
《21世纪》:那么谁来决定“未来”做什么?如何克服研发人员仅凭兴趣做事? 李钟熙:没错,所以我们需要双管齐下,一个自上而下,一个自下而上。
工研院有一个部门专门做市场和趋势的调查,这个团队专门做商业的规划,跟进整个科技和产业的趋势,我们再从中挑选一些自己想要着力、同时可能有比较优势的项目,并建立一些“种子计划”,放到各所、各中心让他们自己运作。
另外,我们鼓励“10%时间”自由创新技术,由研究院同仁自由组成,院里只做适当程度审查,然后支持他们,当然这个经费支持比较小。 《21世纪》:是否方便透露,在工研院众多的项目中,失败的比率有多高? 李钟熙:首先这要看怎么样叫成功,什么叫失败?以我们的观点,真正商业化、起到国际影响力的,大概10:1的关系,最多也是5:1,10个里面出来一个已经不错了,但其它9个并不表示他一点用都没有,只是他没有做得那么好,而9个里边,真正算得上失败的有2-3个。
《21世纪》:冒昧地问一句,通常工研院内做得比较好的同仁,最高年薪能拿到多少? 李钟熙:这要取决于他的表现,目前最高有不少同仁可以拿到几百万新台币,我们希望有上千万的奖励出现。
台积电只是早期模式 《21世纪》:金融风暴是否也影响到工研院? 李钟熙:这次金融风暴对官方影响比较小,但对民间影响是很大的,工研院本身其实也受到影响,主要原因是工研院有很大一个部分收入从民间客户来,民间企业受到景气度的影响,当然也会减少在研发上的支出。
所以如果我们以前做的东西,现在客户不需要了,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些转变。工研院一直希望跑在产业界的前面,业界能做的东西我们尽量回避,我们要做业界不能做的东西,所以难度更高。
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时间拉得更远一点、前瞻性一些;另外就是跨领域的结合,比如IC的,台积电做半导体技术很强,但是如果要投入生物晶片,就要生物技术加上半导体的技术,它就没有这个能力。
而工研院有不同的所,可以把很多新的东西、不同的专长结合在一起,这个对产业界来说难度就很高。 《21世纪》:代表工研院未来的是哪些技术? 李钟熙:工研院目前比较聚焦的几个产业包括光伏产业、软性电子产业、通讯晶片产业、信息安全产业、电动车和LED,还有医疗电子。
另外就是云端运算相关产业、移动应用等等。这几个都是我们现在看起来跑在前面的东西。
项目很多,其中有两个最大的方向,一个是绿能,就是所谓的Green Energy,里面还有生物医学,这两个是我们最主要希望加强的重点。 《21世纪》:台湾工研院创立于1973年,您如何看过去30多年工研院的转变? 李钟熙:从创立初到台积电诞生这个阶段,我认为比较像是在蹲马步、练功夫,那是第一个阶段,那时候经费大都从官方来;到80年代后期之后,我们跟产业界接触加深,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吸引产业界出钱;第三个阶段,我希望我们的规模不要再扩大,但影响力扩大,就是不只是靠产业界来做大,你得有很多发明,这些发明真正的价值是在后面产业化,我们要帮忙把产业的潜力和力量带起来,这个难度就很高了,不只是你给产业界做几个项目就可以的。
所以,前两个阶段有点像做劳力密集产业,第三个阶段比较像以发明IP为核心的阶段。 《21世纪》:成王败寇,有人会认为工研院80年代产生了台积电、联合电子这样的全球有影响力的公司,此后类似“成果”鲜有出现?工研院如何才能产生更多的台积电呢?工研院未来最大挑战是什么? 李钟熙:其实台积电是比较早期的模式,30年前,台湾产业界的能力也非常有限,那时候必须要跟外资合作才能把一个产业弄起来,其实半导体不是我们发明的,但是当时我们有很好的工程师,有一个很新颖的商业模式,所以台积电等做得很顺利,一部分是工研院的功劳,一部分是张忠谋和曹兴诚等创办人的功劳。
时代的因素,造就我们一生Baby,就生出一个“大Baby”。
现在我们每一年都有3-5个新公司产生,都是比较小型的公司,因为与台积电这样制造型公司不同,他们做的事情在产业上更早期,他们个头小,但专利比以前多。台积电分出去时,我们给他专利是很少的,现在新生的公司规模小,比较早期,风险比较高,社会财产占股也比较多,失败率相对高,但是成功后翻本的比率也会高很多。
所以,过去生Baby讲产值,现在讲回收比率。将来的情形会是越来越多是小公司变成大公司,扶持长大后会交由产业界去接手。
另外我们这几年在全球拿了很多创新的专利奖。 这几年企业界更国际化了,包括中国大陆在内,他们在全球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包括中国大陆——这是很大的挑战。
作为一个研究机构来讲,如果你做的东西与别人的类似,人家就不需要了,因为别的地方可能更便宜。所以我们既要做差异化、前瞻性的东西,同时又要做专利的积累。我们看到企业界越来越重视专利,因为技术即便你会做,但权利是人家发明的,你也拿不到。
没有专利,也许短时间可以经营,但是你要想变成国际化公司就不大可能。所以我们在专利的部分也特别加强,一方面是研究实质的内容、内涵要改变,另一方面建立专利群。
台湾经验,大陆市场 《21世纪》:大陆很多研究机构想拷贝工研院的模式,但是鲜有成功,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李钟熙:我也听说了大陆有“26个工研院”(笑)。我个人认为,可能是时间问题,不过也有天生资质的问题,比如项目选得不对,体制、文化因素。
我对他们了解不够多,我只能说,工研院之所以成功,不见得只是因为工研院自身,有一部分是因为台湾的环境和台湾的中小企业。 其实不只大陆有兴趣,美国人常常也过来,说“我们也搞不好”,好像全世界很多地方对工研院都有兴趣,反而是台湾岛内时常有很多批评。
还有一点,工研院的策略和定位都是不一样的,工研院每10-15年会有一次转变,比如张忠谋接任院长后,带进来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我们跟企业界的关系更密切了;后来的阶段,我希望改变,从与企业关系密切变为“跑到企业界的前面”,替他们跑在前面开路,所以专利和发明变得更重要,这些专利的产业化现在都在进行中。
所以,每个阶段工研院的模式都是不一样的,要结合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21世纪》:工研院已经在台湾南部顺应产业需要设立了南分院,随着两岸产业关系的紧密,工研院接下来有没有打算在大陆设立分院? 李钟熙:目前没有,但是将来当然是会考虑的。
我们设台湾南分院主要考虑是台湾南部的产业很多,另外是吸引当地的人才和idea。 另外,我想说,做研究其实不需要很多分院,集中反而比较容易做跨领域创新的东西。最近我们希望未来几年的重点当然是更国际化,更能够面向全球,包括面向两岸,这是大方向。
另外,我强调工研院不是台湾的,真正好的工研院是全世界的工研院,什么地方有机会,我们当然都会去。大陆方面,我们要看实际的需要,另一方面,两岸目前互信可能还不是特别足够。
《21世纪》:联发科、富士康等台湾企业向大陆转移的趋势已经确立,今年以来,开拓大陆内需的呼声也非常高,您如何看两岸科技产业的合作? 李钟熙:大陆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大陆有很多系统整合方面的能力,因为市场比较大,台湾比较偏重于元件,比如说LED,比如说手机都是这样。
台湾做得特别好的很多是一些核心的东西,比如联发科的芯片,但是这些东西最后会受到应用的影响,要跟应用、跟整个市场系统、跟产品结合,发展才会有未来性。
台湾自己要发展这样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台湾市场很小,他只能作为一个先导和试验的基地,但是他很难全部靠自己去发展新的系统和应用,有大陆这样的机会,结合起来,将来可以面向全世界的市场。
另外大陆的基础研究,很多的工程师、科学家都不错,有一些项目其实做得很好,这些科研成果放在家里也没用,我们工研院过去把这部分技术转化成产业的经验应该是个借鉴,包括专利、商业模式、产业界、国际的联接,这是工研院和台湾产业界已经建立起来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帮助大陆的很多研究加速产业化。
《21世纪》:我们在工研院参观时候注意到,工研院在3G上做了很大投入,但是你们投入的重点是WiMax,这是北美厂商主推的标准,暂时还没有进入大陆市场。
您如何看中国以及未来全球的3G,如何看中国制式标准TD-SCDMA? 李钟熙:技术是由市场来决定的,有时候官方会决定一些事情,但要看决定到哪个程度?假如技术推广得不顺利,可能消费者不接受,这都会影响到市场最后的选择,我们不会走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
我们从2000开始选择投WiMax,是因为如果我们选择人家都做的东西,那只能是搭顺风车,里面的专利都是人家的了。
产业界可以搭顺风车,因为他们可以跟大趋势生产很多东西去卖。但是我们在技术上想做下一个阶段的,而不是很热门的东西,热门是可以,但是必须要不一样,WiMax比较适合偏远地区,人口分布不多的地方再拉一条网线的成本很高,这些地方可以直接用无线的方式当做一个干线,这就是为什么WiMax在发展中国家受到欢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