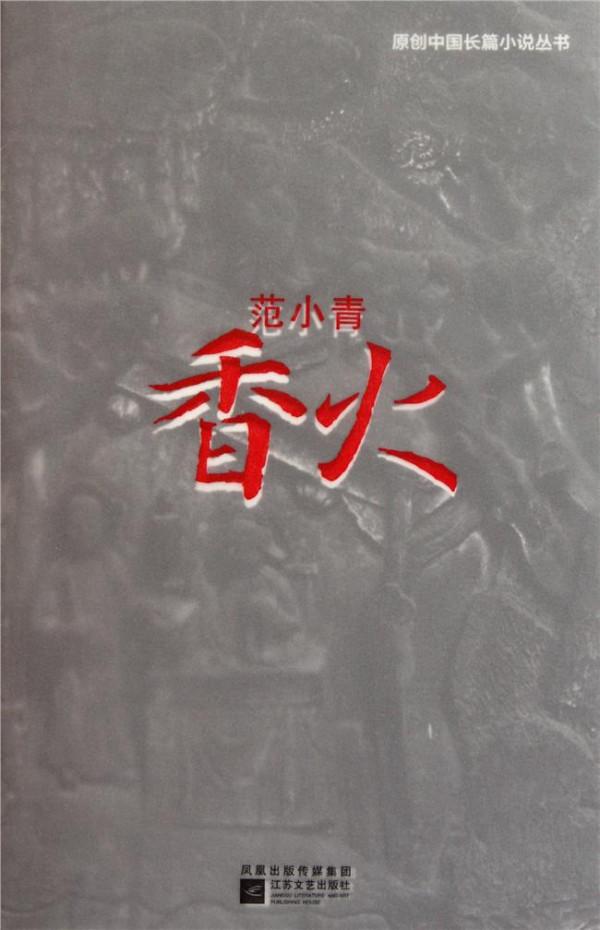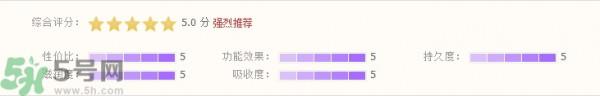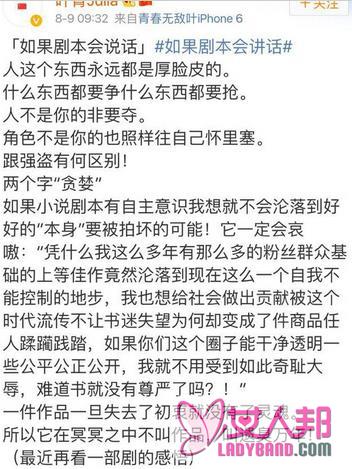范小青香火 读范小青长篇小说《香火》:变化之中有变化
从2005年发表《女同志》、2007年发表《赤脚医生万泉和》一直到2011年的《香火》(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如果不是预先知晓,我们很难想象这三部长篇是出自范小青这同一位作家之手。它们太不一样了。
4年前,南帆在其评论文章的开首便感叹,“《女同志》和《赤脚医生万泉和》的风格差异如此之大”。两年之后斯炎伟的文章《对峙的存在与言说》干脆就是立论于《女同志》和《赤脚医生万泉和》在形式与内容上的不同。
讨论一个作家的风格总是从讨论其作品的变化和差异入手,这大概是中国当代作家研究中一个非常奇特的例外。如今又来了个《香火》,它要更奇异、更加不可思议。读完《香火》之后,我在结尾处写下神不知鬼不觉几个字,以表达自己莫名的赞赏。
一直被认为温文尔雅、姿态柔软的范小青内里竟蕴藏着如此强烈的求变欲望。这使我想起早年范小青那篇谈自己的文章中记下的一桩趣事:一个比较软弱的我,一有风吹草动便夹着尾巴做人,即使风平浪静,也常常居安思危,庸人自扰的我,小的时候竟然拿脑袋去撞苏州街上的石子。
把《香火》比做用脑袋撞石头的书写有点不伦不类,但这种碰撞中插入柔软的“心”便耐人寻味了。用朱文颖的理解,那便是“水”的力量。
《香火》全书12章,贯串始终又无处不在的是香火,他在太平寺、阴阳岗、烈士陵园和孔家村之间来回穿梭。无论饥荒年代、动乱年代和太平年代,他都是亲历者和参与者;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鬼,在场还是缺席,理解还是不理解的,他都起着媒介的作用,他既混淆着对立的双方,同时又站在两者之间。
对范小青而言,写作就是要打破一堵堵墙,墙前是明白无误的谎言,而墙后的黑暗中却隐藏着神秘莫测的永恒。如果说《赤脚医生万泉和》视角的特殊性是自我束缚的,那么《香火》的视角则是一种无限放大:阴阳两界,上天入地,人鬼共舞都是其自由出入的视域。
小说中记录了香火的若干种死法:听说,“香火调戏女知青被死鬼带走了”;又有说,“是庙塌了,压下来砸死的”;传说那原名叫孔大宝的香火“吃了棺材里的青蛙,得了怪病”,“他爹领着他到处看病,碰上大风大雨,摆渡船翻了,船上的人都淹没了”。
不止香火,还有那烈士陵园主任的N种死法,还有香火他爹和船工,他们都还魂般的在故事中复活。
这是一个鬼的故事,但又和传统意义上的鬼故事划清了界线。虚构的世界也可以看做一个心理世界,具有自身的规则。心理分析围绕的核心是弗洛伊德理论:压抑的回归。这种分析机制的关键是时间和记忆的概念;意识既戴着欺骗性的面具,同时也切实流露出某些往事的痕迹;正是意识组织着“现在”的一切。
如果“过去”受到了压抑,它就会不露痕迹地回返到它不被容身的“现在”。为了说明这一点,弗洛伊德特别喜欢引出一段促狭的故事:哈姆雷特的父亲,在被谋杀后还是化身鬼魂回返世间,更换舞台;而恰恰在此时,他成为儿子俯首遵从的法则。
《香火》自然不是弗洛伊德理论的摹仿,但试图释放视角的压抑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叙事者渴望超凡的视角,香火等人则成了回归人世的替身。香火是现实和神话两个不同世界相互交融的产物,是小说双焦视点的产物。
一个叙事者总是隐秘的,换句话说,这种隐秘性既包括通过一个有缺陷的角度提示真相来讲故事,比如《赤脚医生万泉和》;也有我们不知道并且也许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叙事者是谁的观念,比如《香火》。前者把“秘密”当做一种揭示,而后者是一种真正的秘密,即便确有其事也绝不通过任何一种方式揭示出来。
关于香火和烈士陵园主任的数种死法中,究竟哪种是确切可信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秘密,秘密的本质就在于它的不可揭示性。重要的是作者用来意指一种已经消失、可能不存在的人或物可作为一种视线、一种叙述视角,他们似幽灵鬼魂般地四处飘移,余意未尽似的评估议论变化中的现实,不露声色地审视着一个新的或剩下的世界,那些不变中的变化、变化中的不变和重复。
这里,“视角” 这个词也许跟那些迷恋它而用它的人们开了个玩笑。他们借用它的意义,它越快地把他们引向不愿去的地方。一座太平寺,一个庙里打杂的香火经历了三个时代的变迁,而这些经由虚构的、想象的、隐喻的经历让我们瞥见饥饿苦难和动乱的纠缠不休,见证了太平年代财富诱惑和权力。
而且这些经历被滑稽性所模仿、被讽喻所叙述,这是不容忽视的东西当做荒唐的东西加以拒绝或修改的历史。当怪诞或灾难性事件被坦然接受时,这“喜剧”的手法后面便隐藏着作者内敛的情感。叙述从现实中扯下一种荒唐,因此而逆转悲剧情节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