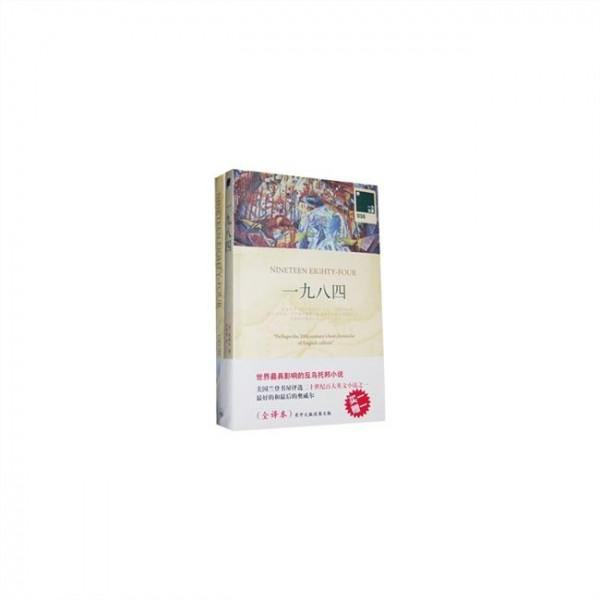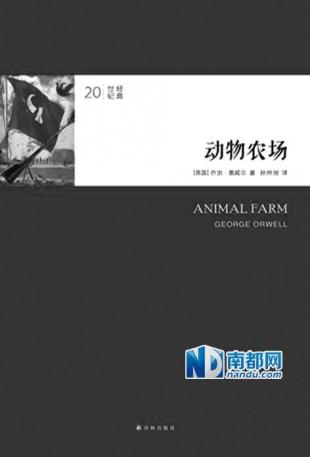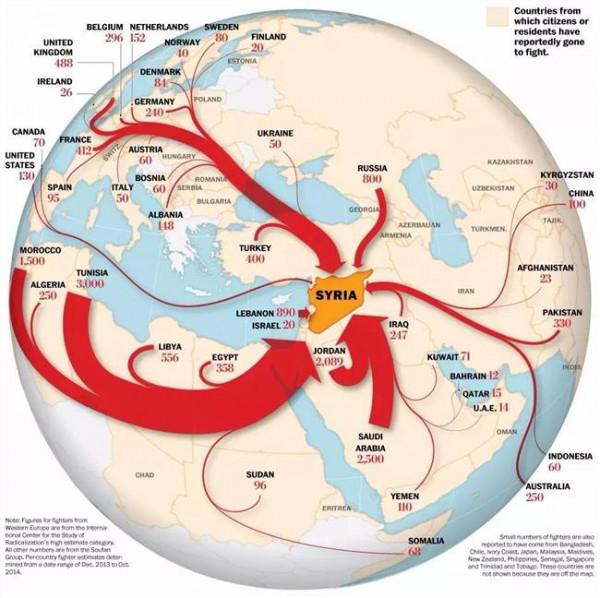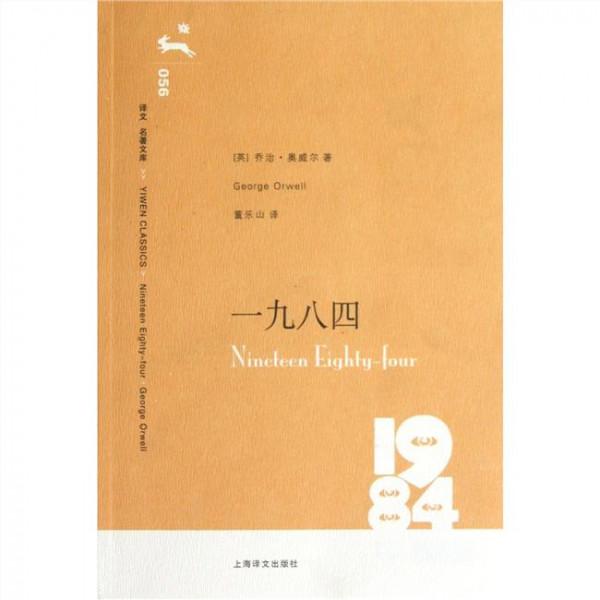1984孙仲旭 1984(奥威尔传世杰作 反极权经典作品 孙仲旭译本)[当当]
★乔治奥威尔*经典的代表作《1984》 ★世界文坛*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1984》
《1984》是一部伟大的政治寓言。1984年的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瓜分,三个国家之间战争不断,国家内部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均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并用高科技手段监视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维持社会的运转。
乔治奥威尔(19031950) 英国著名作家,社会评论家,英语文体家。年轻时曾赴缅甸加入帝国警察部队,后因厌倦殖民行径而返回欧洲,开始文学创作。后参加西班牙内战,并在二战中积极投身反纳粹活动,1950年死于困扰多年的肺病。著有《1984》《动物庄园》等十余部作品,其中充满了社会关怀、人类理想和反极权的思想,被称为“一代人冷峻的良心”。
代译序 1984 附录 一、新话的原则 二、我为何写作
★《1984》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展现出不可磨灭的才华,令其他同类作品无法望其项背。对时代来说,它仿佛毒药瓶上的一枚标签。 《纽约先驱论坛报》 ★乔治奥威尔的遗世杰作……是了解现代历史不可或缺而又引人人胜的一本书。
〕 《纽约书评》 ★乔治奥威尔就极权主义危险发出的警告,给他的同时代人和未来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本书的书名和其中创造的很多新词,比如“新语”,都成了现代政治中丑恶现象的代名词。 《韦氏文学百科词典》 ★只能用两个词来形容奥威尔:一是“圣徒”,指这个人;一是“先知”,因为他写出了《动物农场》和《1984》。
中国著名学者止庵 ★所有英国作家中最受爱戴的一位。 英国作家、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 ★乔治奥威尔最后的杰作,对现代历史令人着迷而不可或缺的理解。 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蒂莫西加里阿什
这是四月里的一天,天气晴朗却又寒冷,时钟敲了十三下。温斯顿史密斯快步溜进胜利大厦的玻璃门。他低垂着头,想躲过阴冷的风,但动作还是不够快,没能把一股卷着沙土的旋风关到门外。 门厅里有股煮卷心菜和旧床垫的气味。
门厅那头钉着一张彩色宣传画,大得不适合钉在室内,上面只有一张巨大的面孔,宽度超过一米。那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蓄着浓密的黑色八字胡,面相粗犷而英俊。温斯顿朝楼梯走去。想坐电梯是没希望的,即使在情形最好时也很少开。
目前白天停电,这是为迎接仇恨周的一项节约举措。温斯顿所住的公寓在七楼,他现年三十九岁,右脚踝上方还有一处因静脉曲张形成的溃疡,所以只能缓慢地走楼梯上去,中途还歇了几次。每层楼梯正对电梯门的墙上,那张有着巨大面孔的宣传画从那里凝视着,它是那种设计得眼神能跟着你到处移动的肖像画。
“老大哥在看着你”,下方印着这样的标题。 在公寓里,有个洪亮的声音正在念一连串数字,跟生铁产量有关。此声音来自一块长方形金属板,它像一面毛玻璃面的镜子,嵌在右墙上。
温斯顿扭了一下开关,声音多少低了一点,但仍清晰可闻。这个装置(叫做电屏)的声音能调小,然而没办法完全关掉。他走到窗前。他的体形偏小,瘦弱,作为党员制服的蓝色工作服只是让他更显单薄。
他长着淡色头发,面色红润自然,皮肤因为使用劣质肥皂和钝剃须刀片而变得粗糙,然而冬天的寒意才刚刚结束。 外面,即使隔着关闭的窗户,看去仍然一副寒冷的样子。下面街道上,小股的旋风卷动尘土及碎纸螺旋上升。
虽然出了太阳,天空也蓝得刺眼,但是除了到处张贴的宣传画,似乎一切都没了颜色。那张蓄着黑色八字胡的脸从每个能望到两边的街角居高临下地盯着。正对面的房屋前面就贴了一张,印有标题“老大哥在看着你”,那双黑眼睛死盯着温斯顿。
下面临街处还有另外一张宣传画,一角已破,在随风一阵阵拍打着,把一个词一会儿盖住,一会儿又展开:“英社”。远处,一架直升飞机从屋顶间掠过,像苍蝇般在空中盘旋一会儿,然后划了道弧线疾飞而去。
那是警察巡逻队,正在窥视人们的窗户。但巡逻队还不足为惧,足以为惧的只是思想警察。 在温斯顿身后,电屏传出的声音仍在喋喋不休地播报有关生铁产量和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消息。
电屏能同时接收和发送温斯顿所发出的任何声音,只要高于极低的细语,就能被它拾音。而且不仅如此,只要他待在那块金属板的视域之内,他就不仅能被听到,而且也能被看到。当然,在具体的某一时刻,你没办法知道自己是否正在被监视。
思想警察接进某条电线的频度如何以及按照何种规定进行,都只能靠臆测,甚至有可能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着每个人。但无论如何,他们可以随时接上你那条电线。你只能生活确实是生活,一开始是习惯,后来变成了本能在一个设想之下,即除非你处在黑暗中,否则你所发出的每个声音都会被偷听,每个举动都会被细察。
温斯顿保持着背对电屏的姿势,这样比较安全些,不过他也知道,即使是背部,也可能暴露出什么。
一公里之外是真理部,那是他上班的地方,是幢在一片不堪入目的地带拔地而起的白色大型建筑。这里他略带几分厌恶地想道这里就是伦敦,第一空域的主要城市。第一空域本身是大洋国人口第三大的省份。他绞尽脑汁,想找回一点童年记忆,以便让他记起伦敦是否一直就是这个样子:满眼都是摇摇欲坠的建于十九世纪的房屋,侧墙靠木头架子撑着,窗户用纸板挡着,屋顶是波纹铁皮,破旧的院墙东歪西斜。
是否一直就是这样?在挨过炸弹的地方,空中飞扬着灰泥和尘土,野花在一堆堆瓦砾上蔓生,还冒出许多龌龊的聚居区,也就是鸡舍一样的木板屋。
是否一直就是这样?可是没用,他想不起来:他的童年除了一系列光亮的静态画面,什么也没留下,而那些画面都缺少背景,大部分也不可理解。
真理部用新话 来说就是“真部”跟视野中能看到的其他建筑明显不同。它是座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白色水泥熠熠发亮。它拔地入云,一级叠一级,高达三百米。从温斯顿所站的地方,刚好能看到党的三条标语,用漂亮的美术字体镌刻在真理部大楼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的房间就多达三千间,另外还有相应的地下附属建筑。
此外只有三座外表及规模类似的大楼分散坐落在伦敦,周围的建筑彻底被那三座大楼比了下去,所以站在胜利大厦顶上,同时可以看到这四座大楼,分别为四个部的所在地,政府的所有职能就分工到了这四个部。
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美术,和平部负责战争,仁爱部负责维持法律和秩序,富足部负责经济事务。
这四个部的名称用新话来说,分别是“真部”、“和部”、“爱部”和“富部”。 仁爱部是真正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那里根本没有窗户。温斯顿从未去过仁爱部,也未曾进入过它的方圆半公里之内。
那里闲人莫入,进去时,还要经过一段布着带刺铁丝网的错综复杂的道路、一道道钢门以及机关枪暗堡。甚至在通向它外围屏障的街道上,也有面目狰狞的警卫在转悠。他们身穿黑色制服,手持两节警棍。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脸上已经换上了一副从容而乐观的表情。面对电屏时,这样做是明智的。他穿过房间,走进那间很小的厨房。这个时间离开部里,就放弃了在食堂的一顿午餐,他也知道厨房里除了一大块黑面包别无他物,得把它留到明天早上当早餐。
他从架子上拿了个装有无色液体的瓶子,上面简单的白标签上印着“胜利杜松子酒”。如同中国的米酒,它散发的也是一股令人作呕、油一般的气味。温斯顿倒了快有一茶杯,鼓了鼓勇气,然后像喝药一样一口气灌了下去。
马上,他的脸变得通红,眼里流出了泪水。那玩意儿像是硝酸,不仅如此,喝的时候还给人一种后脑勺挨了一胶皮警棍的感觉。过了一会儿,他胃里的灼热感消退了一点,一切好像没那么难受了。他从印有“胜利香烟”的压扁了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烟,不小心把它拿倒了,烟丝因此掉了出来。
他又抽出一根,这次好了点。他回到起居室,在位于电屏左侧的一张小桌子那里坐下来。他从桌子抽屉里取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和一本四开大的空白厚本子,它的封底是红色的,封面压有大理石纹。
不知为何,起居室里的电屏安装的位置不同寻常。它通常在远端的墙上,这样可以监视到整个房间,这张电屏却安在较长的那面墙上,正对窗户。电屏一侧有个浅凹处,温斯顿就坐在这里。
建这幢公寓楼时,这地方很可能原意是用来摆书橱的。温斯顿坐在这个凹处,尽量把身子往后靠,这样可以保持在电屏的视域范围之外。当然,他的声音仍会被听到,不过只要待在目前的位置,他就不会被看到。
他之所以想到这会儿要做的这件事,部分原因就是这房间不一般的布局。 同样让他想到做这件事的,还有他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本子,这是本异常漂亮的本子,纸质光滑细腻,因为岁月久远而变得有点泛黄。那种纸至少已经停产了四十年,因而他估计那本本子的年份远不止四十年。
他在一间肮脏的小杂货铺的橱窗里看到它,那间铺子位于市内某个贫民区(究竟是哪个区,他现在不记得了),当时他马上有了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想拥有它。党员不应该进入普通店铺(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买卖”),但这一规定未被严格执行,因为许多东西如鞋带和剃须刀片除非去那里,否则就买不到。
他往街道左右两个方向迅速瞄了瞄,然后溜进去花两元五角钱买下了它,也没想它能派什么用场。
他知错犯错地把它放在公文包里带回家,上面就算什么也不写,拥有它也算是有违原则。 他准备要做的,是开始写日记,这不算是件非法的事(没什么是非法的,因为不再有法律),然而被发现的话,有理由可以肯定惩罚会是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劳改。
温斯顿把钢笔尖装到笔杆上,用嘴吸掉上面的油脂。钢笔是种过时的东西,就连签字时也很少用,他偷偷摸摸、而且是费了些事才得到一杆,只是因为他感觉那种漂亮细腻的纸张配得上用真正的钢笔尖在上面书写,而不是拿蘸水笔划拉。
其实他还不习惯用手写字,除了写很短的便条,他通常什么都对着口述记录器口授,对目前想做的这件事而言,当然不可能那样做。他把钢笔蘸在墨水里,然后踌躇了仅仅一秒钟。
他感到全身一阵战栗,落笔是件决定性行为。他以笨拙的小字体写道: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往后靠着坐在那里,陷入一种完全无助的感觉中。首先,他对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完全没把握,不过可以肯定是那年前后,因为他对自己是三十九岁这点很有把握,而且相信自己是出生于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五年。
不过如今在确定年份时,不可能没有一两年误差。 突然,他想起一个问题,他写日记是为了谁?为了未来,为了未出生的人。他的心思围绕那可疑的年份转了一会儿,心里忽然咯噔一下,想起新话里的“双重思想”一词。
他第一次想到此举的艰巨性:你怎样去跟未来沟通?从根本上说这不可能。要么未来与现在相似,在此情况下,未来也不会听他说;要么未来跟现在不同,他的预言便将毫无意义。
他对着那张纸呆看了一会儿。电屏里已经换播刺耳的军乐。奇怪的是,他似乎不仅失去了表达自我的力量,甚至忘了他本来想说什么。在过去几周里,他一直在为这一刻做准备,从未想到除了勇气还需要别的什么。
真正动笔不难,需要做的,只是将他大脑里没完没了、焦躁不安的内心独白转移到纸上就行了。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然而在这一刻,就连这种独白也枯竭了。另外,那处静脉曲张的溃疡又痒得难受,可是他不敢搔,因为一搔就会红肿发炎。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除了面前纸上的空白、脚踝上方的皮肤痒、电屏里尖锐刺耳的音乐和喝酒造成的一丝醉意,他别无感觉。突然,他完全是慌里慌张地写起来,但他对正在写下的东西并非全然心里有数。
他用儿童式的小字体在纸上随意写着,一开始漏了大写,到最后连标点也不用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天晚上去看了电影,全是战争片。很好看的一部是关于一艘满载难民的船在地中海某处被轰炸的事。
观众很开心地看到一个胖男人奋力游泳逃离一架直升飞机追赶的镜头。一开始看到他像头海豚一样在水里扑腾,然后是通过直升飞机上的瞄准器看到他,接着他全身都是枪眼,他身体周围的海水都变成了粉红色,他突然沉下去,好像枪眼导致进水,观众在他下沉时大声哄笑。
然后看到的是一条坐满儿童的救生艇,上面有架直升飞机在盘旋。有个可能是犹太人的中年妇女坐在船头,抱着个大约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吓得尖叫,把头深深扎进她怀里,似乎想在她身上钻个洞而那个女人把胳膊围绕着他安慰他尽管她自己也已经害怕得脸色发青,一直在尽量掩护着他似乎她以为她的双臂能为他挡住子弹。
然后直升飞机往他们中间投下一个二十公斤重的炸弹一道强光小艇变成了碎片。
接着是个拍得很清晰的镜头是个小孩的手臂往空中飞得高高安在直升飞机前端的摄影机肯定在追着它拍从党员座位那里传来一片鼓掌声但在群众席那里有个女人突然无故喧哗起来嚷叫着说他们不该放给孩子看他们做得不对别放给小孩看直到警察去把她架了出去我不认为她会有什么事谁也不关心群众说什么群众的典型反应他们从来不会 温斯顿停下笔,部分原因是肌肉痉挛。
他不知道是什么让他的笔尖流淌出这些垃圾东西。然而奇怪的是,写这些东西时,他脑子里清清楚楚记起了另外一件事,以至于他几乎也想把它写下来。
他意识到就是因为这另外一件事,他突然决定回到家里并从这天开始记日记。 如果那样模糊的一件事也能称为发生过,那么它是发生在那天上午,在部里。
当时快到十一点了,在温斯顿所在的档案司,人们开始从小隔间里往外拉椅子,摆在大厅中间,正对着大电屏,这是为两分钟仇恨会做准备。温斯顿正要在中间一排某个位置就座,有两个他只是面熟,但从未说过话的人出乎意料地来了。
其中一位是个女孩,他经常在走廊里跟她擦肩而过。他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可能因为她有时两手都沾着油,还拿了个扳手她负责某部长篇小说写作机的机械维修工作。
她是个样子大胆的女孩,差不多二十七岁左右,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脸上有雀斑,动作像运动员那样敏捷。一条窄窄的鲜红色饰带那是青少年反性同盟成员的标志在她工作服的腰带上缠了几圈,松紧程度刚好能显现出她臀部的优美线条。
从第一次看到她的那刻起,温斯顿就讨厌她,他也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她随时随地营造的那种代表着曲棍球场、冷水浴、集体远足和完全心无杂念的氛围。他几乎仇恨所有女人,特别是年轻貌美的。女人特别是所有的年轻女人总是党最死心塌地的信徒、轻信宣传口号的人、业余侦探和异端思想的包打听。
但这个女孩给了他一种印象,就是她比绝大多数女人更危险。有一次,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时,她迅速瞟了他一眼,那眼神好像刺进他体内,并注入一种黑色的恐惧感。
他脑子里甚至想到,她有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不过事实上,这种机会微乎其微,但每次只要她在附近,仍会让他感觉特别不自在,这种感觉混合了敌意,还有恐惧。 另外一位是个男的,名叫奥布兰,是名内党党员。
他的职务重要而不可测,温斯顿对其性质只是略有感觉而已。看到一名身穿黑色工作服的内党党员走过来时,椅子周围的这群人中出现了片刻的肃静。奥布兰高大结实,脖子很粗,面容粗糙,为人幽默而又冷酷。
虽然外表让人望而生畏,但他的举止有一定的魅力。他有一招,就是推一推架在鼻子上的眼镜,这个动作很奇怪,能让人解除戒心说不上为什么,但是奇怪地给人以文质彬彬的感觉。如果还有人这样想的话,这个动作也许能让人想起一位十八世纪的贵族在邀请别人用他的鼻烟。
十几年来,温斯顿见到奥布兰的次数可能差不多也就是十几次。他感到奥布兰对他而言很有吸引力,不仅因为后者温文尔雅的举止与职业拳击手块头的反差让他觉得很有趣,更因为他有个秘密信念也许根本不是信念,而是一丝希望,即奥布兰在政治正统性方面并非完美无瑕,他的表情无疑说明了这一点。
话又说回来,也许他脸上表现出的根本不是非正统性,只不过是智慧。但不管怎样,从外表上看,他是那种可以跟他谈谈心的人,如果有办法躲过电屏跟他单独在一起的话。
温斯顿从未付出一点努力去证实这种猜测,确实,也没办法证实。那时,奥布兰看了一眼手表,看到马上快十一点了,显然决定留在档案司,直到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跟温斯顿坐在同一排,中间隔了几张椅子,一个黄红色头发的矮个女人坐在他们中间,她在温斯顿隔壁的小隔间工作。那个黑头发女孩正好坐在温斯顿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