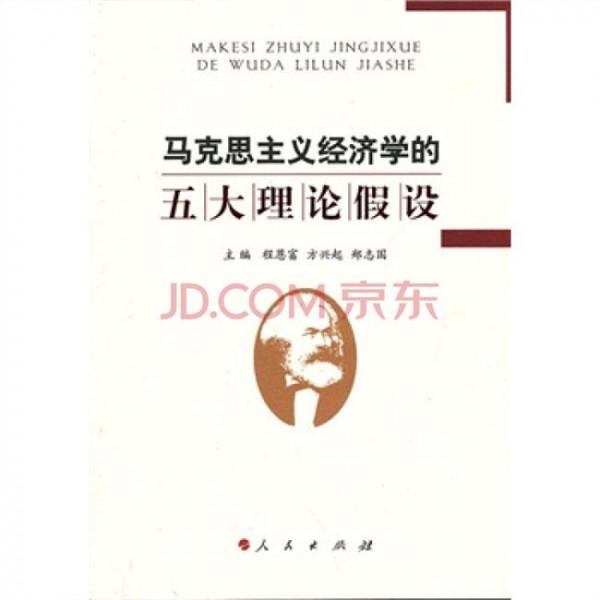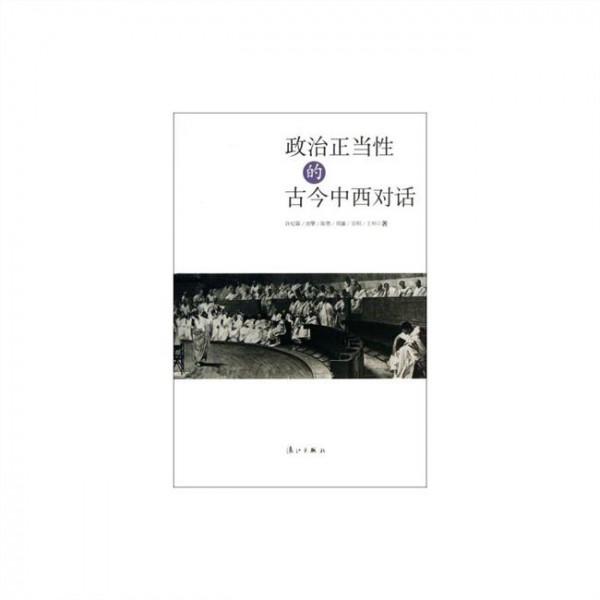巴特勒政治 性/性别不连贯的政治(by:朱迪斯巴特勒)(转载)
当然,这段文字出自搞混了亚里斯多德对普遍范畴和特殊事例之间的区分的中文百科全书。然而,还有皮埃尔•里维埃尔 "粉碎性的狂笑",他杀害家人而摧毁了他的家庭--或许对福柯来说是摧毁了家庭这个概念,这几乎等于否定了亲属关系范畴,而扩大来说的话,也否定了性别范畴。
当然,还有现今很著名的那个巴塔耶(Bataille)的笑,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里告诉我们,这笑指代逃脱了黑格尔辩证法概念掌控的一种超越(excess)。
福柯会发笑,正因为这个问题的立意基础就是他寻求置换的那个二元结构,这个令人生厌的同一与他者的二元结构,不止贻害了辩证法的传承,也同样贻害了性别的辩证。然后当然还有埃莲娜•西苏告诉我们的美杜莎的笑,它粉碎了那让人石化的凝视所造成的平静表面,揭露了同一与他者的辩证是以性差异为轴线进行的。
赫尔克林以一种自觉的姿态呼应了美杜莎的故事,她/他写道:"我的凝视所具有的冰冷的凝固力似乎冻结了"(105)那些与我的视线相遇的人。
当然,伊里格瑞揭露了这个同一和他者的辩证是一个虚假的二元结构,它是一种对称的差异的假象,巩固了形而上学的阳具逻格斯中心经济,也就是同一经济(the economy of the same)。
根据她的观点,他者和同一都是男性的标记;他者不过是从反面来阐发男性主体,它造成的结果是女性这一性无法得到再现--也就是说在这个意指经济里,这是一个不算数的性别。
然而,女性不是一个性别,也是从它逃避了象征秩序所特有的单义意指这层意义上来说,同时也因为它不是一个实体的身份,而与造成它的不在场的那个经济之间,总是、也只是处于一种未确定的差异关系。
它并非"单一"的,因为它的快感和它的意指模式是多元而弥散的。的确,赫尔克林那些显然是多样多元的快感,也许可以成为女性/阴性的标记--具有多元价值,而且拒绝屈服于单义意指实践的简化作为。 但是我们别忘了赫尔克林与笑的关系,她的笑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害怕被人取笑(23),再后来是轻蔑的嘲笑,这是针对医生而发的;这位医生得知了这个天生异常的状况,却没有向适当的单位举报,在这之后她/他失去了对他的尊敬(71)。
对赫尔克林来说,笑似乎代表的不是羞辱就是轻蔑。这两种立场无疑都与一个谴责性的律法有关,两者都屈从于这个律法,或者作为它的工具、或者作为它的目标。赫尔克林并没有踏出那律法的辖权之外;甚至于对她/他的放逐的理解也是以惩罚的模式为根据。
就在第一页,她/他述说了她/他的"位置在这个拒我于千里之外的世界里没有被标示出来。" 她/他道出了她/他自小就有的一种卑贱感,后来这卑贱感先是以一个跟一条"狗"或一名"奴隶"一样的忠实的女儿或情人展现;最后,当她/他被驱逐、也自我放逐于所有人类的领域之外时,这卑贱感终于演变为一种全面的、致命的形式。
从这个自杀前的孤立经验,她/他宣称自己远远凌驾于两性之上,然而她/他的愤怒大半还是针对男人:在她/他与撒拉的亲密关系里,她/他曾经试图篡夺男人的"名号";而现在她/他毫无保留地控诉男人,认为他们以某种方式禁绝了她/他爱的可能。
在叙事的一开头,她/他安排两段彼此"对应"的单句的段落,暗示了对失去的父亲的一种抑郁合并--通过结构性地将那负面情绪建制到她/他的身份和欲望里,而延宕被遗弃的愤怒。
在她/他说出她/他在事先不知情的情况下迅速地被母亲抛弃之前,她/他告诉我们因为某些缘故,她/他在弃儿与孤儿的收容院里呆了几年。
她/他提到那些"可怜虫,被剥夺了母爱的摇篮。"下一句里,她/他形容这个收容所是"痛苦和磨难的庇护所",而接下来的句子提到她/他的父亲,说"突如其来的死亡将他……从我母亲的温柔情意里强行带走"(4)。
虽然她/他通过怜悯其他突然丧母的人,而两次转移了她自己被遗弃的痛苦,但通过这样的转移她/他建立了一种认同,这认同在后来重新以父女共同的不幸遭遇--被剥夺了母性的抚慰--的面目出现。
当赫尔克林持续地爱上一个又一个的"母亲",然后又爱上许多不同的母亲们的"女儿"而冒犯了形形色色的母亲时,这些欲望的转移可以说是在语义上形成了一种复合的状况。事实上,她/他一直在大家所爱慕、为之激动的对象,与受轻蔑、被抛弃的对象两者之间摆荡,这是不加以干预而任其自食其果的一种抑郁结构分裂的结果。
如果如弗洛伊德所说的,抑郁牵涉了自责,而如果那样的自责是一种负面的自恋(关注自我,即使只是以指责那个自我的模式),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赫尔克林:她/他不断地陷入了负面与正面的自恋情绪里,一方面自认为是这个世界上彻底被遗弃和最被忽略的人,同时又认为自己对所有接近他/她的人都具有一种魅惑力,事实上,对所有女人而言她/他是比任何一个"男人"(107)都要好的人。
她/他提到那所收容孤儿的医院,说它是她/他早年的一个"痛苦的庇护所",而她/他在叙事的结尾,带有象征意味地再度与这个寓居之地相遇,而此时它是一个"坟墓的憩息所"。
如同那个早期岁月的庇护所,使她/他能够与父亲的幽灵神奇地交流和认同,死亡的坟墓里也已经躺着了她/他希望能在死后与之相逢的父亲:"看到这坟墓让我与生命和解,"她写道,"它让我对那躺在我脚下的枯骨感到一种莫名的温柔"(109)。
然而这爱--被表述为面对抛弃他们的母亲的一种休戚与共的关系--决非完全涤除了被抛弃的愤怒:在"[她/他]脚下的"父亲,之前被扩大为代表男人这个整体,而她/他凌驾于所有男人之上,她/他宣称自己俯视着他们(107),向他们发出轻蔑的嘲笑。稍早她/他提到发现她/他异常状况的医生时说:"我希望他被打入十八层地狱!"(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