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作品解放战争 对话献礼巨作《解放战争》作者王树增
从《朝鲜战争》到《长征》再到今天的《解放战争》,王树增的书一直保持了一个鲜明而独特的风格,正如《人民文学》主编李敬泽先生所说,“当代以来形成的文学秩序中很难安放这样的作品”。
李敬泽说,我们永远需要另一种历史:叙事的历史,保存着人的具体性的历史,由人类创造并属于人的历史。这种叙事史自司马迁和希罗多德以来,一直是人类公共记忆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形式。所以,我们最终把《解放战争》的体裁标为‘叙事史’。
”他认为这样的作品既“抵达历史,也抵达文学”。 王树增说,自己一直坚持对非虚构类文学写作做较为理想的尝试。“很多人把我的作品称为纪实文学。
有人说,纪实文学只求历史背景真实,对细节则进行虚构。其实,纪实即不是虚构,虚构则不是纪实。我的作品中所有的人,哪怕是战场上的一个战士,都是有出处的;尽管极少对话;战斗打响时是晴天还是大雨,也是有史料依据的。
只不过我的叙事文字,与军事研究机构写出的战史不同,不是那种盖棺定论式的文字;也与一些作家致力于揭秘不一样,没有那种小说情节般的描写。我的作品是纪实的,但我的记述是具有文学品性的。
通俗地说,我说的是真事,不是我虚构的事,但我不是传达文件一样告诉你,也不是小道消息一样告诉你,是一种可以让你感同身受的对历史现场的叙述,是一种包含着我的人文认知、人文情感的叙述。” 至于还原历史真实的程度,他则表示,历史本身都是过往事件,人类是难以穷尽其真相的,因为所有留下的历史都是书写者笔下的历史,所有口述的历史都是说者记忆中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的真实都是相对的。
“我经常会被问及,你写了什么鲜为人知的事?有什么新的史实披露?其实,我不可能在历史本身之外虚构历史。现在很多书冠以解密或揭秘之名,书名确实具有商品社会的广告功能。但是,历史并无多少秘密是别人都不知道,只有他才知道,专门等着他来揭秘给大家看的。
怎么可能呢?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不知道的那些史实,我们永远都无法知晓。或者我们能够捕捉到一些线索,但线索是不足以说明本来面貌。
当然,会有如何叙述历史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将影响作品的客观性,特别是涉及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我们知道这样的书籍出版必须经过军事权威部门专家的审查才能出版。我在三本书中都写了通常认为比较敏感的史实,比如朝鲜战争中的东线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十个师围堵美军陆战一师一个师,最后美军连伤员和战死者的尸体都撤出去了。
比如后来说张国焘放弃川陕根据地,但恰恰是中央红军导致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最终失去川陕根据地的。
但我绝不是从揭秘、暴露的角度写的。历史观将最终决定你复原历史面貌的真实程度,这个历史观就是知道一个具体事件发生时历史的大势。大势一直在,你的叙述就不会让原貌走样”。 同时,王树增也坦承:“当然个别时候,还是下笔有虑有避的”。
前期笔记是成书文字的4至5倍;新中国是用无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是一句空话,是用一个个生命的个数写出来的,“他们给予了我们一个崭新的中国,我们必须珍惜” 自1994年开始,王树增用了15年的时间写《朝鲜战争》、《长征》、《解放战争》。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70岁时,曾带着心脏起搏器重走长征路,写了《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王树增说,索尔兹伯里只是走了中央红军长征时走过的重要地点,而且是中国政府全程保障着他走的。
“对于我而言,长征路,是在我生命的前30年间断断续续走的。我人微力薄,不可能像索尔兹伯里那样有人保障着集中走一遍长征路,并且让此事成为一个国家的新闻事件。
也许是职业的原因,我去任何地方,最令我关注的还是与战争有关的一切,我在我的经历中一点点地积累、收藏着这一切。比如,我并没有写抗日战争,但我会在去江苏开会期间去如皋,我很想看看抗日战争时粟裕打仗的战场是什么样子。
我在写《长征》的10年前,就去了二、六军团北进四川时路过的中甸,我甚至去看了当年贺龙渡金沙江的石鼓渡口,看了那个极其偏远寂寞的小镇。我去山西,看了阎锡山的故居,还去看了徐向前故居。阎锡山故居观者熙攘,徐向前的故居那一天只有我一个参观者,这种情景给予我的感受和感慨,在我后来写《长征》和《解放战争》时,都隐藏在我的文字叙述中。
我还去了锦州城,城市的混乱与嘈杂让我感觉十分异样,那种东北人毫无顾忌的喊叫以及道路难以迈脚的杂乱,宛如大战爆发前。
只是当年支前的民工讲起他们是如何为解放军带路时,我才切实感到战争已经结束60年了”。 王树增用“浩如烟海”形容自己为写作所做的准备工作:“简单地说,要看敌我双方的战史,重要的是要知道敌我双方的战史中,涉及具体的战役时,哪些内容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一样。
还要看所有能够找到的战争亲历者的回忆,上至战役的指挥者,下至一场战斗的参加者,甚至是躲在自家墙根下远远地看着两军打来打去的旁观者的回忆。
另一个重要的工作是阅读电报,我用了5个月的时间,阅读我能找到的有关解放战争的所有电报,对于每一封电报,我一定要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封电报,它出现的前因后果是什么?我认为没有什么比电报更真实的了。
比如,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在给林彪的电报中曾经说,打这场仗,要准备死多少人,战前须准备多少裹尸布,而毛泽东给出数字令我十分震惊。
我可以读出当时的形势有多么严峻,毛泽东的决心有多么强硬,而战争在那个瞬间的演变将以多少人的生命为代价。我在《解放战争》中特别摘引了这封电报。而更重要的是,我要明白毛泽东和林彪何以要这样?当时中国的什么问题导致共产党人不惜一切地抗争?还有,那些士兵为什么情愿付出生命,是什么使成千上万的青年投身到战火中?这些思考是至关重要的,是写作过程中始终的心理依据,是使作品的叙述具有生命力的唯一要素。
还有历史文献,我要花大量时间去读它,比如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军队作战,每每战前都有政治动员令。以今天的眼光看,那些文字极具特色,甚至是一种世间少有的古怪特色,在它之前和之后都不会有这样的文字了。读来可理解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它何以会在4年间让整个战争翻盘”。
通过一个简单的数字,读者或许可以知道王树增为写作付出的心血,那就是他在前期所做的大量笔记:“《长征》、《朝鲜战争》、《解放战争》笔记的文字量几乎都是是成书的四五倍,费时费力费心难以言表”。
同时王树增也表示,写作中的最大困难或者说遗憾,并不是掌握与占有材料的艰辛和全面与否,而是对历史认知的深度和广度。
“个人的能力总是有限的,在有限的能力下总渴望通过无限的努力,达成对历史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认知。这种努力做得越有成效,对历史的解读就会对于今天更具价值。
但是,确实无法穷其尽”。 对于680万字的《解放战争》一书,王树增谈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最大的体会时却只用了简单8个字,那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水可载舟,也可覆舟。
“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无论是夺取还是巩固政权,这是必须牢记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再过半个月,共和国就将迎来自己诞生一个甲子的庆祝日,作为共和国的一名军人,作为一位一直关注近代以来历史大势、长期致力于现代革命战争史写作的军旅作家,王树增有着简单而质朴的告白———珍惜今天。
他说,新中国是用无数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不是一句空话,是用一个个生命的个数写出来的:济南战役,人民解放军伤亡29278人;辽沈战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7339人;淮海战役,人民解放军伤亡124772人;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伤亡46001……“他们给予了我们一个崭新的中国,我们必须珍惜。
同时,在生命中的某一天,可以想一想,你为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做了什么。”(李雪萌 中国作家网/济南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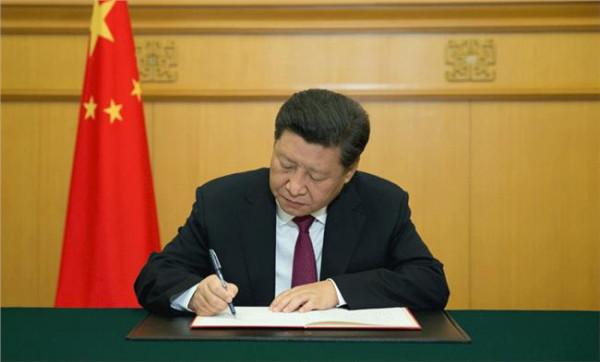








![杨增新碑文 [图文]血溅欢宴:“新疆王”杨增新被刺疑案揭秘](https://pic.bilezu.com/upload/2/47/24746ae64f1ff6f98ad1624709ef2527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