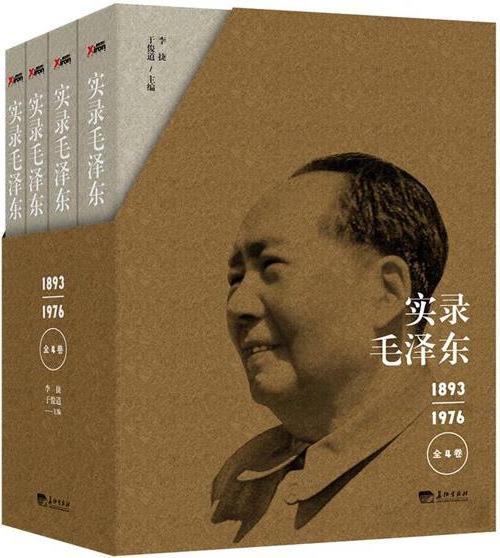朱道来子女 贺子珍寻儿风波朱道来到底是谁的孩子?
编者按:我们刊登这篇文章,决非想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是希望本刊读者阅读此文后,更能体会革命前辈创业的艰辛,以及他(她)们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文/速泰春 徐 育
贺子珍寻子心切
贺子珍,一代巾帼英雄。她是毛泽东的第二个夫人,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
贺子珍于1927年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相识,之后一直跟随在他身后,不久结为夫妻。他们共同生活了整整10个年头,直到1937年分手。
全国解放后,因为身份的特殊,以及可以理解的原因,贺子珍被安排在上海居住。除了几个她身边的工作人员,人们对她一无所知。她几乎和外边的世界隔绝。在上海四川北路溧阳路上一座古老幽静的两层小洋楼里,她寂寞地度过一天又一天,陪伴她的,常常是那些没有生命的与扑克。
当然,她更多的是回顾与思念。
她在与毛泽东生活期间,先后生下5个孩子。1929年,在闽西二打龙岩后,生下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孩子出生不足一月便托付给一位群众大嫂了。3年后,她找到那位大嫂想接走孩子,方知孩子已不在人世。
1932年11月,她在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产下第二个孩子。这是个男孩。当时,她和毛泽东住在一个姓杨的老乡家里。老乡有个儿子,叫大毛。“那我们的孩子就叫小毛吧。”毛泽东抱着新生的儿子对贺子珍说。贺子珍笑着答应了,从此称之为“毛毛”。
第三个孩子出生在长征路上。那是1935年。生下后只有几个小时便送给了当地的老百姓,连名字也没给取一个。除记得是个女孩之外,做母亲的是一无所知。
1936年,长征的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延安。贺子珍生下了她的第四个孩子。仍是个女孩。邓颖超赶来祝贺。她把孩子抱在手中,说:“真是个小娇娇。”从此,大家都叫她“娇娇”。毛泽东则给她取了个名字,叫“李敏”。
贺子珍最后一个孩子诞生在苏联莫斯科。那是她在和毛泽东分手不久出生的。可惜孩子只活了10个月,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5个孩子,只有李敏是在身边看着长大的。解放后,李敏赴京读书,和父亲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了。几年来,贺子珍倍感骨血亲情的重要。身边无子女的孤寂生活只能促使她更加追念过去,还有她失去音讯的孩子们。
最让贺子珍牵肠挂肚的是毛毛。
在幽居上海的第4个年头,她终于忍不住,给江西省邵式平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能帮助她找回失落在江西的儿子小毛。
为革命先辈寻找骨肉,责任重大。邵立即作了安排。但是,几个月过去,半年过去,毫无下落。
只有一条信息使贺子珍稍稍感到宽慰:她当年的战友朱月倩认领了一个男孩。有人告诉她,那孩子很象毛泽东。没准就是小毛毛呢。
寻子心切的贺子珍决定亲眼看一看。她打听到朱月倩和那孩子在南京之后,便赶去了。
当朱道来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忍不住流下了热泪。她捉住孩子的双手,喃喃道:“毛毛,你受苦了。妈妈对不起你……”
朱月倩当仁不让
对党史有所了解的,或许见过霍步青这个名字。霍步青,四川人,1925年参加中国党,黄埔四期学生。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和周恩来一起到上海党中央工作。当时周恩来是中央组织,他是。是党内难得的人才。
1930年党内出了叛徒。霍步青被国民党通缉。党中央原派他去苏联,因秘密交通站被破坏,未能成行,后又决定让他到湘、鄂、赣去,因情况有变,亦未去成。他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努力工作。1932年6月,地下组织又遭破坏,他和妻子以及项英夫妇从险境里逃生,一起转移到江西苏区。先后担任过红军学校政治部、宁清归特委、福建省第三军分区。他的妻子则在瑞金中央军委总政机要科工作。
霍步青的妻子就是前面提到的朱月倩。
朱月倩和霍步青于1927年在上海结婚,正值大革命失败之后的革命低潮里。在上海生活期间,共生下三个女儿。大女儿曾与毛岸英、毛岸青同被安排在一所地下党开办的幼儿园里。
夫妇俩从上海撤离时,上级有令,不能带着孩子,无奈,只得忍痛丢下。当时,三女儿才生下28天。当他们到达瑞金后,设法和上海方面取得了联系,才知道3个女儿均遭不幸。
1933年秋,霍步青在病中遭到敌人的暗算,不幸牺牲。他撇下了朱月倩和一个尚在腹中的孩子。
沉重的打击,使得这个孩子提前问世了。
当时,同志是朱月倩的顶头上司(军委)。对这位不幸的烈士遗孀,小平同志关怀备至。他多次叮咛朱月倩;这儿条件差,如有临产征兆,请提前打招呼,好作安排。
10月5日,怀孕八个月的朱月倩感到身体反应异常,突然晕倒在地。同志得知,立即让身边的三个同志放下手中工作,又招来一个警卫员和一副担架,赶紧将昏迷过去的朱月倩抬起,急匆匆朝医院赶去。中央和红色医院相距20里路,颠簸了半天,刚到医院,朱月倩便生下了孩子。
孩子落地,无声无息。有人以为是个死胎呢。“接生婆”傅连璋在孩子的屁股上连拍数掌,终于听到了微弱的哭声。
由于条件的限制,朱月倩分娩后一直发高烧,常常十几个小时昏迷不醒。住在隔壁治疗的邓颖超大姐时常过来照看,端茶喂汤,无微不至。
朱月倩生下孩子后没有奶水。当时担任总政治部的王稼祥知道后,请了卫生部一负责人帮助找一个奶妈来。正巧,卫生部所在地房东朱盛苔的老婆黄月英的奶孩子刚夭折9天。孩子就这样托付给这对夫妇了。
为纪念霍步青,朱月倩给孩子取名为霍小青。
小青是在朱月倩半昏
这以后直到红军撤离前的8个多月里,离中央20多里之外的朱坊村,朱月倩不知往返了多少趟。她对这一路太熟悉了,那山山水水、花草树木,以及朱家的小宅院……她常常带着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分给干部的食品和衣服送给小青奶妈的一家。尽管少得可怜,但她舍不得自己享用。
1934年夏,由干第5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北上长征。根据中央的决定,陈潭秋、瞿秋白、毛泽覃、项英、陈毅等部分同志留在中央分局。朱月倩也随留下。但是,形势一天天恶化,非常严峻。为保存实力,中央决定再将分局分散,开展游击活动。红军的孩子全部留在当地。
1934年7月的一天,朱月倩最后一次来到朱坊村,她找到奶妈和她的丈夫,把组织的决定告诉他们,请他们把小青带好。为了孩子的安全,他们商量把小青的姓名改为“朱道来”。安排就绪,朱月倩抱起还不到一岁的孩子,深情地亲吻,一下又一下。热泪止不住脱眶而出,流淌在儿子稚嫩的脸蛋上。黄月英站在一边也流下了眼泪。她说:“大姐,你放心吧,我会把小青抚养成人交给你的……”
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过去了整整16年。
在这风风雨雨的16年里,朱月倩辗转各地,最后又回到故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直到全国解放。但是,对远在他乡的儿子,她是一刻也不曾忘记的,始终和瑞金朱坊村保持着联系。还不时寄去一些钱物。
1950年初。朱盛苔领着已长大成人的霍小青来到上海,在空军某部找到了在此供职的朱月倩。他要亲手把孩子还给母亲。
小青已是个17岁的小伙子了。朱月倩盯着他看,目光久久不肯移开。这就是她日夜盼着的小青吗?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霍步青在儿子身上留下的印记是那样深刻,她一眼就看准了:这就是她的小青。
母子相见,是不尽的泪水。
朱盛苔在交还孩子之后,又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介绍信来。这是瑞金地区专员朱开铨写给华东局刘晓的介绍信,上面写着:“介绍霍小青回来其母亲朱月倩处。”他将介绍信递给朱月倩,舒心地笑了,这表示他已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朱月倩凭着这份介绍信,为霍小青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同时,也为朱盛苔取得一份供养报酬和返回江西的路费。
一年后,华东空军迁调南京,朱月倩和儿子一起来宁。霍小青随迁就读于南京华东干部子弟学校。一切都很圆满。失去的骨肉回来了,朱月倩开始领略起幸福生活的滋味了。她由衷地感谢奶妈一家。
她万万没有料到,一场动荡正在等待着自己。
贺子珍和朱月倩曾在一起工作过,彼此姊妹相称,关系相当不错。自从江西一别,两人已有十几年没见过面了。有一天,贺子珍忽然出现在她的家中,令她又惊又喜。
老战友、老姐妹相逢,话题无边。都是做母亲的人了,孩子,自然是她们谈论的重心。
朱月倩很快就看出来了,贺子珍似乎对小青特别感兴趣,问得最多最细。她注意到,贺子珍看着小青时是那样的专注、喜悦、深情。来宁后,她几乎天天走进干部子弟学校,简直看不够。
对这一切,朱月倩并没介意。她理解一个母亲的心,她完全能体会贺子珍的心情。
这年初秋,朱去上海看病,顺便去看望贺子珍。午饭时,贺突然对朱说:“小青到我这里来了,在楼上呢。”朱月倩连忙道歉说:“这孩子真不懂事,您身体不好,怎么好麻烦您呢?”贺子珍说:“话说到哪里去了,麻烦什么?”午餐是在匆忙中结束的。饭毕,贺子珍上了楼。
良久,不见贺子珍下楼来,朱月倩也上去了。
楼上一片沉闷。果然,小青呆坐在写字台前。饭菜依然放着,早已冷了。贺子珍坐在一边没有说话。朱月倩当即批评小青说:“你到贺妈妈家里来,为什么不跟我打声招呼?”
小青没有回答。贺子珍却开了口:“月倩,你来了也好。有件事,我早想跟你说了……”朱月倩不解地看看她,问:“什么事?”贺子珍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小青其实是我生的。我的印象是,你在瑞金时并没有什么儿子啊?”
朱月倩被这突如其来的话打闷了。
好一阵子,朱月倩才回过神来。她说:“子珍,小青确是我的孩子。他是我在瑞金红色医院生的。这事谁都清楚,邓大姐、小平都可作证。如果你是因为喜欢小青的话,我可以送给你……”
贺子珍不说话了。面无表情。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在她雕塑般的面容上打了层暗金色的光彩。
“争儿风波”惊动了中组部
霍小青是住读学生,只有星期天才回家和母亲过。每逢周日,朱月倩总要上街买些好吃的回来。有好看的电影则买上电影票,好让小青在家里能痛痛快快过上一天。
然而有一次破了例,小青未回。
第二天,朱月倩赶到学校去找。
朱月倩心一沉,预感到事情不妙。她立即打电报给华东局,报告儿子失踪的事,请组织帮助在上海找一找。随后,动身赶往上海。
视点集中到贺子珍家。
事情很快就弄清楚了,霍小青果然在贺子珍家里呆着。
华东局的领导感到此事颇为棘手,因为它涉及到的一个孩子和两个母亲,非等闲之辈,各自都有特殊的背景。两位母亲都是革命的有功之臣,为了革命事业,她们几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现在,作为母亲,她们只是想获得拥有一个孩子的权力。这种感情是挚烈的,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受到伤害的。然而,麻烦恰好在这里:两位母亲争执的是同一个孩子。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伤害两颗羸弱的母亲之心。
华东局领导同志对此事非常重视,决定由赵尚志亲自处理。
这位精干的通过方方面面的调查了解,心里已经对“朱道来”的身份有了一个谱,但他仍不肯轻易结论。“只能细心谨慎行事,万万不可马虎大意。”他反复这样叮嘱自己。
他走进了溧阳路上那座静悄悄的洋楼庭院。
此时,贺子珍已经将“朱道来”当年的奶妈黄月英接到了上海。这几天,一向幽静的庭院热闹起来了,贺子珍忧郁的脸上出现了难得的笑容。她将奶妈黄月英当作亲姊妹,也当作贵宾,盛情款待。她详细向黄月英叙述了自己丢失爱子的经过,反复强调孩子托付的所在地就是黄月英的家乡。
她问黄月英,当时的情况还记得不?
黄月英点点头。但没有作答。她是老区来的群众,对眼前这位母亲、这位干部及其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她明白自己的表态举足轻重。
贺子珍更具体地问:“孩子是由两位红军干部和一位地方干部送过去的。你还记得吗?”
黄月英又点了点头,但却是很含糊很不肯定的了。
近一个月时间,她们反反复复议论着孩子的事。
当赵尚志找到黄月英,请她谈谈事情的原委,询问“这孩子究竟是谁的”时,回答竟是那样毫不犹豫,令他吃了一惊。
黄月英说:“孩子是毛的呀。”
这个回答打破了赵原先的论断,从而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尽管他再三提及朱月倩及其证据,黄月英仍不改口。
赵尚志也找到了“朱道来”,但是一问三不知。
赵尚志见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便打电报给江西省邵式平,请求当地协助作进一步调查。任务下达到民政厅朱头上。朱当即派了年轻干部王家珍负责调查了解。
江西方面的调查很快就寄来了。几乎所有的都在证明,“朱道来”是贺子珍的孩子。甚至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的群众联合签名,证实“朱道来”的生母系贺子珍,“朱道来”的小名是“小毛”。还有人提到一件小棉袄,说那是贺子珍亲手缝制留给孩子的,如今小棉袄还在朱盛苔家中呢。
眼前“事实”和预想的越来越远了。赵尚志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难道朱月倩提供的证据有假不成?似乎不象。朱月倩将奶妈所有的来信以及她给奶妈寄钱寄物的收据都保存完好,全提供出来了。其中一封是由奶妈的丈夫朱盛苔写的,再清楚不过了。信中这样写道:“刚解放时不少人来找孩子,有人说小青是朱总的……我说不行,他是朱月倩的……”
为了证实“朱道来”是自己的孩子,朱月倩也同样费尽心力。她向所有了解实情的老首长、老上级、老战友、乡亲们发出了信函。回信基本是一致的,即她确实在瑞金红色医院生下一子,并托付一户群众收养。其中包括同志的亲笔回信:“信中所说在瑞金生一个小孩的事是真的,可以加以证明……”这封于1952年9月的来信及时转交到赵尚志的手中。
精明的赵尚志感到束手无策了,只好将问题上交。当时身任上海的胡立教同志(刘晓已去苏联出任大使)看了所有后认为,这不很清楚嘛!“朱道来”就是朱月倩的孩子。还是做做工作,让孩子回到南京他生母处。可惜,的指示未能奏效。
万般无奈之际,矛盾上交,只有请中央来解决了。于是,奶妈、“朱道来”由赵尚志带领,上了北京。
让中组部来处理一个孩子的归属问题,似乎有点小题大作,但在当时,中组部确实是这样做了,非常严肃、慎重地进行了处理。
中组部委托邓颖超同志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请来了许多了解内情的老同志。邓颖超还特地请毛派自己的秘书前来参加。毛不想卷入这场“争儿风波”,他通过周恩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没有和人家争孩子。”因此没有派秘书参加。
在京期间,不少领导同志前来看望了这个引起争执的孩子“朱道来”。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以及曾碧琦(古柏的夫人)、钱希均(毛泽民的夫人)等“妈妈”们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多次同孩子谈心,关心他的成长。
座谈会开了三天,终于有了结果。邓颖超同志在会上宣布了结论:“朱道来”确系革命烈士霍步青遗孤无疑。
事后,邓颖超妈妈把孩子叫到自己的跟前。她对孩子说:“我和同你爸爸在一起工作多年,你的神态和你爸爸很象,你该弄清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当然也不要忘记养育过你的养父养母。你长这么大,不容易啊。”说着说着,她流下了泪水。
康克清同志后来在回忆这场“争儿风波”给朱月倩写信说:“我们看到小青,人人都说他象你和步青同志,孩子大了,他自己也很清楚他的父母是谁。”
尽管有了中组部的结论,但霍小青却没有返回南京生母的身边。这是因为上海、南京相距很近,况且霍小青已为此事耽误了近两个月的功课。为使孩子安心学习,中组部决定将孩子留在北京就读,并由担任中组部副的帅孟奇具体照顾霍小青的日常生活。
为使两位母亲能理解组织的苦心,帅孟奇副派了专人前往上海和南京,同二人交换了意见,做了细致的工作。
“争儿风波”至此平息下来。
未能实现的美梦
“争儿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然而,风波的中心并没有就此平静无事。
霍小青,这个踏着南方泥土,刚刚走进都市生活的年轻人,做梦也没想到,迎接自己的竟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局面。17岁,一个人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年龄,多少美梦和希望,多少选择和机会在它的面前等待着实现啊。霍小青在激情的漩涡中有点不知所措了,被冲得晕晕乎乎的。
小青留在北京了。他被安排在北京师大南二附中(即后来的101中学)读书。在这里就读的有许许多多革命先辈、先烈的子弟。学校条件优裕、教师尽职尽心。小青走进这个新环境,很快就被吸引住了。他自知文化知识根浅底薄,一心想追赶上去。这一年,他门门功课都居上游,期终考试,平均每门功课在80分以上。
小青既没有和生母朱月倩失去联系,也没有和贺子珍“妈妈”中断关系。还有养育他长大成人的奶妈黄月英,他和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来往。他随时将自己发生的情况向她们汇报,和她们共同分享欢乐,当然,也希望她们能分担委屈与烦恼。
三位母亲继续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每个月,她们都按时给他寄衣服、食品和零花钱。他是班上的“富翁”。零用钱由每月十几元上升到几十元。第三年,他的零用钱已达每月七八十元,和一个18级干部工资水准相当了。
在北师大念书的李敏早已从母亲贺子珍的来信中得知有个叫“朱道来”的“弟弟”已经来京,后来又得知“弟弟”“朱道来”已被判定为别人家的孩子。母亲在来信中常常谈及这个“弟弟”,还给她寄来照片,希望她能和他见面,照顾他。
有机会最好能让爸爸也看一看他。李敏很听母亲的话,她很快就和“弟弟”取得了联系,而且关系也相处得十分融洽。她带着他在北京兜风,买好吃的,向他介绍一切有趣的事儿。“朱道来”很感激,很幸福。久而久之,他真的把李敏作姐姐了。
周围的人渐渐发现,霍小青的身上正在发生着某些变化。那憨厚、笨拙的乡村气息明显褪去,他已经熟悉城市里一切时髦。他会花、肯花,气派十足,当然,他也拿得出。他渐渐和那些父辈职务稍低的同学疏远,和那些出身显赫的子弟们愈发靠近。
1956年的一天,江西的王××给他寄来一封信,信中装有一份群众联合签名的证明,认定“朱道来”就是贺子珍的儿子。霍小青捧着来信,心潮翻滚,他多么希望这是真的。他不再顾及什么了,根据王××的建议,他把自己的姓名改成了“贺雄”。
霍小青私自改名的事很快就被帅妈妈知道了。她很为这件事生气,当即以组织的名义给校长王逸芝挂了,把霍小青的身世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并严肃表示,今后,未经中组部的批准,霍小青的姓名不得随意改变。
不久,朱月倩也知道霍小青改名换姓的事了。她为此苦恼万分,几夜不能合眼。终于她耐不住性子,赶到北京去了。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热情接待了她,专门腾出时间设家宴招待了她。两人竭力安慰她。席间,周恩来对朱月倩说:霍小青就是霍小青,任何人都没有权力改霍小青的名字。当他们回忆在上海共同工作、战斗的不平凡的经历之后,朱月倩告诉他们,她在上海生的三个女儿至今下落不明。周一番感慨,对她说:“你总算找到一个儿子了。”
朱月倩去看儿子,儿子有意回避。当母子相见时,朱月倩已发现儿子和自己拉开了远远的距离。这使做母亲的伤心不已。
霍小青无法摆脱“当毛儿子”的诱惑,他一步步走近这一迷梦,又一次次被敲醒。1964年“四清”运动中,他在一份“自我思想检查”书中坦言说,“我是知道自己是霍步青和朱月倩的孩子,但总觉得当一个烈士的儿子不如当的儿子赫赫有名。”
美梦扰乱了霍小青的心灵,他有意无意地追求起另一种生活方式。和别人相处,冷不丁能冒出“我其实就是毛的儿子”之类的语句。他整天恍恍惚惚,不知如何是好。学习、功课对他再无引力,他时常缺课旷课,还悄悄找了个女朋友闹起对象来,学习成绩开始直线下降。这一年期末考试他没过关,留级了。
1957年,霍小青因在北京公共汽车上耍流氓,被扭送。法律无情,他被判处二年劳教,遣送到黑龙江新凯湖农场劳动。期满后留场工作直到1966年。
1966年初,中组部为照顾朱月倩的生活,将霍小青从东北调回南京,安排在南京工艺装备厂当工人。
此时的霍小青再也不是当年青春年少、单纯可爱的小家伙了。儿子虽然回到了母亲身边,但两人之间已经划上了一深深的裂痕。
“文革”爆发,霍小青活跃起来了。昔日的迷梦又在他脑际盘旋。他常常用手掌将头发向后一抹,问伙伴们:“你们看看我象谁?”然后又问:“象不象毛?”人们弄不清他的底细,只是依稀感到此公来头一定不小。
他对生母朱月倩由不满、怨恨以至发展到仇恨。有一天他竟冲进母亲的住处贴起大字报来,语言之刻,难以想见是儿子针对生身母亲。
命运有时也太无情了。当霍小青的美梦重新浮出脑海的时候,癌细胞悄悄打进了他的肝脏,1971年11月发现时已是“肝癌晚期”了。同年12月,终因抢救无效而一命归西。他只活了38个年头。
18年之后的今天,当笔者面对孤独一身的朱月倩老人,向她提及霍小青短短的,却又不平静的一生时,老人黯然神伤。她说,小青当初有那么好的条件和机会,又有那么多关心他成长的“妈妈”们、叔叔、伯伯、阿姨们,可他不知好歹,不求上进。他当年的同学不少人上了大学,有的还到苏联去留学,多有出息!可他呢……唉……叹息声发自心底,因而显得特别沉重。
老人满头苍苍白发。她指着白得刺眼的头发说:“我的第一撮白头发就是为小青急出来的。”
让历史保持真实
这场风波过去很久了,但并未完全平息。
如果说当年妈妈黄月英违心说假话(经邓颖超同志批评后又说出真相),江西某些人热衷搞什么“群众签名证明”,是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的话,那么,直到近两年还有人泡制《为贺子珍寻儿记》之类文章,颠倒事实真相,就更令人难以理解了。
这篇文章1987年7月刊于江西某杂志。文内硬说朱道来是贺子珍的骨肉,说毛看了朱道来的照片,也认为很象年轻时的毛泽覃。正当贺子珍母子相认时,半路出的“程咬金”(即朱月倩)使朱道来的身份发生了分歧,云云。
这篇文章轰动一时,几经报刊转载。许多不明真相的人,为朱道来曲折坎坷的历史深表同情,对那个半路上出的“程咬金”表示不满。这等于给一生坎坷的朱月倩老人受伤的心灵上又插上了一。她气愤难平,于1988年3月致信邓颖超大姐,信中说:“……文章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竟要翻案,无中生有地说霍小青是贺子珍的亲儿了,而我这个亲生母亲反被骂成‘半路上出的程咬金’,对此事,我气愤又百思不解,给贺子珍写传,为什么要中伤我?何况贺本人也未这样。
我一生坎坷,到晚年还受此侮辱,心里很难受,我该怎么办?……”
邓大姐很快给朱月倩回信了。随信还附有一份致那家杂志的函件,要求杂志尊重事实。
然而,很长时间过去了,对方没有反应。对此,81岁高龄的朱月倩老人连呼:“不理解,不理解。”
笔者在采访朱老时问过一个不大适宜的问题:“如果您默认霍小青是贺子珍的儿子的话,将会有何后果?”
老人说:“那就不会有这场风波。但是,这样做我的情感会受不了。在子女问题上,我和贺子珍有相同的不幸,我们也就有相同的要求。我和她有同样的作为一个母亲的权力。虽然在实际上,小青已不在我的身边,甚至后来犯错误劳教去了,再说他后来和我的感情也不好,可我还是要说,他是我的孩子。”
这或许是一个母亲的心声。
“历史就是历史,试图为了某种历史而改变另一种历史,这是错误的。”朱月倩老人又说,“现在小青已经过世,他的一生也无多少值得我夸赞的,留念的,但他仍是我的儿子。他是历史真实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