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如何做哲学 杨国荣 | 如何做哲学
摘 要: “做哲学”的方式在哲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多重形态。在实质的层面,哲学之思展开为对智慧的追求,后者体现为以人观之和以道观之的统一。以人观之意味着从人的现实存在境域和背景出发,以进入人的知行之域为研究和追问的对象;以道观之则意味着跨越知识的界限,贯通存在的不同方面,把握世界的整体,并追问人和世界中的本源性问题。
在形式的层面,哲学之思作为以理论思维方式来把握世界的过程,又表现为“运用概念”的思维活动。
哲学思想凝结在概念之中,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也通过新概念的提出而实现。今天的哲学思考还需要回到存在本身。所谓回到存在本身,意味着既要杨弃囿于语言逻辑的分析哲学,又要扬弃囿于意识领域的现象学,进而回到具体的、现实的存在本身。哲学之思同时涉及理论与经验、知识与智慧的互动。
关键词:做哲学;以人观之;以道观之;回到存在本身
如何做哲学?这一问题涉及哲学研究的方式和进路。哲学在考察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由之“如何做哲学”的追问与“何为哲学”的省思也彼此相关。历史地看,哲学在其演化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学科性和超学科性双重品格。
按其内在规定,哲学以追寻智慧为指向,从而不同于旨在达到特定知识的具体学科。但近代以后,随着哲学融入分科化的教育系统,它也渐渐地衍化为某种专门之学,并在一定意义上具备了学科化的形态。哲学的双重品格,既关乎对哲学的理解(何为哲学),也涉及哲学研究的方式(如何做哲学)。
在取得学科形态之前,哲学的研究和思考过程与哲学家的生活过程往往相互交融。无论是先秦时代的孔子,还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其哲学思考和生活过程都呈现彼此重合的特点。对于这一时期的哲学家而言,哲学的探索和日常的生活实践难以截然相分,以中国哲学的观念来表述,即“为学”与“为人”无法分离。
此所谓“为学”,包括广义上的智慧追求或哲学探索,“为人”则涉及具体的践行过程。孔子很注重“为学”,《论语》首篇《学而》就从不同方面讨论有关“学”的问题,其中的“学”也关乎智慧追求。
对孔子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学”(包括广义的智慧追求)并不是闭门思辨的过程;如果个人能够做到“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便可以称之为“好学”。
“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属于具体的做事或生活过程,以此为“好学”,表明包括智慧追求的“好学”过程融人实际生活中的“为人”过程。按孔子的理解,一个人只要对相关的人生理念身体力行,并实际地处理好各种人伦关系,则“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从如何“做哲学”的视域看,以上观点意味着对宇宙与人生智慧的探索展开于多样的社会生活过程之中。
近代以后,哲学进**学的教育系统,成为诸多学科中的一种。哲学曾被视为科学之母,但到了近代,各门学科逐渐分化出来。与这一分化过程相伴随的,是知识与智慧之间愈益明显的分野。在学科没有分化之前,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区分往往隐而不彰;但是随着学科的分化,两者之间的区分便逐渐显性化。
分化的各种学科主要关乎知识领域,与之相对的则是智慧之域。从实质的层面看,近代哲学在取得学科形态的同时,又进一步展现了哲学作为智慧之思的品格,并以此区别于分门别类的知识进路。
从形式的层面看,哲学在取得学科形态之后,往往更为自觉地表现为运用概念来展开思维的过程。这种概念性的活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它可以是对概念的理性化运用,与之相应的是逻辑层面的思维活动,如在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近代哲学家那里,概念的运用与逻辑思维的过程联系在一起;它也可以以非理性化的方式展开,哲学史上的直觉主义、意志主义等往往就是以非理性的方式运用概念。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直觉主义、意志主义固然不同于理性主义,但却依然离不开概念的运用,如作为意志主义代表人物的尼采便提出并运用了“权力意志”、“永恒轮回”等概念;在柏格森这样的直觉主义者那里,则可以看到“绵延”、“创造进化”等独特的哲学概念。
即使哲学论域中的神秘主义,也并非与概念完全分离。按照罗素的说法,神秘主义的特点在于拒斥分析性的知识,强调“不可分”与“统一”。这个意义上的神秘主义固然常常与个体性的体验、领悟、感受等相联系,但当它作为哲学共同体中的一种形态而呈现时,也要诉诸于某种概念,如“大全”、“太一”等。
当然,直觉主义、意志主义和神秘主义总是试图与理性保持某种距离,其概念的运用也有别于逻辑的推绎,并与直觉、意志以及神秘体验等非理性的规定联系在一起。
概而言之,在取得学科形态之后,哲学一方面在实质层面上越来越呈现出以智慧追求为指向的特点,另一方面在形式层面上则更为自觉地表现为运用概念而展开的理论思维活动。以上趋向当然并非仅仅存在于近代以来“做哲学”的过程,在取得学科形态之前,哲学探索同样关乎以上方面。
但是在传统的形态中,“实质层面上的智慧之思”和“形式层面上的概念的活动”这两个方面往往与哲学家的生活过程融合在一起,从而,与之相关的“做哲学”方式与哲学取得学科形态之后也有所不同。
就当代而言,哲学的进路呈现出不同的趋向。首先可以关注的是20世纪初以来的分析哲学,其特点在于将语言的逻辑分析作为“做哲学”的主要方式。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哲学进路所强化的,乃是哲学作为概念活动这一形式层面的规定。
由此,它进而倾向于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作为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20世纪以来另外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潮是现象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从实质的层面上强化了“哲学作为智慧之思”这一规定,这种强化同时又与突出“意识”联系在一起:相对于分析哲学之关注语言,现象学更加注重意识。
尽管现象学的奠基者胡塞尔早期以所谓反心理主义为旗帜,但现象学实质上始终是以意识为本的;从意向性到本质的还原、先验的还原,再到纯粹意识、纯粹自我等现象学的观念,都与对意识的考察相联系。
胡塞尔追求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这需要以确立最本源的根基为前提,这种根基具体表现为通过本质的还原、先验的还原而达到的纯粹意识或自我意识。对胡塞尔而言,“纯粹意识”或“纯粹自我”既具有明证性,又呈现出直接性:它没有中介,不可再加以追溯,从而表现为最原始的基础。
可以看到,现象学的进路基于对意识的关注,而与意识相联系的,则是智慧之思的思辨化、抽象化趋向。如果说,分析哲学从强化形式层面的概念活动出发而导向了实质层面智慧之思的弱,那么,现象学则由赋予意识以本源意义而使智慧之思趋于抽象化、思辨化。
在更宽泛的层面,从当代哲学中同时可以看到智慧的知识化趋向。(1)以时下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智慧的知识化往往表现为研究的还原,即哲学的研究还原为哲学史的研究,哲学史的研究进一步还原为思想史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最后还原为学术史的研究;被还原的研究又主要关乎文献的疏证、史实的考察,等等。
这些还原的直接后果,是哲学的思辨消解于历史的考辨,与之相应的则是智慧之思的退隐。(2)智慧知识化的另一种表现是“道”流而为“技”。
以疏离形而上学为总的背景,向具体的知识性学科趋近,成为哲学研究中的一种进路,后者的关注点往往指向经验领域的各种特定问题,如基因、克隆、人工智能等。哲学固然需要关注现实及其变迁,但如果主要限定于特定的领域和对象,则又难以使“向道而思”的智慧旨趣与经验层面的技术关切真正区分开来。
以上考察从不同方面展现了哲学之思的历史进路,它们同时构成了今天思考“如何做哲学”的前提和背景。哲学的形态当然可以具有个性化特点,哲学的探索也可以展现不同的风格,但从普遍的视域和方式上看,“做哲学”总是涉及若干基本的问题。
1、“以人观之”和“以道观之”
“以人观之”既关乎所“观”的对象,也与“观”的主体相涉。哲学的追问指向人和人的世界。所谓人和人的世界,具体而言就是进入人的知、行领域中的存在,后者不同于本然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也非与人完全不相干的洪荒之世。
就“观”的主体而言,“以人观之”表现为“人”之观,这一意义上的以人观之,既有别于以宗教论域中的上帝之眼来看存在,也不同于以人之外的动物来考察世界。一方面,宗教论域中的上帝被赋予绝对、超验的性质,人则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绝对者,也并非如宗教所理解的上帝那样全知全能。
人无法像上帝那样去理解世界,只能从自身出发去考察这个世界。另一方面,从人的视域理解这个世界,也区别于以动物的眼光去看外部存在。动物的特点之一在于受到自身物种的限制:每一种动物都归属于某一类的存在,并受到它所从属之物种的限制而无法超越。
尽管目前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动物的权利、动物的解放之类的提法,似乎动物可以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但事实上,所谓动物的权利、动物的解放并未超出以人观之;按其实质,这是人从自身的角度赋予动物以某种地位。
换言之,这是人给动物立法,而不是动物自身为自己展现一幅世界图景。总之,人既不是以上帝之眼去考察存在,也不是以动物之眼去看世界,而是从人自身的存在境况出发去理解这个世界,这种存在境况包括人的需要、人的能力、人的历史发展以及这种历史发展所形成的社会背景。
以上述背景为前提去理解和考察世界,即具体展现为“以人观之”的过程。从根本上说,本然的存在、自在的世界并没有意义,意义乃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意义的生成也与人自身的知、行过程无法分离。人对世界意义的认知,归根到底基于人自身的视域。
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既表现为“以人观之”,又展开为“以道观之”。“以道观之”意味着没有停留于经验的层面,而是源于经验又升华于经验。与之相联系,对世界的这种把握方式也不同于知识层面的理解。知识总是指向世界的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并有自身特定的对象和界限;哲学作为具有超学科性品格的思想形态,则以对智慧的追寻为其内在旨趣。
哲学对智慧的追寻表明,哲学无法(也不会)将自己的研究或探索限定于某一特定对象和领域,而总是试图把握不同事物或领域之间的关联,并追求对世界的整体性的理解。
在这方面,“做哲学”的过程展现了不同知识性或经验性的进路。从存在之维看,在真实的世界被知识划分为不同领域和对象之前,其本身是统一的和相互关联的;由此,把握真实的存在不能仅仅限定于彼此相分的状况,而是需要进一步把被知识分离开的方面沟通起来。
作为哲学视域的体现,“以道观之”也意味着追问人和世界中那些具有本源性的问题。科学追求“真”,哲学则进一步追问“何为真”、“如何达到真”;道德追求“善”,哲学则进一步追问“何为善”、“如何达到善”;艺术追求“美”,哲学则进一步追问“何为美”、“如何形成审美的意识”,如此等等。
就人的日用常行而言,其形态主要表现为人的实际生存过程,哲学则进一步追问这种生活过程的意义以及如何达到理想的人生;日常生活中的人对人生意义往往“日用而不知”,一旦人开始自觉地反思生活的意义,哲学的意识便开始萌发。
概而言之,“做哲学”需要有大的关怀,从传统论域中的“性与天道”,到今天面临的“社会正义”,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都应当成为哲学关注的对象。如果仅仅停留在技术性的关切或特定的知识经验之上,那么哲学便会自限于具体学科的层面,其作为智慧之思的意义亦将不复存在。
把哲学加以知识化、技术化和应用化,从对象的角度看意味着存在的碎片化,从哲学的层面看则意味着智慧的消解。“以道观之”所要克服的便是此种倾向。中国哲学很早就提出“下学而上达”的要求,其中亦涉及以上视域:“下学”关乎对世界的知识性、经验性理解,“上达”则意味着由日常的经验知识,进一步引向对“性与天道”的终极性关切。
作为“做哲学”的两个方面,“以人观之”与“以道观之”并非相互隔绝。所谓“以道观之”,归根到底乃是人自身“以道观之”。“人”一方面从自身出发去考察世界,另一方面又努力以“道”的视域去理解世界。正是人自身在广义的认识过程中不断跨越知识的界限,追问世界中的本源性问题,由此实现了“下学而上达”。
2、理论思维与概念性活动
“以人观之”和“以道观之”的统一,主要在实质的层面体现了哲学之思的特点。从形式的层面看,哲学又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把握世界。理论思维方式具体表现为运用概念的活动,即以概念活动为形式,赋予哲学以不同于艺术和科学的特点。
艺术首先借助于形象,科学主要基于实验和数学的运演,哲学思想则凝结于概念。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或者通过新概念的提出而实现,或者通过对已有概念的重新阐发而展现出来。德勒兹曾指出,哲学首先表现为概念创造的过程。
哲学作为运用概念而展开的理论思维活动,首先涉及概念的生成和辨析。概念的生成可以取得两种形式:其一是“新瓶装新酒”,也就是通过新的概念的提出以表达新的思想,比如庄子提出“齐物”之论,便是以新的概念阐发其形而上及认识论方面的独特思想;其二为“旧瓶装新酒”,也就是通过对已有概念的阐发来发展某种新的哲学观念,比如尽管“仁”在《诗经》、《尚书》中都已出现,但孔子却通过对“仁”的创造性阐发提出了新的哲学思想。
另外,与概念生成相关的是概念辨析,后者主要表现为对概念的界定和解说。
哲学的概念不能停留于模糊、混沌的形态之中,需要有确定的界定,唯有如此,才能既成为哲学共同体中可以批评、讨论的对象,又能够在实质的层面展现思想的发展。
除了概念的生成和辨析,概念性的活动还体现于观点的论证。宽泛而言,观点的论证过程也就是说理的过程。哲学在实质的层面表现为对智慧的追寻,在形式的层面则离不开说理。缺乏智慧的内涵,说理将导向空泛的语言游戏或纯然的逻辑论辩;悬置说理的过程,智慧之思则容易流于独断的教条或个体性的感想。
在哲学领域,提出一个观点需要加以论证,并提供相关观念之所以成立的根据。中国哲学家很早就提出,论辩过程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同时也是哲学作为概念活动的基本要求。哲学不应当是独断的教条,也不能仅仅表达个人的感想和体验;不仅其立说需要经过论证,而且在回应不同意见或批评时,也应有理有据。
需要指出的是,概念性的思考不能等同于抽象的思辨。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概念本身可以区分为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如果所运用的概念包含具体规定,那么与之相关的思考过程便具有现实的内容,而不能简单地归入于抽象的思辨。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倾向:把具体的形象性叙事和概念性思考对立起来,以经验性的品味代替概念性的思考,赋予想象的诠释以优先性,并专注于所谓“古典生活经验”或 “古典思想经验”,等等。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不仅仍流于前述的思想还原(“古典生活经验”或“古典思想经验”均未越出思想史之域,哲学则相应地被还原为哲学史和思想史),而且在更实质的意义上表现为疏离于概念性的思考。
对概念性思考的这种疏离,在逻辑上往往可能导向哲学的叙事化和文学化:哲学本身成为一种思想的叙事,而修辞则可能由此压倒对现实世界和观念世界的理论把握。
哲学当然也关乎叙事和修辞,但叙事和修辞不应当取代通过概念而展开的思与辨,否则哲学就可能流于抒情性论说或哲理性散文;后者确实可以带来某种美感,但它们提供的也仅是想象性的文学美感,而无法使人从智慧的层面或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理解世界和人自身。
3、回到存在本身
哲学以把握世界为指向,“回到存在本身”首先体现了哲学的这一基本使命。就当代的哲学思考而言,这一要求又以20 世纪以来的哲学衍化趋向为背景。如前所述,20 世纪主流的哲学思潮是分析哲学。以语言的逻辑分析为主要取向,分析哲学在关注语言的同时,往往又将视野限定在语言的界限之中,不越语言之“雷池”一步。
这一意义上的概念的分析,常常流于形式化的语言游戏。分析哲学**惯于运用各种思想实验,这些思想实验往往并非从现实生活的实际考察出发,而是基于某些逻辑设定(tosuppose),作各种抽象的推论,从而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远离现实存在的语言构造。
当哲学停留在上述形态的语言场域时,便很难达到真实的世界。以此为背景,“回到存在本身”首先意味着走出语言,回到语言之后的现实存在。
哲学当然需要关注语言,语言分析的重要性也应予以肯定,但不能由此囿于语言之中,把语言作为与存在相隔绝的屏障。语言应该被视为达到存在的途径和工具,“回到存在本身”意味着不再将语言作为终极的存在形态,而是通过语言走向真实的世界。21世纪哲学的未来发展,将表现为不断地超越“语言中心”的观念。
“回到存在本身”中的“存在本身”,不同于现象学所说的“事物本身”。现象学曾提出“回到事物本身”的口号,“回到存在本身”似乎容易混同于此。然而,从实质的方面看,这里所说的“存在本身”与现象学论域中的“事物本身”在内涵上相去甚远。
现象学所说的“事物本身”,在终极的意义上与经过本质还原、先验还原而达到的所谓“纯粹的意识”或“纯粹自我”具有相通性,这一意义上的“事物本身”并不是现实世界中的真实存在【1】。在当代哲学中,如果说分析哲学侧重于语言,那么现象学则始终把“意识”作为根基,早期胡塞尔便试图使哲学成为“严格科学”,其具体进路即是从意识入手。
哈贝马斯曾区分了20世纪以来的两种哲学形态:其一为语言分析哲学,这种哲学主要存在于从弗雷格到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衍化过程之中;其二则是意识哲学,现象学是其重要代表。这一看法也有见于现象学与意识的关联。
从中国哲学的演进看,宋明理学往往较多地关注“心性”之域,当代新儒家则提出由内圣开出外王,其中也蕴含以“心性”(内圣)为本的趋向。可以说,从理学到当代新儒家,“心性”构成了其核心的方面;只是在关注“心性”的同时,他们也往往表现出限定于“心性”的趋向。
晚近的哲学中还可以看到“情本体”论,尽管这一理论的哲学基本立场与理学及当代新儒家存在重要的差异,但就其将作为精神世界的“情”提到本体的位置而言,“情本体”论似乎也表现出强化意识的趋向,这与“心理成本体”的主张在理论上彼此呼应。
以人和人的世界为指向,哲学当然离不开对意识和精神世界的考察,但却不能如现象学、心性之学那样,仅仅停留在心性、意识的层面之上。21世纪的哲学既需要走出“语言中心”,也需要扬弃“意识中心”,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对分析哲学和现象学的双重超越。
那么,哲学应该回归的“存在本身“”究竟所指为何?概而言之,“存在本身”就是具体的、现实的存在。儒家曾有“本立而道生”(《论语·学而》)之说,其中包含十分重要的观念。此处之“道”,可以理解为哲学的智慧,“本”在引申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存在的具体形态或现实形态。由此,“本立而道生”表明了哲学的智慧和存在的具体形态密不可分:前者(哲学的智慧)基于后者(存在的具体形态)。
存在的具体形态体现于对象和人自身两个方面。其一,就对象而言,世界本身表现为道与器、理与事、体与用、本与末之间的统一;进而言之,这种一并不仅仅呈现为静态的形式,而且同时展开为一个过程。正是道与器、理与事、体与用、本与末以及过程与实在的统一,构成了对象意义上的真实存在或“存在本身”的具体形态。
从历史上看,哲学家们往往主要关注或突出现实存在中的某个方面,如经验论者较多地强调“用”、“器”、“事”,理性主义者则更多地突出“体”、“道”、“理”。
问题在于,在片面突出某一方面具体形态之下,存在本身或真实的存在往往会被遮蔽起来。其二,就人自身而言,其存在具体表现为“身”、“心”、“事”多方面的交融。“心”涉及的是综合性的精神世界,这里需要特别关注其“综合性”,它包括知、情、意和真、善、美的统一,以及个体能力和境界的互融。
“身”既表现为有血有肉的感性存在,又是渗人了理性的感性,体现了具有社会性的个体性,这个意义上的“身”不同于生物学视域中的躯体。
“事”在中国哲学中一方面与“物”相对而言,并与实践、行动相关联,所谓“事者,为也”(《韩非子》);另一方面“事”又不同于自然对象而表现为社会领域中的具体存在,可以视为社会实在;两方面意思综合起来,“事”具体表现为社会实践和社会实在的统一。
在人类思想史上,心性之学主要突出的是人在精神世界方面的规定,即人之“心”;主张“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经验主义以及当今所谓的“身体哲学”、“具身知识论”等,常常强调的是人之“身”;现代实用主义、行为主义则更为关注人的存在中的“事”之维。
以上哲学流派固然都涉及到了人的存在中的某一方面的规定,但对“心”、“身”、“事”的统一,则未能给予充分的关注。
要想真实地探究人本身,便要回到人的存在本身,即从“心”、“身”、“事”的关联和统一去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而不能仅仅关注其中某一个方面。事实上,传统哲学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荀子曾对“学”作了多方面的考察,他所理解的“学”既在广义上包括智慧追求的过程,也与人自身的存在相涉。在荀子看来,“君子之学”的特点在于“人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荀子·劝学》)。“人乎耳”突出了感性的通道,“著乎心”关乎广义上的精神世界,“布乎四体”涉及人之“身”,“形乎动静”则表现为人的做“事”过程。
按照以上理解,与人相关的“学”,总是涉及“心”、“身”、“事”多重方面;推而言之,对人自身存在的具体把握,也无法离开这些方面。
4、史与思
从内在的思维过程看,哲学研究既涉及哲学的历史,也关乎哲学的理论,与之相关的是史与思的交融。一方面,今天被作为哲学史对象来考察的哲学系统,最初是历史中的哲学家所形成的创造性理论,(孔子的儒学系统,便是孔子在先秦时期所建构的哲学系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他们在古希腊时期所建构的理论体系),这些思想系统首先是哲学的理论,尔后才逐渐成为哲学的历史,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另一方面,任何新的哲学系统的形成,都是基于对以往人类文明及其文化成果的反思和批判。
如孔子思想的形成,无法与他整理“六经”以及更广意义上对殷周以来文化发展成果(包括礼乐文明)的把握和反思这一背景相脱离;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思想系统的形成,也无法摆脱他们对前苏格拉底思想的反思和批判性总结。
就现代哲学而言,冯友兰“新理学”系统的形成,同样无法与其哲学史的工作相分离;海德格尔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哲学家,对康德、尼采甚至是前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都进行了深刻的理解和阐释,其思想的创造也离不开对以往思想成果的把握。从这方面看,即便真正有创造性的哲学思考,也无法离开历史中的思想积淀而凭空产生。
引申而言,哲学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其“问题”往往“古老而常新”,在这方面,哲学与科学之间亦呈现差异:科学的问题往往具有相对确定的答案,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解决并有了确定答案的问题,很少再被提出来加以讨论;在哲学领域,关乎哲学思考的问题很少有一劳永逸的确定性答案,先秦、古希腊哲学家讨论的问题,今天我们依然在讨论;每个时代的哲学家也往往站在他们所处的特定背景之下,对历史中的问题作出新的理解和回应。
“问题”的这种历史延续性,也从一个方面展现了哲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理论之间的相关性、互动性。以上事实从不同方面表明,创造性的哲学研究总是无法离开史与思之间的互动。
5、理论与经验、智慧与知识的互动
哲学固然以理论思维为形式并表现为对智慧的追寻,但并非隔绝于经验和知识。事实上,理论与经验、知识与智慧之间总是展开为互动的过程;其中,知识与智慧之间具体呈现为“技进于道”和“道达于技”的统一。“技进于道”意味着在理解世界的过程中,知识升华为智慧;“道达于技”则展现为哲学的智慧运用于对经验世界的理解和变革,这既使智慧在具体的知、行过程中得到确证,也使知识得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由此,理论和经验、知识和智慧扬弃了彼此的分离。
从具体的哲学思考来看,知识和智慧的互动同时表现为“大处着眼”和“小处入手”的交融。如前所述,哲学需要有大的关怀,并进行本源性的追问,但是,这一过程不能流于泛泛的空论和抽象的思辨,而应当从现实存在出发,并通过对“事”与“理”的具体考察和缜密分析而展开。忽略“大处着眼”,将导致智慧的遗忘;无视“小处入手”,则容易引向智慧的抽象化。
知识与智慧的互动,同时表现为理论与现实世界、现实生活之间的交融。理论既需要基于现实、关注生活,也应当规范现实、引导生活。从知识与智慧的关系看,智慧一方面跨越知识的界限,另一方面又不能游离于知识之外。智慧的沉思如果不基于各学科形成的多样的认识成果,往往会流于空疏、思辨、抽象。
与知识经验相关的具体对象,还包括社会存在。一般而论,哲学的发展有两重根据,一为观念的根据,二为现实的根据。前者包括多方面的思想成果,后者则首先展现为社会存在。
哲学思考需要对社会发展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也需要对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引导和规范,此两者都涉及哲学和现实存在之间的关系。对后者的关注同样也构成了今天哲学思考的重要方面。
当然,从哲学的层面关注现实,应避免流于庸俗化。哲学对现实的关切和引导,并不表现为提供具体的操作性方案,这种关注乃是通过理论思维的方式而实现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这方面便提供了值得注意的范例。该书形式上虽然非常思辨,但在实质的方面却涉及很多具有现实社会内涵的问题,如其中讨论的主奴关系,便折**现实的社会关系,并构成了当今政治哲学讨论“承认”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可以看到,哲学家乃是以他们独特的方式体现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而并非简单地提供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提供某种技术性、操作性的方案,往往涉及实证性、经验性的活动,后者与哲学之思具有不同的规定。
要而言之,一方面,创造性的哲学思考无法离开知识经验与现实存在;另一方面,知识与智慧的互动又并不意味着将理论思维的方式还原为经验科学的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基于现实与规范现实的统一、关注生活与引导生活的统一,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在更高的层面上回到传统哲学所注重的哲学探索和生活过程的统一、为学和为人的统一。当然,这是经过分化之后的回归,其中蕴含着对说明世界与规范世界双重哲学向度的肯定。在此意义上,古典哲学不仅是吸引我们向之回顾的智慧之源,而且其“做哲学”的方式也是一种可以在更高层面向之回归的形态。
(《哲学动态》2016年第6期)
本文内容基于作者2015年12月在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年会上的发言;相关研究被纳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冯契哲学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15ZDB012] 。
注释【1】 参见杨国荣:《哲学的视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92-39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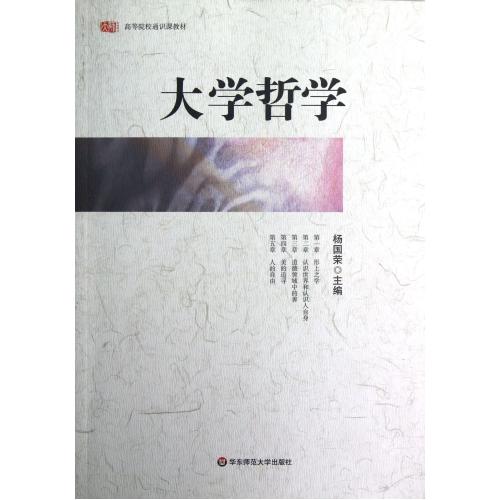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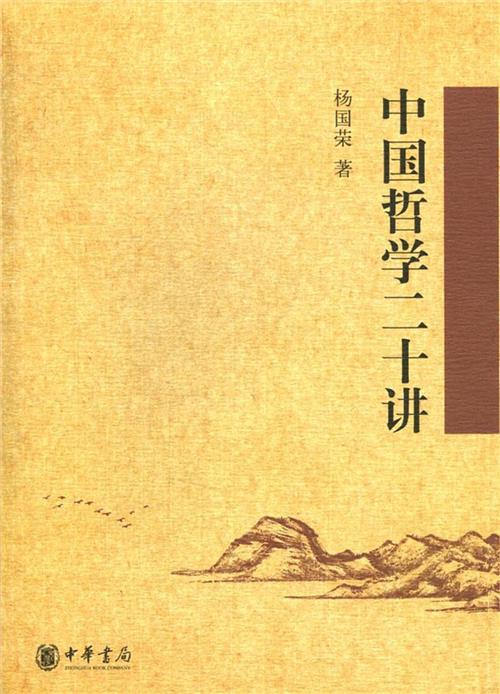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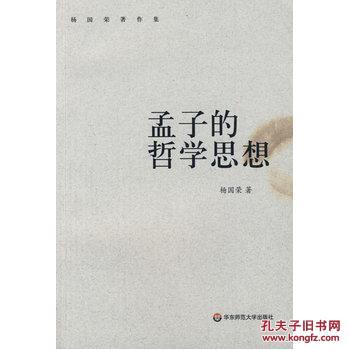





![杨开慧的父亲 杨开慧怎么死的 杨开慧的悲壮事迹 [趣闻]](https://pic.bilezu.com/upload/8/40/84061bc395d777b00fde952ab9958a2b_thumb.jpg)



![>[视频]窝窝 杨国强>>杨国强几个孩子>>杨国强的女儿](https://pic.bilezu.com/upload/c/9f/c9f92a43cca584977d678f599aaed38b_thumb.jpg)






![>[视频]窝窝 杨国强>>杨国强几个孩子>>杨国强的女儿](https://pic.bilezu.com/upload/3/dd/3dd1a9796882b05bf8ac9286fa199c04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