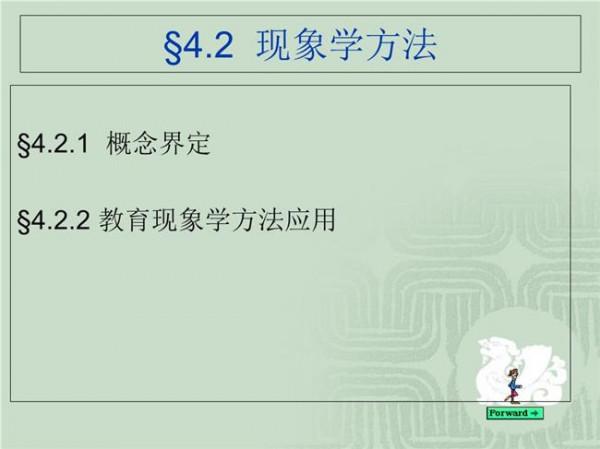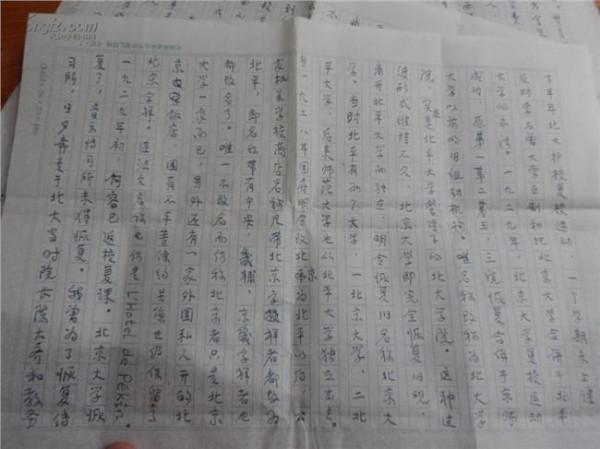刘良华现象学 刘良华:从“现象学”到“叙事研究”
1994年,我第一次接触“现象学”。那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有一位同学,叫赵哲。赵哲身体强壮,喜欢看哲学书,偶尔写一些诸如“毕业后我们都会走散,我去找你时,你不要逃走,做一条光身子的鱼”之类的歪诗。我以为喜欢看哲学书喜欢写诗的人身体都比较弱小,赵哲是一个例外。
在我们那一届,赵哲是聪明、好学而剽悍的学生,我们视之为“老怪物”。他也有弱点,就是不善于和女人打交道。他一遇到他喜欢的女孩子就使劲地跟她谈论哲学和诗歌,把女孩一个一个吓得都远远地躲着他。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赵哲在西南师范大学杏园(研究生宿舍在杏园)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到了星期五的晚上,他常常会黯然伤神。他说他平生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在他还没有找到如意女郎的时候他的同寝室的那个人竟然把女朋友带到寝室来谈天说地而且那个男的如此猥琐那个女的竟然什么都不在乎。
他黯然伤神的时候,就有可能拐到我的寝室来找成就感。他其实并不了解我,只是因为我经常对他不以为然,说他“不懂装懂”又说“你懂的我都懂”,他就一定要找我来证明他的实力。
有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他特意拿来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他说我随便找一句海德格尔的话,就把你弄糊涂了,你信不信?我当然说不信。
他就说不信你就试试看?我说你把书合上然后随便打开一页指定一行看你如何能把我弄糊涂? 他真的把书合上然后随意打开一页找出一行:“存在是自明的概念。在一切认识中、一切命题中,在对存在者的一切关联行止中,在对自己本身的一切关联行止中,都用得着存在。
”([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5页。) 他问:“你说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还不明白,这句话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存在是一个自明性的概念。
既然是自明性的概念,就不必解释,本身已经很明白。海德格尔自己都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话,不需要解释,你竟然还要我解释这句话,海德格尔要是知道了你这样胡闹,他会骂死你。
” 他很生气,发誓不再跟我谈海德格尔。 等他走后,我就开始一个人安静地读《存在与时间》,并做了一大堆零碎的阅读笔记。书是读了但没有读完,笔记也做了但经常被海德格尔的奇特的话语方式弄得晕晕忽忽的。
我对《存在与时间》有很多好感,这符合我的“好感”标准,凡是得不到的总会有很多好感。但当时感觉海德格尔的话语无法用到我的专业研究上。后来就几乎放弃了对这本书的阅读。 1997年,因为那段时间经常做一些事务性的、很现实的工作,比如拿发票到财务处报帐,拿电脑到设备处登记“固定资产”等等,感觉生活没有了“自由”没有了“想象”。
人好像有一种本性:做“有用”的事情太多了就想做一些“无用”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太长久了就希望过一种“想象”的生活;听“日常”的话听得太厌烦了就想听一些“陌生”的词语。
于是忽然有一天开始怀念起海德格尔的书来。海德格尔的书可能没什么用,但正因为“无用”才让人感觉自由;海德格尔的建议可能太过于想象,可是人只有凭借想象才有可能把自己从现实的无聊中拯救出来;海德格尔的话语可能太新奇太喜欢炫耀甚至有些自恋,但正因为新奇才让人重新有陌生感。
当天晚上就到中山大学西门口的“学而优书店”买了一本《存在与时间》。
买回来之后也没有读多少,但感觉自己的灵魂好像重新恢复了自由,感觉自己的现实生活与想象生活有了一个交界的地带。 1998年,我再次进入学生生活。在上海的那几年有事没事就去逛书店,书店里不断推出有关现象学的书,我的书架上也开始有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和伽达默尔等人的译本。
我再次开始阅读《存在与时间》,那段时间老师要求我们读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我把更多的时间放在阅读《存在与时间》上。
听杜威谈《民主主义与教育》时,感觉杜威说了一堆大白话。听海德格尔谈《存在与时间》时,感觉海德格尔说了一串串诗情画意的废话。虽然是废话,却又诗情画意,于是我就拿它来与同学“高谈阔论”。
有一天晚上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楼停电,我们五六个人正好从外面喝酒回来,我带头高唱《回到拉萨》的开头几句兴致勃勃地回寝室高谈阔论海德格尔。 我说:海德格尔是读不明白的,他也不希望我们把他读明白。
他就喜欢故弄玄虚,弄得你似懂非懂。要是我们把他读明白了,他会生气的。有谁能说把海德格尔读明白了? 我说这些话其实也只是一时的感觉,信口说说,并没有多少根据。没想到有人把话传到一位老师那里,传过去的话是:“刘良华说,某某老师根本不懂海德格尔”。
这句谣言曾经让我和那位老师之间弄得很不愉快。 我的老师曾经问我“你是不是说了那样的话?”我说:“我说过!”老师后来又问:“你真的说过那样的话?”我说:“只有白痴才说那样无聊的话。
” 我今天把这件事写出来,算是“海德格尔”给我制造的一件麻烦。 因为看海德格尔的书,也就很自然地开始看他的老师胡塞尔的书。 读胡塞尔的书,比读海德格尔的书更容易让人震撼。 我甚至不知道胡塞尔究竟说了些什么,反正从一开始就感觉受到震撼。
我一直想:要么胡塞尔是天才,要么胡塞尔的书是“皇帝的新装”。 在没有看明白之前,我宁愿胡塞尔是天才。 具有天才气质的人,常常有“怀疑”的精神。
胡塞尔显然有这个精神。他比笛卡儿更加有“怀疑精神”。 具有天才气质的人,常常会引导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曾经引导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今次胡塞尔的气势是再次引导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我关心的问题是:胡塞尔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究竟是什么? 现象学一再申明自己要反对“自然的观点”,也就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的研究态度。
但现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又如此一致地关注“事实”,现象学也是一门“实证科学”。
这就令人有些费解。 现象学的第一口号是“面向事实本身”,它看重的是“事实”、“实事”、“事件”。现象学与一般意义上的“实证科学”的不同只在于:后者强调观看者本人的观念与观看的对象之间的“符应”、“对应”、“符合”、“吻合”,凡“符合事实”的就是被“证实”了;凡“不合事实”的就是被“证伪”;现象学与之不同,现象学更重视观看者本人的“个人视角”、“个人立场”、“个人感觉”和“个人想象”,后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解释学实际上现象学的分支)把观看者本人的这种“视角”、“立场”、“感觉”和“想象”直接称为“前见”、“偏见”。
以我的理解,这种不同其实只是对待“事实”的姿态不太一样。当现象学呼吁“面向事实本身”时,它是鼓励观看者个人面向事实并作出个人的感觉和想象。
这有些类似诗人或小说家的态度;当“实证科学”强调“面向事实”时,实证科学是建议观看者不带私人情绪地面向事实并作出客观的可重复验证的结论。
这有些类似拿手术刀的医生。 同样是重视“事实”,现象学更重视“个别”事实,并在“直观”个别事实的当下领会、领悟事实的本质。现象学称之为“本质直观”、“现象学直观”。实证科学虽然也从个别事实着手,但实证科学更期望从“个别”事实中抽象出“一般”规律。
这样看来,现象学是把普遍的一般的规律“还原”为“个别”、“特殊”、“偶然”事实的活动,实证科学是从个别事实中“抽象”出“一般”、“普遍”、“必然”规律的活动。
当然,任何“观看”总得看出点“门道”、“本质”、“本性”来,现象学观看也不例外:现象学当然重视“门道”、“本质”、“本性”,只是现象学的态度是不离开个别去寻找所谓的本质、本性,而是在观看个别事实的过程中直接获得直观的领会、领悟。
不仅如此,现象学往前再走了一步:现象学坚持各人观看时总是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视角不同、立足点不同,各人的领会和领悟也必不相同。现象学珍重由此而发生的个人的感觉、个人的领悟。
可是,究竟如何在观看个别事实的当下获得直观的领会、领悟?这种个人的领会、领悟如何用表达出来? 这就面临一个难题。这才是现象学的真正难题。 重视个人感觉、个人直觉、个人直观并不是现象学的发明。
此前已经有大量哲学、心理学、宗教学在谈论感觉、直觉、直观的问题,中国哲学中老早以前就有“直觉主义”一脉,中国研究现象学的人也有人把西方现象学和东方的“唯识宗”连接起来考虑,这是有道理的。 这样看来,现象学在提出“现象学直观”时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知识。
但现象学还是有它的魅力的。现象学的魅力就在于它往前迈出了一步:它不只是提出了“直觉”、“直观”的口号,它开发了用直觉、直观去观看事实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悬隔”、“终止判断”;返回“生活世界”;返回“语言”和“描述”。
第一个方法是“悬隔”、“终止判断”。当你面对一个事实时,你应该把你原来有关这个事实的所有“概念”、“偏见”统统抛弃掉,不是说原来的都错了,而是不必要,所以要把这些预设的概念“用括号括起来”,用铁链把它们锁住,不让它们跑出来干扰你的观看。
把原来你拥有的概念、观念用括号括起来之后,你成了一个无知的孤儿,成了一个初生的孩童,你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你成了一个被“洗脑”的人。
空白并不可怕,空白之后,你才真正能够直接面对事实本身,你就不再用你的原来的腐朽的、败坏的概念来干扰你眼前的、身边的事实了。这样你就能够面对一个“纯粹”事实,面对一个“还原”了的事实。
胡塞尔经常讲“纯粹现象学”、“现象学还原”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面对纯粹的事实之后,接下来你怎样观看这个纯粹的事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中国的王阳明曾经就用“直观”的办法去观看门前的“纯粹”的竹子,但王阳明很苦恼,他什么也没有看出来,而且弄得生了一场大病,估计是“伤寒”。
如果胡塞尔也去看门前的竹子,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胡塞尔的办法很简单,他会说:现象学的别名是“想象现象学”。
你虽然观看的是“个别”的现象,但你可以“想象”很多很远的地方,通过“想象”把有些东西给“回忆”出来,在“想象”、“回忆”中获得领会。胡塞尔说:“而谈到回忆,它不是一件如此简单的事情,它提供了各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对象形式和被给予形式。
所以人们能够指出所谓原初的回忆,指出与任何知觉必然交织在一起的保留。”(胡塞尔著,倪梁康译:《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话虽然说得有些别扭(我总觉得是翻译、硬译的问题),但还是可以看得出来,胡塞尔悬隔了概念之后,对“回忆”是很看重的。
可是,按照胡塞尔的建议,你不是将以前的所有“概念”全部用括号括起来了、用铁链锁起来了吗?没有了以前的概念,你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你又如何能够“想象”、“回忆”呢? 胡塞尔再说:概念“没”了,但你还“有”自己的生活体验嘛。
这就对了,你还有你的生活体验。现象学悬隔了传统的方法,它自己给自己出了难题,自己把自己逼得没办法了,就提出了返回“生活世界”这个方法。
返回“生活世界”是现象学开发出来的第二个重要方法。胡塞尔本人早先并没有提出这个方法,所以他不断地讲“想象学还原”啊、“本质直观”啊,人们总是将信将疑。
胡塞尔晚年提出返回生活世界之后,“现象学还原”、“现象学直观”就有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地基。 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之后,“生活世界”究竟是什么,引起很多争议。真正的思想家总是不愿意把话直接说透,他让人去猜疑,争议,他躲在后面偷偷地得意,“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所以真正的现象学总是引起解释学。 无论思想家如何神秘,他的思想总有被人破译、被揭秘的时候,这个工作常常由思想家的学生去做。
自然,这从来就是一件危险而吃力不讨好的劳作。胡塞尔比较得意的学生是海德格尔,但即使是得意门生,学生在解释老师的思想时,虽然偶尔会让老师颔首微笑,也免不了会受老师的怨怒。这是一个两难情境。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解释,也不幸坠入而这个两难情境。
海德格尔算是做得比较高明的,他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差不多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海德格尔举的例子是“用锤子钉钉子”(法国现象学家常用的例子是“杯子”,中国常用的例子是“竹子”,这几个例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很有“意味”的)。
你如果想领会锤子是什么、钉子是什么,你就不要去“认识”、“打量”那个锤子和钉子,你需要转换态度,去“亲近”锤子和钉子,去哼着小调“用”锤子钉钉子,去“倾听”锤子钉钉子的悠然的回响。
你在使用锤子和钉子的生活过程中你领会了锤子和钉子的意义。你如果不这样,你停顿下来,去思考、反思你究竟是如何扬起锤子,究竟如何对准钉子,你就离开了锤子和钉子本身,锤子和钉子就从你的身边溜走了。
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说:返回生活世界是一种态度,观看者最好由“认识”、“打量”的姿态转换为“欣赏”、“使用”的姿态。你不要把锤子和钉子当作“认识”的“对象”,不要把自己当作一个认识的主体,把锤子和钉子当作一个被认识的客体;你要欣赏、亲近,你要与锤子和钉子融为一体、打成一片、抱成一团。
你和锤子和钉子无法分开,二者之间不分彼此,二者之间是相互交往的关系,二者在一起发生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性质。
不仅观看钉子和锤子如此,观看小说不也如此?你读小说时,你如果想去“认识”、“分析”,你就永远别指望理解、领会那部作品。比较适合你的姿态是:你欣赏他、你投入其中、你参与到里面、你与他对话、你向他提问并倾听他的回声。
欣赏、投入、参与、对话、提问并倾听其实是另一种“思”。笛卡儿曾经乐观地说“我思故我在”:我思考,我就一定存在,这是不可怀疑。 可是在海德格尔看来,事情就没那么简单。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如果你的思考方式不正确,你仍然不存在。
以前人们都习惯于用概念来思考,用推理来思考。想想,还有没有别的思考方式,你想过用艺术的方式去思考没有? 什么是艺术的思考方式? 就是“描述”、“描写”,是欣赏、投入、参与、对话、提问并倾听。
但如何“描述”?也不简单。 真正的“描述”不是直愣愣地“盯”着、“对”着眼前的现象,不是把现象当作一个“对象”。你可以设想,如果他人直愣愣地“盯”着你,“对”着你看,你会舒服吗?如果他人那样对待你,你就一定会感觉“他人就是地狱”。
你因他的存在而恐惧,他的存在是你的噩梦,你会感到“烦”、“愁”、“不安”。 你究竟希望他人如何“看”你? 其实也不复杂,好的“看”法只是“欣赏”、“来往”、“交往”。
你并不希望他人观察你,你只是希望他人“和你相好”,希望他人与你友好地“打交道”、与你“交互往来”。 如果他人不与你打交道,而是一相情愿地想观察你、采访你、琢磨你、研究你,你就会拒绝。
他一旦想研究你,你就不想和他玩,你想离开。从他打算研究你的那一刻起,你的心已经离开了他。他不再属于你,你也不属于他。你和他没有了心灵上的会面。他虽然也是一个人,但在你看来也许什么都不是,他离你远远的,他和你没有关系。
真正的看是“守护”,是“守”和“护”,看的本意是看守和看护。他人既没耐心守侯你,也不愿意护卫你,你一定不喜欢与那个人打交道。你讨厌他,你厌恶,你恶心,于是,你和他分离了。
你看,胡塞尔在晚年好不容易提出了这么一个“生活世界”的说法,这几乎是他晚年的最后一根稻草,很不容易才抓到的。但胡塞尔又把这个“生活世界”搞复杂了,以至于他本人都无法把它说明白。好在胡塞尔有海德格尔这么一个学生,尽管胡塞尔对海德格尔一直怨恨在心,但做老师的人有这样的学生,也还是不容易的。
胡塞尔只能提出返回“生活世界”的道路,但他本人却并不能清楚地把它说明白。这与胡塞尔本人的气质有关系。胡塞尔作为一个现象学大师的开拓者,他实际上是走了一条“自己否定自己”的、“自杀”的道路。
他本人的气质是传统的、学院派的,可是他开发出来的道路是“新锐”的、“艺术”精神的。 这是胡塞尔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他是一个开拓者,是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但他本人并不能直接实践他的理想。
胡塞尔本人既非诗人、画家,也不是音乐家,他是一个数学家。数学语言过于“技术化”、“人工化”,与“生活世界”的语言离得太远。 胡塞尔的理想只能由别人或下一代来完成。
完成的最有声势的据说是他的学生海德格尔,可实际上完成得最认真、诚实的人并不是海德格尔,是另外的人,另外的人比海德格尔更厉害。海德格尔为什么被认为是很厉害的人?不过是因为海德格尔和他的老师一样善于用“谜语”、“隐喻”、“遮遮掩掩”的方式说话,说得“神”乎其“神”,以至于后来的读者觉得那个人“很神”、“很神气”、“很神奇”、“很神秘”,如果你对那样神奇的思想(不是思想,其实是词语)都读不懂,就一定不是思想家的问题,而一定是你脑子笨,所以你最好说你懂,说那个思想家啊,“很了不起”。
比海德格尔更厉害的人究竟是谁?这些人甚至不在德国,而在外国,主要是在俄罗斯(托尔斯泰)、法国(萨特)、中国(鲁迅)、美国(海明威)、捷克(米兰"昆德拉)或其他国家。
说萨特是现象学家会有人同意,如果我说托尔斯泰、鲁迅、海明威、米兰"昆德拉这些小说家是现象学家,肯定会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也就是说说,你可以不信。
我这样说时,就涉及到现象学开发出来的第三个方法:返回“语言”。 第三个方法是返回“语言”,用“语言”来“描述”。现象学兜了大半个圈子,竟然又回到“语言”以及“描述”的道路上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如果说现象学所提出的“怀疑”、“悬隔”、“还原”、“加括弧”等系列策略是受了笛卡儿的影响,那么,返回“语言”和“描述”则是受了尼采的启示。前者由胡塞尔完成,胡塞尔本人曾专门写过一本《笛卡儿式的沉思》的书,这里面有“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情绪;后者由海德格尔完成,海德格尔本人则专门开设过关于“尼采”的讲座,后来又专门写过一本厚厚的直接以《尼采》为标题的专著(参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尼采》,北京:商务引书馆,2002年版,第1页)。
这里面自然也有某种“感念恩师”的情结。或许可以认为,在海德格尔的身上,尼采的影响甚至远远超过胡塞尔。 由此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不愿意接受,但我还是愿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真正的现象学的开创者,既不是胡塞尔,也不是海德格尔,而是尼采以及尼采的追随者(如鲁迅)。
如果由此再提出一个问题,可能会招来更多的反对和非议,其实也无妨,我也还是愿意把它提出来:真正的现象学者,既不是胡塞尔,也不是海德格尔,甚至不是尼采,而是艺术家,尤其是小说家。
艺术家尤其是小说家才是真正懂得“语言”和“描述”的人。“描述”在现象学方法中地位很高,想象、回忆之于现象学也是重要的,不过“描述”乃是将想象和回忆兑现为“面对事实本身”的基本器具,可见描述之于现象学实在事关重大。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惟楚有材,于是为盛”。海德格尔就认为([德]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1页。
): 现象“的”科学等于说:以这样的方法来把捉它的对象――关于这些对象所要讨论的一切都必须以直接展示和直接指示的方式加以描述。“描述性的现象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用语其实是同语反复。
可是,重视“语言”,重视“描述”难道不是艺术家尤其是小说家向来重视的技艺吗?由此看,艺术家、小说家天生就是现象学家。小说家米兰"昆德拉有些不满地断言:“小说在弗洛伊德之前就知道了无意识,在马克思之前就知道了阶级斗争,它在现象学家之前就实践了现象学(对人类处境本质的探寻)。
在不认识任何现象学家的普鲁斯特那里,有着多么美妙的‘现象学描写’!”(米兰"昆德拉著,懂强译:《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 艺术(小说)的基本技艺是把某个“事实”(“主题”或“焦点”)放到某个背景、情节、故事中。现象学一再强调Horizont(可译为“边缘”、“地平线”、“境域”、“视域”),大体也就是这个意思。
海德格尔所举的“锤子钉钉子”的例子和“此在在世界中”等思路差不多也还是这个意思。钉子本身是不能被认识的,钉子只能放在与锤子打交道的事件中才能被领会。
小说中的某个道理是不能被认识的,道理只能隐含、潜伏在小说的情节中。无论人们如何反感“文以载道”,“道”总还是愿意被载于“文”中。 老子早就窥见这个秘密,他的结论是:“道可道,非常道”。 既然“道可道,非常道”,既然道理是不可以直接讲解、不可以直接传递的,那么,道理如何被领会呢? 这就是艺术尤其是小说诞生的缘由。
道可道,非常道,于是,艺术诞生。任何艺术都是把某个被领会的道理用晕轮的效果、有某种边缘的画面表达出来。
道理是焦点,但真正的道理却有隐含在“焦点―边缘”的整体之中。 说了这么多,只有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所谓叙事或叙事研究,其实是一种现象学精神。所谓现象学精神,其实是艺术和小说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现象学重视面对事实本身的“想象”和“回忆”,艺术和小说显然一直就在重视面对事实的“想象”、“回忆”。 而在所有的面对事实本身的想象和回忆中,比较诚实的“想象”和“回忆”是“传记”,更诚实的想象和回忆是“自传”。 这就是我对叙事研究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