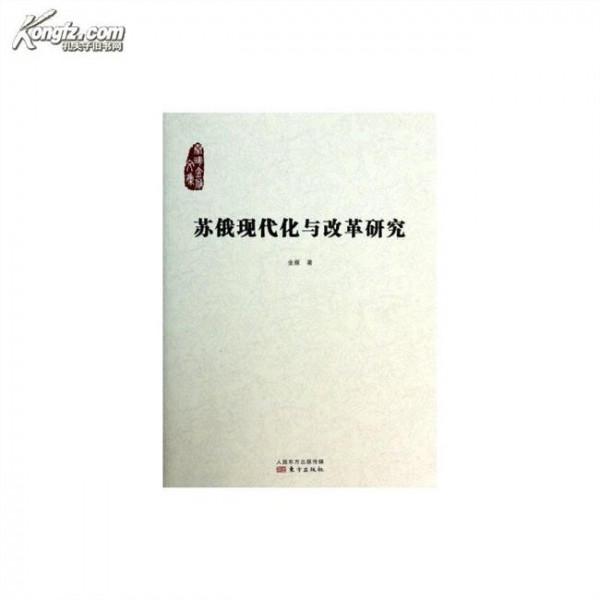秦晖金雁 金雁:多面秦晖——他的小清新与重口味
有一年正月十五,我们在旷野里散步,混浊的空气使那一轮满月都变得黄黄的,有些凄凉和惆怅。秦晖突然兴趣所致唱起了词调,从一剪梅、贺新郎、菩萨蛮、忆秦娥、孤雁儿、蝶恋花,一首接一首唱下去,很好听,也符合当时的意境,有些中间歌词记不清的地方,就胡乱编排含混的带过。
我很感动他为我唱的这些词曲,望着他想说点什么,可看他根本就没有理会我,沉浸在自我当中,就知道他不是为我唱的,而是自己想唱,就像他突然走进了中国词牌房间,打开了记忆一发不可收拾。
可转念一想,能有幸成为听众也不错。这个发癔症的老兄,不是你想让他唱什么他就能唱什么,而是他信马由缰想唱什么你就只能听什么。十五的鞭炮声远远传来,他一口气唱了十多首曲,被混浊的空气呛得直咳嗽,这才意犹未尽地住口,并不忘告诉我说,宋代早期的词牌大多是香艳伤感惆怅的,后期以后才有了像破阵子、满江红这种大气雄壮带有阳刚气的词牌。
他的这种知识讲解并不错,但是一下子就破坏了刚才唱词牌时的意境,真是职业毛病,非得把淡淡思绪和情调变成煞有介事的课堂教学,真是不懂情趣。
最好玩的是,有一次他突然讲起在农村采风的时候收集的“酸曲”,便一口气唱了几首,有的已经被《刘三姐》加工成什么“蜘蛛结网三江口,水冲不断是真丝(思)”,有的还保留原初状态如什么“想妹多,想妹多,吃饭当吃药,睡觉睡不着”,还有更黄的,“席子垫妹,妹垫哥⋯⋯”之类。
据说当初作为下乡知青的他,被县文化局借调搞民间文艺创作,在农村收集山歌小调的时候发现全是这些“黄段子”,因为觉得不符合时代精神,再加年纪小害羞,初次接触民间真白火辣的东西,只把曲调记录下来而没有记录歌词。
现在想想其实这也是一笔财富,虽然每个地区的民间都有类似的“酸曲”,但南北方言的差异使得曲艺的表现有所不同。我还看了他当年用这些曲调改写的壮剧、彩调之类应景的宣传剧目,全是“文革”中的宣传材料,有文献价值没有欣赏价值。我倒是对民间原始东西兴趣更大,因为那是这些东西可以在民间流传的原因,但可惜的是他能记起来的已经不多了。
2011年大唱“红歌”的时候,他也唱,但他说薄熙来搞的那些都是假的,当年真正的“革命歌曲”有延安和重庆两种类型,典型延安型的主要是军队歌,而重庆型的都是骂“党国”、反专制的“学生歌”。薄熙来是在重庆唱“红歌”,怎么就那么数典忘祖?他应该请我到重庆教“红歌”!
说着就唱起上世纪40年代学生运动中讽刺言论管制的《茶馆小调》,骂通货膨胀的《五块钱》,骂警察的《古怪歌》《你这个坏东西》,还有《民主青年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很多歌都是他父亲当年搞学生运动时唱的歌(秦晖父亲是广西师院1947年的学生会主席,是反蒋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说在革命党阶段,真正的“红歌”都是抨击现实的,歌功颂德的歌曲只能叫“保皇歌曲”。
秦晖改歌词的功夫也很厉害。比如《雪山飞狐》的主题曲,他过去为了吓唬女儿不要到处乱跑,把歌词改为《大妖怪》,“在马路边的高楼里住着一个大妖怪,那个妖怪他不吃别的专门吃小孩,妖怪的牙齿很锐利,它的爪子很厉害,捉住那小孩一口就将那小手咬下来”,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原歌词。他的记谱能力很强,很多曲调张嘴就来,但是往往记不住歌词,所以改词几乎不假思索张口就来,且每次都不一样,很少重复。
有次他看到电视上关于车臣“黑寡妇”的新闻,便随口哼起《回娘家》,把“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改成“杀了一个人,放了一把火,安装了一个定时大炸弹,哎呀,怎么去见我的妈”。恐怖新闻让他弄得可笑又可气,我们直骂他没良心。
早上吃药的时候他就会以《我是小海军》调子唱,“我是个药罐子,呱呱叫的药罐子,白天也得吃,晚上也得吃,天天都吃药,将来还得死。”有时我问他:“今天吃什么?”他会套用《橄榄树》的曲调唱道:“不要问我想吃什么,面条大饼都可以,你做出什么我就吃什么,草根树皮也可以。”
如果他做错什么事我批评他,他就套用《劳工神圣》的曲调,“被压迫的是我老公,被剥削的是我老公,世界呀我们来创造,社会呀我们来拯救,你是我老婆,我是你老公,老公,老公,应做世界主人翁!”由于我们作息时间不一致,有时候他会在我凌晨睡得正香时,突然跑过来对着睡眼惺忪的我,深情款款地唱“见时亦难别亦难”“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之类的古曲,让你在睡梦中有一丝感动,待到醒来想让他接着再唱时,坐在电脑前的他脑袋就像短路般,接不到那根线上了。
如果要说秦晖的爱好,旅游无疑可以排在第一位。可能他在旅游时分泌出来的多巴胺比较高,这也许是童年时在地图上漫游的愿望能够得以实现的刺激,好像天下没有他不想去的地方。有一次有人来电话问他想不想去战乱中的缅甸,是我替他答复的,说“这个环节可以略去”,因为我知道,越乱他兴趣越高。还有人问他愿不愿去南美的一些小国家,说整个旅途会很辛苦,这些因素压根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火星他都愿意去”。
我曾说,如果要问什么是秦晖的软肋的话,“旅游”说,意思是指一对情侣出国旅行,旅行中的秉性脾气、爱好情趣、生活习惯不同,一路上的细节摩擦,回到机场就从此“拜拜”了。此话不假,如果不是报团的旅游,完全自由行的话,是很考验相互的默契和应变能力的。
所以现在电视荧屏上“爸爸去哪”“花儿与少年”之类的旅游节目很火,就因为它的意外性和戏剧性是一大看点。对我而言,秦晖算不算得上“好伴侣”可以另说,但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好旅伴”。
我女儿曾把秦老爹戏称为是“天下第一导游”。他经常在出游时以“迷倒一票人等”而受到赞誉,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当地通”,也对他如此熟知当地的掌故惊讶不已。他的解说加上图片,立马就可以成一篇图文并茂的佳作。
女儿曾列出与秦老爹出游的三大好处和三大劣处,我基本认同。与秦晖一同出游的好处在于,第一,他的导游是有历史厚重感的,而且真实,绝不是旅游点上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故事可以比的。他就像考古挖掘现场一样,会按文化累积层来一层层递进地讲清因果关系,有文字记载,有旁证,有争议之处,一下子便能显现出历史学家与导游的区别。
他经常能从导游附会添加的“野史故事”中听出破绽,加以纠正或指出逻辑漏洞。很多专业导游就怕遇上这种“较真”的学者。
记得我们在美国旅游,在意大利、土耳其旅游的时候,他几乎一路纠正导游的错误,搞得人家很下不来台。以后导游就刻意回避他,可偏偏这位老兄缺少“眼力见儿”,又有好奇心极强刨根问底的精神,一边要纠正导游的错误一边得了机会还要再问导游,看得我们这些旁观者忍俊不禁。
第二,他的讲解是立体感的,上到自然资源的山川河流、矿产储备、下到建设开发、拆迁征地等社会问题。他的导游是有现实感的,有人文关怀以及比较意识的,所在国家的国歌、党派政治人物无一不关心,无一不涉猎,而且往往还会与中国联系起来比较。有一次在捷克旅行途中,他在介绍完捷克的风土人情后,突然兴致大发,唱起了捷克国歌,捷克司机一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伸出大拇指举得高高表示赞许。
另外,他的识图能力超强,只要一图在手从来都不会走错路。这可能得益于他小时候喜欢看地图的习惯。在还不太识字的时候他就爱看地图,那时候有很多旧版的书,阅读顺序和现在的不一样,所以他把黎巴嫩读成“嫩巴黎”,心里想这个“巴黎”比较“嫩”,法国的“巴黎”比较“老”;把“板门店”记作“门板店”,想着那个地方一定是卖门板的;或者认得其中的一个字,比如把“立陶宛”读成“立瓷碗”,不一而足。
这种认图习惯使得他在任何城市都可以游刃有余行走。
我们很多次在国外陌生的城市里穿行,一行人里,语言好的有的是,但认路的能力比他更好的,我还从没有见过。他带着我穿大街过小巷,沿途还不忘顺便去几个有典故的地方,从来不走重复路;正当我怀疑他带的路是否正确时,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知道从哪个小胡同里钻出来,酒店就在眼前。
在华沙的时候,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那住过将近两年,起初他总是问我那里有什么,这条路该怎么走,后来发现我这个“路盲”根本靠不住,索性按图索骥,绝对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效率最大化。
当然,秦晖的这种导游方式也不是没有短板,他的那一套不是所有人都买账的。我有时就嫌他厚重有余轻松不足,知识性过于密集,趣味性不足,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本来人们出来旅游是为了换个环境而放松的,跟着他听一天信息量太大,没了那种悠然自得,反而紧张得像打仗。
每次出行回来,我都需要“休整”多日才能恢复元气。好多年前他带着女儿和小侄子去看历史博物馆,对着一个橱窗讲起来没完没了,小孩子哪有那个耐心,我女儿敢怒不敢言,无奈地跟着,旁边倒有一个听众很喜欢他的讲解,一个橱窗不落地一路跟着听得很过瘾,连称“高人”。
我小侄子一溜烟地自己跑了一遍,回来说:“姑父,我已经从当代社会回来了,你怎么还在原始社会呢?”可见这种讲解多么不适应小孩子的口味。
与秦晖一同出游的三大“短处”,首先,他的旅行不是享受型的,而是受苦型的,甚至是自虐型的,因为他有“旅游兴奋基因”,别人不见得能够始终保持这么饱满的情绪。二十几年前在南京39度、40度高温的时候,他带我们去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们戏称,在大屠杀纪念馆的30万人后面要再加上三人,因为我们三人是“热死”的。在新疆吐鲁番盆地45度高温时,他在戈壁带我们去看古墓,我因为中暑差点没命断在古墓里。
其次,由于他的安排过于饱和,总怕某一处地方的历史古迹有遗漏,每天都累个半死,再加上他是个“拍照达人”,用张鸣的话说,他一路走过去,“死的、活的、半死不活的,都要一网打尽”。像我这体力好的人都吃不消,到最后疲劳感抵消了兴趣,也就兴味索然了。
所以到最后我们每每要和他分道扬镳,说宁肯在路边的咖啡馆里看行人也不跟着他乱跑了。还有,他一般不去那些成熟的大众景点,而要去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在抚州为了去看宋代思想家陆九渊的墓,一路走一路问,在当地人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硬是在一个荒草萋萋的山坳里找到了。在意大利为了要去看墨索里尼“萨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旧址,花费了很多时间,而错过了大众化的经典项目。
最后,他的旅游项目里,没有购物这一条,他觉得在把有限的时间花在购物上不值当的,更何况国外旅游点90%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而这一点也让我们觉得很不爽,我们的逻辑是“不花钱的女人那还叫女人吗?”所以五天以上没有购物环节我们就会“罢工”,拒绝与他同行,当然我们所谓的“购物”,无非也就是在商店里看看。
秦晖的作息时间之混乱,就像没有生物钟一样,经常是我起来的时候他躺下,他起来了我却按照正常作息该睡觉了。大部分时候我们居住得都很拥挤,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米,我们家因为书多,就更显得凌乱不堪。我们开玩笑说,干脆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得了,反正是轮流睡觉,一张单人床足矣,还能节省些地方。
即便有时夜里能正常作息,他经常会睡到半夜穿着裤衩背心消失一会儿,就像梦游一样,一会儿再悄无声息地躺下。你问他干嘛去了,他就说,我敲了几行字。
他也会在厕所里大叫,送一支笔来,可能又是想起了什么,以后我们干脆就在厕所里搁上卡片和笔,以便于谁想起什么来,拿着也顺手。久而久之,家里到处都是随手涂写了几行字的字头。他的桌子上凌乱无比,灰尘遍布,即便如此,他的桌子是不能擦的,秦晖和明成祖订立的“片板不下海,寸货不入番”的规则一样,给我们规定,“卡片不出门,寸纸不乱丢”,以防我们把他随手记下来的灵感当垃圾一样扫地出门了。
这样的结果就是家里像废品收购站,自己掐在窄窄的一溜地方连胳膊都伸展不开写东西。
按理说我们的住所不算太差劲,但架不住秦晖不断往里塞东西,家里的书到了都要“流”出去的地步,摆在门口的废旧报纸堆经常会垮下来,搞得从外面回来连门都推不开。如果恰好赶上我们俩连续有课的日子,那家里就到了要什么找不到什么的地步。我最窝火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浪费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拿来找东西了。”
这时候我就特别想让他出差出去几天,赶快归置一下,虽说脏乱的环境得不到彻底根治,起码能让我心静下来。否则他的“乱”就会导致我的“躁”,特别容易上火,心神不宁的无名火。每次他出差刚一出门,我立马进行“大扫荡”式的清理工作,从桌子上和床上清扫出半簸箕的废纸垃圾,当然他的那些卡片是不能丢掉的,顶大不了就是摞一摞,等到擦干净桌子、清理出一些地方的时候,总会长出一口气,有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
我知道等他回来但凡找不着什么又该大喊大叫了,说每一个字头都有特殊的用处。
秦晖并不高产,写作速度一点也不快,在网上大量查阅就不说了,光是在家里翻书,每次都像抄家一样,案头和床上堆得像小山一样。他的扩展能力很强,那种自然天成的特点处处可以流露出来,他所需要占的空间是他身体的数倍,是那种有多大地儿就能占满多大地儿的人,写文章铺的摊子大,经常是满床满桌的资料文献,搞得他自己没处睡觉,别人无处下脚,把他的“存在感”扩散可以达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