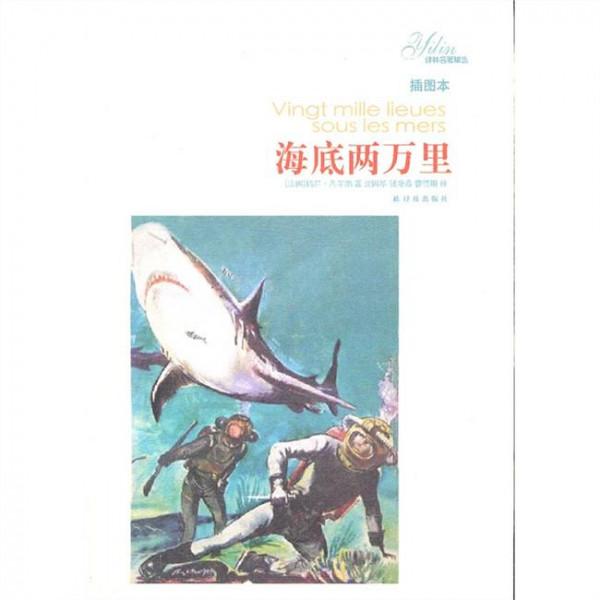梁宗岱与沉樱 何与怀:他以闷雷般的吼叫告别世界——怀念梁宗岱先生
记得一九八三年年底某一天——当时我在纽西兰奥克兰大学英语系硕士班进修并紧张准备报读博士学位,我太太从广州带来一个噩耗:梁宗岱先生去世了。
梁先生是是年十一月六日辞世,患的是脑动脉硬化兼败血症。去世前一段时间,他已经身体瘫痪,神志不清。让我极其震撼的是,梁先生弥留中一两天,变得异常豪迈粗犷,不作呻吟,而是发出一阵阵闷雷般的吼叫,在整座楼房中激起巨大回响,惊天动地。
是否此时神志不清的梁先生,灵魂深处可能还在痛苦地挣扎着,想要诉说此生要说而未说的话,或者是发泄某种感触,某种悲愤?……
也许他又在与什么人争辩了?也许是与年轻时的畏友朱光潜先生?游学欧洲的时候——那是多么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岁月啊——青春年少血气方刚的他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后来他们回国任教在北京同寓,在一块住过相当长时间,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有一次梁宗岱外出,见到朱先生发表的文章,还是顿感“来而不往非礼也”。
这样留下的辩论文章,现在清楚知道的,就有创作于日本叶山的〈论崇高〉等。他们两人的意见好像永远是分歧的。
或许梁先生此时不但动口而且又动手?又一次和罗念生先生打了起来?罗教授是著名的古希腊研究学者,一九三五年他和梁先生在北京第二次见面时就发生了这么一桩事:两人为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最后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这是罗先生的一面之词,也许梁先生另有记忆?
或许梁宗岱先生弥留中还为他一生的遗憾愤愤不平?
梁先生可谓是浪漫派的学者、才子和诗人。他自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又得父亲刻意栽培,逐养成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开阔自由的情怀。十五、六岁,一个中学生的他,即以清新的诗作在广东文坛上崭露头角,尔后更被誉为“南国诗人”。
一九二一年,郑振铎、茅盾等人发起并成立文学研究会时,十八岁的梁宗岱分别接到这两位文坛权威的来信邀请加入,成为这个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在广州的第一个会员。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一年,他先后在日内瓦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海德堡大学及意大利斐冷翠大学、罗马大学攻读文学,学习法、德、意语。一九三一年梁宗岱回国,是年仅二十八岁,就担任起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兼教授。
梁先生七年深造,精通几国文字,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但却像陈寅恪一样,不修学位,只求与异国文艺界交朋友,与文学大师的心灵直接沟通。而他作为巴黎文化沙龙的座上嘉宾,雖然年紀輕輕,其诗人气质和文学才华竟也让一向崇尚高贵和浪漫的法国文化人为之倾倒。
他們中有世界文坛中如雷贯耳的顶尖级人物。例如世界著名文学家罗曼·罗兰、法国后期象征派大师保罗·瓦雷里,以及后来(一九四七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安德烈·纪德等人。一九二九年寒假,梁先生把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园田居〉、〈饮酒〉、〈咏贫士〉等十多篇代表作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很快便得到充满赞赏的复信。
后来,他译成的法文本《陶潜诗选》又由保罗·瓦雷里亲自序言,并给予高度评价。
梁先生后来曾在一篇文章中這樣說:“……影響我最深澈最完全,使我親炙他們後判若兩人的,卻是兩個無論在思想上或藝術上都幾乎等於兩極的作家:一個是保爾·瓦雷裏,一個是羅曼·羅蘭。”先生在欧洲游学的七年,无疑是他一生最为自由得意也最悟性蓬勃、才思敏捷的时期。
梁先生在诗歌的创作、翻译,特别是研究上的确卓有成绩。现存主要作品有:诗集《晚祷》,词集《芦笛风》,诗评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译著有《浮士德》上卷、《水仙辞》、《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罗丹》、《一切的顶峰》等。
他的翻译在当时就很有影响。朱自清在一九四四年写的〈译诗〉一文中,在举例说明译诗的历史时说,“最努力于译诗的,还得推梁宗岱先生”。戴望舒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恶之花掇英》中说到波德莱尔的诗在中国的翻译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梁宗岱。
然而,这样一个学者、才子和诗人,后来几乎半个世纪早就人为地被中国大陆的诗坛和翻译界遗忘了。而此人的后半生,也的确“无所作为”,或者是难有作为!梁先生此时弥留之际,微弱的神思可能下意识地最后一次在残损的一生中游走?他闷雷般的吼叫亦下意识地伴随着一阵阵发出?
那么,梁先生其中一个很大的遗憾,一定是一直未能写出《狱中记》了?
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共产党刚刚接管大陆的年头。那时,生活在广西百色专区的梁先生,仍然口无遮拦,多嘴多舌地向地区新政权的“权力代表”提意见。这个土皇帝当然不可能知道什么文学,什么诗的价值,什么罗曼·罗兰、瓦雷里。
一九五一年九月,他以“通匪济匪”等四百八十多个罪名将梁先生送进大狱,进而准备进行“公审”判决。后来经过诸多周折,惊动了最高大人物,梁先生才保住了性命,得以出狱。这近三年并一度走近阎罗王的冤狱,真可算是梁宗岱一进入新社会就首先迎来的当头一棒。而这一棒竟准确地预示了他整个后半生的厄运!先生弥留时闷雷般的吼叫,也许也是发泄他心头未能忘却难以释解的冤屈啊!
我早在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当学生的时候,从师长的谈论中已得知“梁宗岱”的大名了,得知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这一年间,先生曾在这里任教。有时从图书馆借书,偶然看到借阅登记卡上留有先生的签名,想着几乎三十年前先生也曾经阅读过这同一本书,还会窃窃自喜。
但初见初识梁先生是在一九六四年秋天。那年我刚毕业,分配到广州外国语学院任教,而此时学院尚未成立,广东省高教局让我们一起分来的十几个未来的年轻教师先到中山大学外语系进修。
一到中大,我便像个崇拜者一样寻找机会和梁先生接近。每个星期六下午,按照党的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策,整个系的教师不分专业都法定要在一起做体力劳动,这个思想改造的庄严的时刻也成了我们交谈的好机会。
梁先生喜欢年轻人,喜欢崇拜者,总是很高兴向我“吹牛”,还给我看他不久前在海南岛参观时写的诗,使我深深觉得他宝刀未老。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江山如此美,惊鹿也回头”……他这些描写海南岛鹿回头的优雅诗句。
梁先生是系里甚至整个中山大学康乐园里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几乎一年四季,除非是寒潮到来,他的“标准”装着是运动背心、西装短裤,赤脚凉鞋。好像老见他摇着大葵扇,精神抖擞,急促促地、甚至是雄纠纠地行走,脸庞满溢红光,总是开朗明快,笑起来像顽童,坦坦荡荡。
但梁先生在康乐园里出名,最主要还是因为他爱争好胜,万事“第一”,真可谓文人的风度,武士的气质。多年前有一位温源宁先生,一九二五年的北京大学英文系主任,他在一九三五年出了一本名为《Imperfect Understanding》 (《不够知已》)的英文书,其中一篇就已经这样描写梁先生早在那时的状态: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
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未跟宗岱谈,你便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车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精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我在康乐园里看到梁先生似乎还颇受“欢迎”,常常路上就被人截下谈笑一番。談到哪个话题他都能夠信心十足且极其雄辩地自称在哪個方面“第一”。諸如“学问第一”、“教书第一”、“喝酒第一”、“种菜第一”、“养鸡第一”或“力气第一”……并惠及夫人──夫人也有不少“第一”。
据说好事者曾算出诸如此类的“第一”竟有四五十个。他万事“第一”自然引起不论熟人或生客的兴趣。我发现,一些人,特别是那些“根正苗红”因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逗他开心,觉得好玩,绝非真心尊敬他。
事实上,早在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插红旗”“兴无灭资”运动中,梁先生作为中大外语系的“大白旗”曾经被劈头盖脸地痛批过(主要罪名是“天才教育主义”──他偏爱学生中的聪慧者,如又是漂亮女学生更甚;“老子天下第一”也是罪名)。
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政策宽松时,领导向梁先生作过赔礼道歉因而现在不算“反动分子”了,但其“野人”之称是相当公开的(这称号奇怪地被“统一”在一个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背地里甚至有人称他为“性细胞”、“草包教授”……
我隨著这组进修教师于一九六五年开春之后离开中大,因为这年广州外语学院正式开办,我們也成了创办人,移居到当时广外校址广州东郊瘦狗岭编写教材,迎接新生。不料,一年后,“伟大领袖”却点燃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卷进翻江倒海、暗无天日的红色恐怖中。
传来的消息是,梁先生已经立时被诬陷为“牛鬼蛇神”。攻击先生的大字报贴满校园,更有写成文采斐然的章回小说的,吸引川流不息的观众。一些幸灾乐祸、居心叵测者像过盛大节日似地兴高采烈,上窜下跳。
先生好几次被抄家——据说“正式“被抄七次,被乘乱抄家十三次。梁先生珍藏了数十年的瓦莱里与罗曼·罗兰写给他的十九封親筆信,以及他辛辛苦苦译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浮士德》第一部的译稿,被当作“四旧”付诸一炬。先生好几次更惨遭毒打,有人专踢他要害部位,非常阴毒。我心里担心地想着:先生言多必失,又一股倔强脾气,刚直不阿,不知能否渡过这个凶险的鬼门关?
过了几年,广州外语学院率先恢复办学(最初是办社会各界的短训班,接着招“工农兵学员”,还招过学制长达五年的小学毕业生,最后于一九七七年才和全国所有高校一样通过正式入学考试招生)。我是一九六九年国庆前从广东三水南边干校被召回学院的,先是参与编写词典,后到设在广东花县的邮电英语培训班教学。
不久,一九七零年,据说是遵照广州军区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什么战略意图,中山大学的外语系和暨南大学的外语、外贸系以及广东外语学校一概并入,广外一下子大大膨胀起来。大概是在一九七一年吧,扩大了的广外从瘦狗岭搬到广州北郊黄婆洞。不久之后,花县邮电英语培训班结束,我在那里的教学任务算已完成,也回到黄婆洞校本部。
又看到梁先生了,而且现在是同事了。他的标准装着没有改变,性格亦依然故我,还是爱胜好强,口上还是挂着他的多少个多少个“天下第一”,甚至自豪地宣称自己在文革中“处之泰然”,“有惊无险”,如此這般亦算是一種“第一”。
他似乎在法语专业一些教师中并不自在,所以常常到我们系(當時称为“一系”,即英语系)串门,喜欢找李筱菊、黄伟文等我们几个编教材的高谈阔论(我们教材组的老師没有上课下课的时间限制)。但梁先生现在更不愛谈什么文学什么英语法语什么学术了。他最热衷的话题是他几十年来不断研究不断改良炼制出来的、号称能治妇科病、不育症、各种炎症包括癌症的山草成药“草精油”和“绿素町”!
梁先生此时的状态,从他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上的表现也可见一斑。那次在广州召开的盛会,全国從事外国文学这一行的大人物、知名人物都来了,一些刚刚被解放出笼的“牛鬼蛇神”也从各地赶来了。我们廣州当地的后辈也兴致勃勃地走来听讲。
可是梁先生在大会小会上几乎不发一言,绝不对文学问题、文化问题发表意见。当时在大会上用了上午下午一整天作关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评价问题的长篇主题报告的后起之秀、现为法国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的柳鸣九回忆起来,也是会议中梁先生只津津乐道、甚至可谓起劲地“推销”他的药酒。
梁先生于一九七七年在给卞之琳的信中也是这么说的:“我的工作当然还是完成学院的任务,但主要似乎已转制药、施医……”传说胡乔木在一九七九年也向他要过一些“绿素町”。真是一个另类的教授!在全国中可能再无二人可比了。
那几年,广外小圈子内还流传一个说法:梁先生珍藏了数十年的瓦莱里与罗曼·罗兰写给他的信件,一般人以为在文革中被抄去付诸一炬,其实是当时被系里一个“革命”而又“识货”者偷偷挑出并私藏起来,而事后时间越久越不敢坦白交出。
但由于没有证据,谁也说不清楚。这些宝贵文物大有可能永远不见天日了。梁先生心里也许一直窝着闷气,但嘴上不说。比起几十年来受轻视受折磨,受苦受罪,这些信件的失踪又算得了什么?!那些年月,并非“四人帮”一倒台就万事大吉。我感觉到,梁先生是干脆决心把超脱出世、看破红尘的作风保持到底。
我还有一个感觉,经过这么多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文革之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