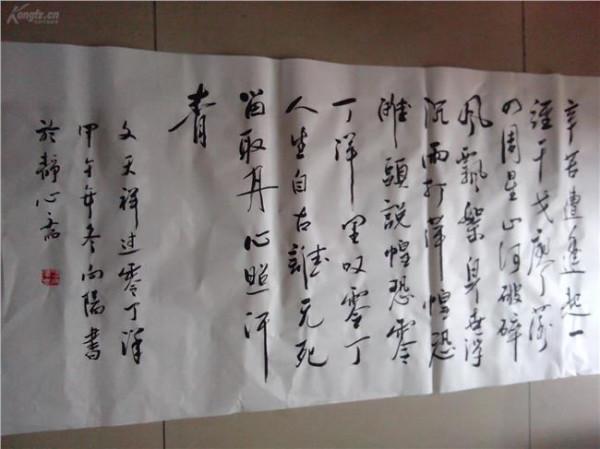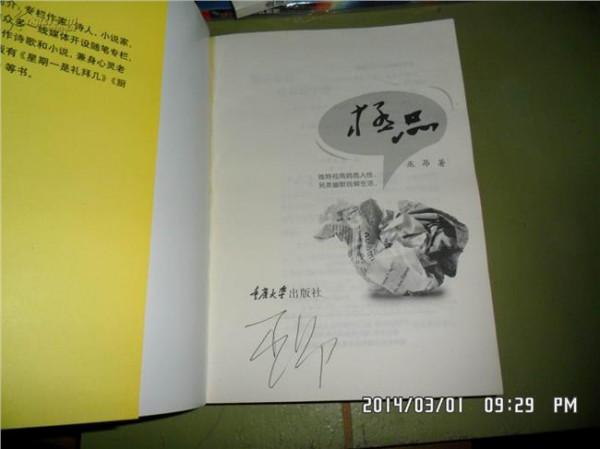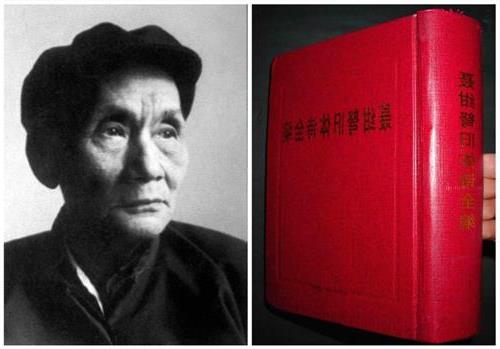巫昂的诗 巫昂答诗人口猪问:尊重写诗这种奢侈的行为∣《文学青年》巫昂专号
问:在2008年7月19日,你写了一首短诗《祖国》:这五十九年/干净得跟没有一样/冰箱冰冻了1949年/父母吃了大部分/他们吃剩的继续冷藏/而我们每天都在开那扇冰箱门。
答:记得第三代诗人孟浪的同题短诗《祖国》,最后一节有两句,“我们在可怕的黑暗中……/我们在可怕的飞翔中……”。阿赫玛托娃有一首著名短诗《祖国土》,也是用“我们”表述。于是出现一个关于“我们”的问题。我觉得你的这首诗,若将“我们”缩小为“我”,则会变成另一种效果。我想反思,诗人心里的“我”和“我们”相对应于“个人”和“集体代表”之选择,在不同时代,在这三首诗里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我也想请教你的看法?
答:你这个问题真厉害,我喜欢。
问: 当我们说到我们的时候,一定是放在一个集体的背景下的,好像集体无意识,就是中国人普遍都知道,这个我们在1949年之后指什么,孟浪的那个可怕的黑暗和可怕的飞翔指什么,俄罗斯人一定也才知道阿赫玛托娃的我们指什么,这种集体经验不是普世经验,更像是在共同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环境跟成长环境当中获得的经验,犹太人有集中营的集体无意识,美国人有911的集体无意识,大概如此。
我的那首诗,我们如果换成我,明显的,诗的所谓空间感就没有那么强了,刺穿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了,人心或许相同相通,我们的父母经验也大概相通,大家吃的食物品类差不多,喝过的水的滋味差不多,爱的机会跟恨的,也都差不多。
诗歌的好处,就是可以极其精准地刺穿它,无情地给它一个集体经验的答案,原来,我们是被批处理过的,不是精致地区别对待。
问: 你在《杀手》一诗里说“作为女人我不愿生育,作为作家我厌倦出版”。我刚阅读完你在2013年出版的新诗集《干脆,我来说》。我发现里面情诗的篇幅几乎占了三分之一多的诗集容量。我一直喜欢你情诗的气质,我甚至设想你若专门出一本情诗集,会很精彩。你的情诗一直贯穿一个“伤害”的主题,而且也投射着尖锐的性别问题。非常想了解你作为一个写情诗的高手对于“爱情诗”的见解?
答: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我特别会写情诗,你也是第一个这么评论的人。
还是先谈一谈爱情吧,狭义的男女之爱。
我们每个人的本能,都渴望有一段非常好的爱情关系,一个理想爱人,生活经验告诉我,如果两个人底下是联通的:价值观基本趋同,关于爱的理念一致,再加上日常生活基本默契,那就很难分开,有问题的关系大概是这三个环节出了两个甚至以上的问题。
我有一个爱情三角理论:其一,是性的吸引力,相当于化学反应,其二,是精神上有交流,价值观一致,其三,是过日子没问题。你用这三角理论去对照你所知道的所有情感关系,最好的,是三角俱全,其次是有两个角,最差的,是三个角都有问题,那是早晚散伙的节奏。
有些人有第一个角,便过起来了,忽略了其他两个角,消耗着最初的好感与吸引,消耗光了,关系也就戛然而止。我会始终觉得第二个角最重要,第三个需要生活经验和智慧,以及比较好的脾气,如此天时地利人和,一段长期的、有深度的爱,才可能存在,你看,既简单,又困难。
在爱情关系中,我们像是得到了一面最直接,最感性,也最丰富的自身的镜子,看到自己,看到对方,看到两个人的探戈是否和谐,我喜欢去思考爱的问题,所以我在诗里面愿意多写写爱,爱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体的重要指针,也是造化的神奇所在,而情诗,那不过是派生物,情诗的存在不是为了表达对于爱人的感情,更多地,像是某种祷告:愿我懂得爱,会爱,并得到对方之爱,在身心交融中,两人建立起一个属于两个人的坚固堡垒,抵抗乱世之浮沉,喧嚣之声响。
问:你早在“下半身”时期成名于诗坛,从诗歌及小说,一直写作到现在。我观察你的轨迹,这十几年更像是一种从诗歌圈渐行渐远的路程,呈现一种主动边缘化的倾向。在杭州聊诗歌时,我对你往内心挖掘的“一毫米”印象深刻。有诗人已经评价你是“世界级的诗人”。如今,当年的同行者不断在各种社会平台以诗歌的名义获奖,(而在我看来,这大都是一种庸俗化或诗歌平庸化的裂变开始),对于你,有否重新认知自己诗歌的质地或重量?
答:我会问我自己,我最想从写诗中得到什么?答案是肯定的,创作自身的乐趣,以及好的作品,其次,也许可以得到一二知己。喧闹的圈子化的交际,对我来说,是越来越可有可无了吧。我更希望过上独善其身,深度地往内心挖掘的诗歌生活,而不是其他,当然了,前提是料理好自己的生活,别给任何人添麻烦。
有一次,两个诗人在我跟前,以及几个不写诗的朋友们跟前谈论获奖的事,讲得很入戏,很认真,我真是很想祈求他们不要讲了,太掉价了,给诗人。关于诗歌和奖,我有几个基本原则:得了这个奖,不要让我自己跌份,别让我求着这奖,反之,让我得了它,是它的荣耀。写诗的人,得有入门级的骄傲,有些人脑子全在这上头,算是不尊重诗歌。
而得不得奖,有没有各种荣誉,对我来说,不会降低我对写诗的基本认识,得自己先尊重自己的创作,尊重写诗这种奢侈的行为。然后呢,得奖当然是世俗成功学的标志之一,我不认为我对世俗成功还有很大的热情,因为诗歌本身的绝对价值告诉了我更多,让我更感荣耀,上天给了你好作品,除此之外,都不要贪心,因为衰老有时,败落有时,活着的历程就是如此,我想保持内心的稳定性和平衡感,你向外界祈求安全感和肯定,必然容易失望。
关于巫昂
巫昂于199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攻读现当代文学并获得硕士学位。之后曾为《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后辞职,成为自由作家。在《南方周末》、《新周刊》、《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开设专栏,并持续创作诗歌与小说。旅行各地,时居北京。2007年,巫昂回归诗坛,以《犹太人》等一系列诗歌作品,赢得了新的创作高度,和广泛关注。2010年底,创办手工品牌S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