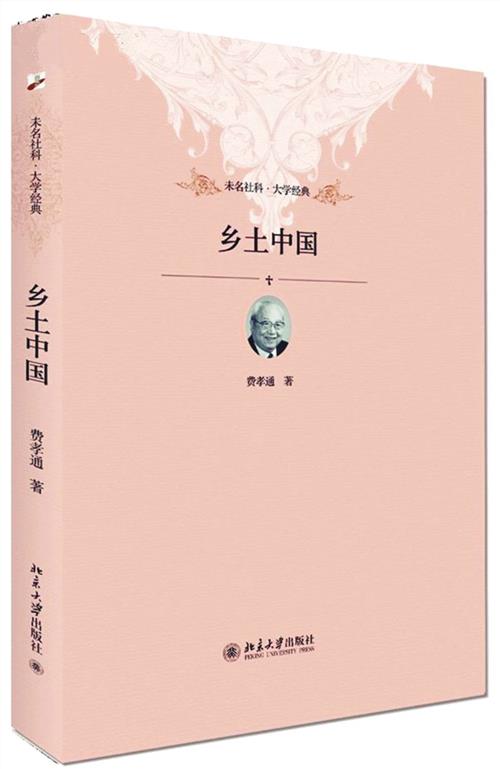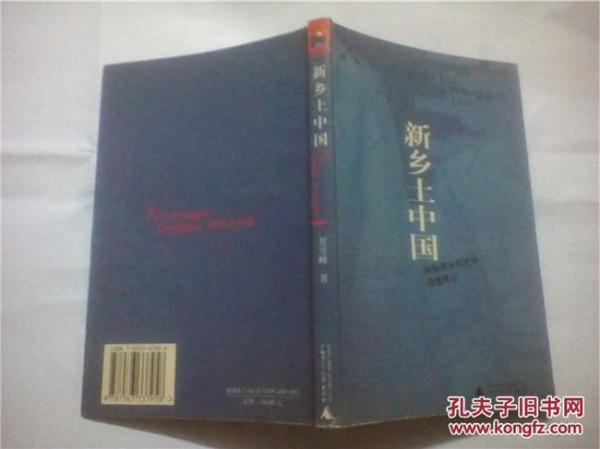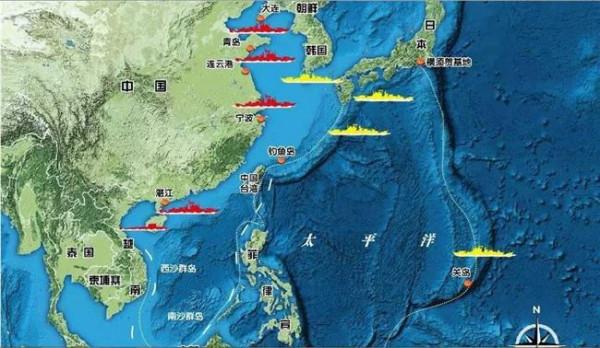费孝通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与法治——读费孝通《乡土中国》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费孝通的这一比较研究,揭示出了中国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在社会结构与秩序层面上的一对基本矛盾,即差序格局与法治之间的矛盾。本文试图根据费孝通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论述,并引申出一些我认为值得重视的问题。文章相应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概括费孝通的比较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前提性意义;第二部分则在社会变迁的视野下对这对矛盾进行具体的分析;第三部分提出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比较视野下传统社会的结构与秩序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对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结构的概括。首先,他描述出一个"他者",即西方的社会结构——团体格局,然后再以这个"他者"为鉴,反照中国社会结构的镜像。他说:"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几根稻草束成一把,几把束成一捆,几捆束成一挑。
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是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在社会,这些单位就是团体……我们不妨称之为团体格局。
"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这种差序,是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也就是儒家所谓的"伦",即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是一种有差等的次序。[2]
团体格局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在差序格局下存在的则是自我主义。费孝通指出:"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在个人名义下,一方面是平等观念,指在同一团体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个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权利;一方面是宪法观念,指团体不能抹煞个人,只能在个人所愿交出的一分权利上控制个人。
这些观念必须先假定了团体的存在。在我们中国传统思想里是没有这一套的,因为我们有的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以‘己’为中心的主义。"[3]在这一差序格局中,没有可以普遍应用的道德,社会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会道德也只有在私人联系中才起作用。
不难看出,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水波"描述与其说是一种定义,不如说是一种比喻,因此,尽管差序格局早已成为人们分析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对它的具体涵义还存在争论。比如,人们通常根据费孝通的比喻把差序格局视为一种对社会关系的描述,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将差序格局理解成社会关系的结构,再推论成为人际关系的结构,再进而变成"关系"、"关系网络"的同义词,是对这个概念的重大误解,因为费孝通一再把差序格局界定为"社会结构"。
正确的理解应当是把差序格局看作"一种立体多维的结构,而不仅仅是一个平面多结的网络。在这个结构里,纵向的等级差别至少与横向的远近亲疏同等重要。"[4]我也倾向于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费孝通讲差序就是人伦,而中国传统社会所有的人伦都是讲差等;此外,儒家讲的"仁"除了具有"亲亲"的含义外,也包括"爱有差等"的含义,即人与人之间无论是血缘家庭关系,还是社会政治关系,都必须有亲疏贵贱的伦次等差,否则就会陷于混乱。
这些例子都明确地表示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存在。
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礼治秩序",就是利用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伦理维持社会秩序。其本质是依赖着相关个人自动地承认自己的地位。[5]在费孝通看来,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
如果单从作为行为规范的意义上来说,礼和法律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然而二者维持规范的力量是不同的: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维持礼这种规范的则是传统。[6]也就是说,维持礼俗的力量不是身外的权力,而是身内的良心,这种秩序注重修身,注重克己。
与团体格局相联系的则是法治秩序。在这种格局中,"人和人的关系是根据法律来维持的。"[7]在这样的社会中讲的是个人权利,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要保护这些权利,因而制定法律。法官在审判的时候不是在分辨是非,不是在教化人,而是在厘定权利。
通过这种比较的分析,费孝通精当地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与秩序特征。当然,对他所提出的这些概念,仍然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比如有的学者对礼治秩序中的"无讼"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明清以来诉讼的频繁,说明乡土中国已经孕育了现代性的法例要求。
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驳难。[8]但是,这些观点并不能否认这一研究的价值。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和秩序的分析和判断是有说服力的,而孙隆基所说的中国人的"自我压缩"、许琅光概括的"情境中心"、杜赞奇所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和"内卷化"等提法,其实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差序格局"的判断。
同样,也有许多研究表明中西方文化确实存在一种背向特征。比如昂格尔就认为,如果把法治的程度当作坐标轴,那么传统中国构成其负的极限值,近代西方构成其正的极限值,其他各种文化社会都只是在这两者之间各得其所而已。[9]
从比较研究的方法论角度看,比较研究的本意"是为了分析而不是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差异,都来自于社会生活条件的不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传统社会的性质是相配合,而且相互发生作用的。但是,费孝通的这一比较研究实际上也指出了一个重要的矛盾,那就是试图在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建立本应以团体格局为依托的法治秩序,必然会面临着严峻的问题。
二、社会变迁与矛盾的呈现
实际上,在费孝通的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本来是个有机循环体,而西方技术、制度、文化的侵入打破了这一循环。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在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原来的某些社会需要还存在,但新建立的体制却发生了障碍,不能代替原有机制满足这种需要,结果造成文化各部分的相互脱节。
他深刻地意识到:"不论是好是坏,这传统的局面是已经走了,去了。最主要的理由是处境已变。在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洋的旁边,决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
适应于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新的处境里了。"[10]当然,社会变迁是否主要是由外部压力引发,尚值得讨论,但是社会变迁已经不能为社会继替所吸收,社会的改变开始加速,传统不再能够维持原有的社会秩序,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必须做出很大的改变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这在中国就体现为对现代化的追求。
在这一现代化的努力中,对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是重要的一环,这首先是因为礼治秩序在快速变迁的社会中是很难维持的。"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
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所应付的问题如果要由团体合作的时候,就得大家接受个同意的办法,要保证大家在规定的办法下应付共同问题,就得有个力量来控制各个人了。
这其实就是法律。也就是所谓‘法治’。"[11]然而,这种法治,在逻辑上是与中国社会结构相悖的。正如费孝通所说:"在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认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统一规则,而现行法却是采用个人平等主义的。"[12]这与法治所要求的普遍性、确定性无疑是背道而驰。
的确,对西方现代法制的学习与借鉴,是中国近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中的一部分,无论是清末的变法修律,还是民国时期的全盘西化和大规模法律移植,都体现了建构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然而,事实也证明,如果无视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盲目推行这些所谓的先进制度,并不能实现改造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目的,相反,这些制度要么被废弃不用,要么被现有社会秩序所同化,甚至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正如费孝通在书中所描述的:"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法治秩序。
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13]
在当代中国,这一问题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变得更加严峻。如果说清末和民国的法制变革是形式重于实质,而且因为社会的剧烈动荡也使我们难以看清二者之间的矛盾的话,这一矛盾的当代体现就格外清晰。这是因为,一方面,法治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已经被确立,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而另一方面,"差序格局"这一描述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结构的概念仍然有效,也即社会基本结构的深层文化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有学者指出,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之间存在的是社会结构原则的差异,是基本价值观的差异,而不仅仅是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或者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之间的不同。
因此,经济发展自身不会改变差序格局;相反,经济发展还有可能有赖于差序格局。
[14]因此,虽然由于市场的作用,乡村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发展,使得农民走出家庭,离开土地从事生产劳动,乡土社会由血缘地缘为本位逐步向业缘拓展,然而,进城农民与农村非农产业的离土农民的根,仍然扎在乡土血缘和地缘关系中。
[15]值得注意的是,差序格局随着社会发展在内容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婚姻关系与拟似血缘关系渗进差序格局当中,"利益"成为差序格局中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等等。[16]
由此可见,"差序格局"在当代社会不仅没有因为政治、经济的变革而消失,而是仍然深深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导致了一种"关系秩序"的产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从法社会学的观点来考察,礼的本质无非是特殊的持续型人际关系的制度化形态,是在互惠原则和礼乐教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秩序"。
[17]但是,在礼治秩序之下,由于传统的力量非常强大,而重在自律的长期教化亦能够起到约束的作用,但是当下的关系秩序,则由于传统的失落而失去了道德上的依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利益与力量的竞技场,使得社会秩序更加缺乏可预见性。
关系秩序不仅是区别于"法律秩序"与之并立的非正式的民间秩序,而且被编织到"法律秩序"当中成为正式的国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正式规则之下的"潜规则"。
在这样的格局里,关系网络无所不在,个人甚至可以借助"关系学"的技术来为自己或者为他人做出角色定义,改变自己与社会的边际,从而部分地塑造和修改社会的结构。[18]
差序格局及与之相伴随的关系秩序的存在,对我们建构法治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消解的作用,使得"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19]具体而言,差序格局与法治的矛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差序格局下独立人格的缺失和法治的主体性要求之间的矛盾。差序格局否定了个人人格的独立与平等,正如黑格尔所描述的:"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
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的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
"[20]这种社会结构造成了一种所谓的"差序人格",这一概念是由当代社会学研究者在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概括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意味着,在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结构的社会里,作为个体的个人决不是不可再分割的、具有本元意义上的最小单位。
相反,个人仅仅存在于一系列的关系之中,并通过这些关系来不断地根据具体情境(即自己与对方的关系)来界定自己的位置、角色以及存在的意义,个人人格需要不断地调整以适应于这个差序结构。[21]这种文化上的等级观消解了制度上的主体性,因而构成了一种对平等与一致性的阻碍。
其次,是差序格局下的个别化对待与法治的普遍性要求之间的矛盾。这与上一个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一个以差序格局为结构的社会当中,个人的权利义务不是普遍的,而是取决于在家庭、社会、国家中的位置。人不仅是家庭中的人,更是各种远近亲疏关系中的人,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同等适用的权利义务,而只有因人而易、因事而易的权衡,日本法学家川岛武宜就曾指出:"在传统社会中,人的固有支配领域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所规定的只有普遍性的秩序。
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或精神上的气氛来决定的,因此,在这里人对自己有多少权利,负有多少义务并没有明确的意识。"[22]这一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的每一个结都附着一种道德要素,而不存在某一种笼统性的相同的道德标准,也就因此,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这种以"关系"或"情境"为中心的秩序观在现代社会必然导致一种不确定性,与法律的对预期的寻求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不相容的。
这种格局追求的是一种"个人化正义",即纠纷的解决是依照双方的个性、身份或其它个人特点进行的,而不是根据诉讼本身。正如波斯纳所指出的,这种个人化正义大大扩展了关联的范围,使得做出决定的过程极为繁琐,却无法预测法律责任。
它增大了诉讼者之间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后果,还导致了司法的腐败。[23]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法律的同等保护"。与西方社会"团体格局"中的道德体系相反,"差序格局"是以自己作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并由此而组成一个社会圈子。
因此,"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24]
再次,是差序格局中的"社会性博弈"与法治的确定性要求之间的矛盾。由于在差序格局中关系网络是可伸缩的,权利义务是相对的,因此在关系秩序发挥功能的一切地方,个人就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法律秩序不可能还原为某个单纯的要素,规范内容也不可能是单义的,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更不可能彻底排除偶然的因素。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问题就是通过"交涉"的媒介,很容易流于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一切的事态,使原则和规范名存实亡,失去意义。
[25]当然,法律过程中的博弈并不全然都是消极的,实际上,现代西方法治的发展趋势正是形式性的弱化和互动性的增强,正如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所指出的"自治型法"向"回应型法"的转变,[26]就体现了这种思路。然而,如果这种讨价还价缺乏制度的有效约束,缺乏透明度,即等于一种暗箱操作,其结果取决于利益和力量的多寡,这与法治基础上互动性的增强是完全不同的。
有的学者倾向于从观念的角度解释上述矛盾,提出了一种"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理论。即,以适应现代化社会潮流的较为先进的制度性法律文化和以传统社会为根基的较为落后的观念性法律文化,这两种相互冲突的法律文化共融于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整体结构中。
[27]然而在我看来,这决不仅仅只是制度与观念的矛盾,而是我们对社会秩序的变革性安排与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之间的矛盾,这是任何一种"规划的现代化"都难以避免的困境,因为这种社会变迁的方式不容许我们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摸索和尝试,从而发展出一套能够调和理想与现实的方式。
更为深刻和复杂的是,在当代社会,由于发生了利益上的分化,差序格局与社会分层、关系秩序与法治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它们代表了不同的社会运作模式,对不同利益主体有不同的作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既有可能通过诉诸于普遍性的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有可能通过"攀关系、讲交情"的办法实现自己的利益。
也就是说,一方面存在着对法治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存在着对法治的自觉不自觉的破坏。费孝通在另一部著作中曾精辟地指出:"一种文化要素可以对于社会中一部分的人有利益而对其它部分的人没有利益,甚至有害。
有利的要保持它,有害的要取消它,没有利害关系的对之无所谓。保守和改革双方因之发生了争执,这文化要素能够维持就得看双方力的消长。"[28]因此,未来中国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秩序将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还处在一种不确定性当中。
三、道路通向何方?
费孝通在书中揭示出的这个重要的问题,对于今天我们认识和思考法治问题都有很大的助益。遗憾的是,费孝通对于差序格局并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和阐述,但是循着他所提出的这种理论路线,对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正如季卫东所说:"在法治秩序的建构屡试不成、改革的目标迟迟不能达到的今天,的确有必要检讨一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社会的把握是否正确、新制度的设计是否适当、能否采取某种与西欧法治模式在功能上等价的替代性方案等问题。
"[29]
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差序格局与法治的这种矛盾是否是可以调和的?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在差序格局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实现法治?这是一个具有前提性的问题。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实现所谓的"礼法双行",即采取制度化的方式把个人选择转写到公共选择的框架里,再用公共选择的框架限制个人选择,以避免秩序的复杂失控,而又能够合理区分日常生活与公共生活,为双方都保留充分的选择空间。
[30]问题在于,差序格局具有一种很强的渗透性,它通过差序人格和关系秩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很难在日常与公共、关系与法治之间人为地确定一条界线。
这与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关系在结构上是等同的,斯宾格勒曾说,乡村文化孕育和滋养了市镇文化,但最终,乡村心灵被疯狂增长的世界城市所吞噬。
在中国,我们则发现了另外一种情形:现代城市的发展非但没有导致乡村文化的消亡,而且不知不觉地被内在的乡村心灵所支配。[31]因此,在差序格局所导致的关系秩序和我们孜孜以求的法治秩序之间,必然存在一个互相影响的问题,它们之间存在的是一种"结构性矛盾"。
如果二者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存在一种"结构性矛盾"的话,接下来的问题就必然是,差序格局是否有可能为我们所有意识地加以改造以适应于法治的要求?实际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直都在以各种方式改造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但是这些尝试对社会结构似乎都没有起到应有的变革作用。
这一方面说明了变革的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生活对这种结构仍然存在需求,因为从功能主义的观点来看,人类创造文化为的是要增进他们生活的价值,而不会以维持文化为目的而牺牲生活,因此,需求的存在也说明了人们的生存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境遇中,现代性在本质上还处于一种"不在场"和"无根基"的状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设计的主导取向存在一定的缺陷,即我们的主导价值不是促使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变革,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强化了乡村结构的经验式文化基础,这突出地表现在城市化战略的人为滞后。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秩序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的乡里制度、宗法血缘关系把传统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对土地的依赖之上。
从根本上说,农村和农民并不单纯是一种地域概念、领域概念或身份概念,农业并不单纯是一种经济形态或社会结构,它首先代表着一种文化存在方式或生存模式。[32]上个世纪的社会变革虽然使旧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严格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等依旧以某种方式延续着人对土地的传统自然依赖,即使在现在,尽管户籍制度已经出现松动,人口流动也不断增加,但是这些问题仍然存在,而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家不仅是一种现实状态,也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一种发展思路。
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如果得不到根本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也难以有所改观。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两难的困境:是继续改造社会以适应于法治,还是改造法治以适应于社会。前者是包含了强烈价值取向的对社会的塑造,是所谓"规划的发展"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不完全对应于现实生活,而是要"以规则委屈事实"。
[33]这种方式先设定一个理想模式,然后不断推动现实向这个理想靠拢,最终达到二者的统一。但正如上文所说,这种做法遇到了许多根本性的困难。而后者则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是否一定要照搬西方的法治模式,我们是否能发展出一种建立在所谓"本土资源"上的中国式法治?这一问题可能非常有吸引力,但也是不甚清晰的,因为其前提是可以有对法治的不同界定,这种说法当然不错,但是我们对法治的理解的差异究竟可以扩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还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当然,这种思路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一切的改革都不可能是无视社会现实的,正如费孝通所说,研究中国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是进行一切有效改革的前提:"文化的改革并不能一切从头做起,也不能在空地上造好了新型式,然后搬进来应用,文化改革是推陈出新。新的得在旧的上边改出来。"[34]但是至于怎样改,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这众多重困境之下,无论是继续改造社会以适应于法治,还是改造法治以适应于社会,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对这种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保有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费孝通晚年所提出的一个重要主张,它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去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坚守传统"。
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时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改造和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与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35]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寻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之路。
【作者简介】 杜健荣,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3]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4]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5]费孝通:"乡土重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6]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7]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8]参见梁治平:"从礼治到法治?",载《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2期。
[9][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10]费孝通:"乡土重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11]费孝通:"乡土中国·礼治秩序",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
[13]费孝通:"乡土中国·无讼",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14]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此外关于经济发展可能依赖于"差序格局"或者说"关系秩序"的分析,可参见[美]裴文睿:"中国的法治与经济发展",载《洪范评论》第1卷第1辑。 [15]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阐释及现代内涵",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6]对差序格局在当代的发展与变化,可参见:谢建社、牛喜霞:"乡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新趋势",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一期;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阐释及现代内涵",载《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洪建设、林修果:"从传统—现代两种视角论差序格局的特质",载《新疆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17]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18]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19]费孝通:"乡土中国·差序格局",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20][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21]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22][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申政武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23][美]波斯纳:《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7-398页。
[24]费孝通:"乡土中国·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25]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
[26][美]P.诺内特、P.塞尔兹尼克:《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迈向回应型法》,张志铭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7]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4页。
[28]费孝通:"乡土重建·后记",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29]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30]季卫东:《宪政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31]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32]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33]许章润:"法律:民族精神与现代性",载《清华法治论衡》(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4]费孝通:"乡土重建·后记",载《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35]费孝通:"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与体会",载《师承·补课·治学》,三联书店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