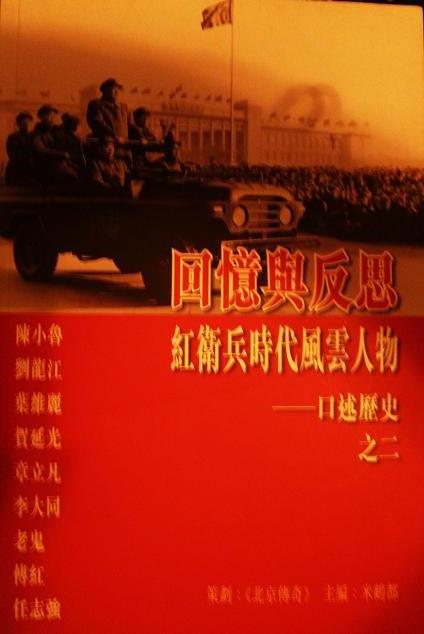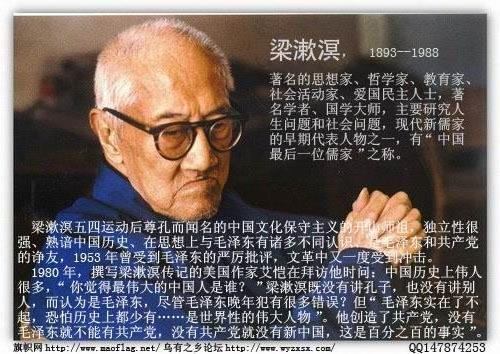刘自立:蒯大富说得不对!
最近,文革造反派领袖和很多其他人物一样回返清华,对文革定位说了一些话;主要意思是:……“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
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我不觉得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怎么说呢,如果都作为平等的身份,那么我们都彼此伤害过。文革初期,他们把我打成反革命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没有后来毛泽东给我平反,我的下场可能会更惨。
他们也从未对此表示过任何歉意,所以我没必要给他们道歉。”(老蒯言)这句话应该如何解读,也许仁智皆备,难以一统。我们的说法,也该阐明一下。
主要有几种观点,提供老蒯参考。1,文革是毛刘斗法,采用无法无天的办法,打倒刘邓陶,回返到比较毛刘周时期更坏的一类极权主义统治——这类统治的党内内涵,就是从65年以前的毛-刘双日统治,走向绝对独裁和个人迷信——这个统治,又以保留邓的权力为冗余,为毛的后期统治让位给邓做好准备;虽然,以后发生四五运动,邓的党籍,依然保留。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毛游戏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且以其死和周恩来之死做死后较量之局面。
究竟是毛胜,还是周胜,迄今没有结局——因为,邓的改革出现的问题,正在以毛化泛滥的情形,出现在中国;如,重庆现象,即为其证。
2,本质来看,毛刘斗法并不是自由派谴责文革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从一件事情,即可打住毛刘“是非”说——这就是,王光美派和毛戚的大和解——从这一点看,老蒯本来就是政治斗法里面的一个卒子——这个卒子的作用,就是被和谐或者“被斗争”与他们的此一时彼一时之需要——用后,即可扔掉。
在此意义上,蒯大富的悲剧地位和小丑地位,永远不会改变。我们看到,蒯的说法有些道理。在他早期绝食和后来被周平反的日子里,我们作为文革时期的少年人,曾经通过让红旗杂志的林杰,上传他是于高层,为老蒯后来被平反,作出努力;这样的拥毛派行为,当然是毛、周乐意见到的举止。
问题在于,时过半个世纪,我们又当如何看待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举动,有些什么意义?其实,这个意义,就是无意义;因为,就像人们探索共产党究竟有无真理一样,人们探索文革有无积极意义——是打倒刘有意义,还是拥护毛有意义;这个意义,现在看来,就是无意义。
3,为什么?因为就像纳粹运动一样,人们并非要区分纳粹集团内部有无内斗和分歧,而在于,总结和探索纳粹运动对于人类造成的严重伤害和死难。这就是说,蒯,作为清华文革的主要分子,是不是应该对清华乃至全国的文革迫害,负责,承罪和忏悔;这个迫害,甚至可以完全除去对于党内走资派的所谓打击是非论——这个打击,或者不打击,至少对于笔者而言,毫无意义。
故此,蒯,应该对于比如砍去人头这样严重的伤害事件,直接或者间接负责——更主要的是,他们应该对于死难者负起道德责任和良心谴责。
如果只是认为打倒刘,是因为刘迫害了他——就像戈林谴责希特勒对他的迫害一样;忘记了作为冲锋队员的蒯,对于整个清华学校的动乱和死难负有责任,那么,是非就会颠倒,道德就会湮灭。
文革的罪过,不是党之文件所谓对于党内大员的破害,而是对于中国老百姓的伤害。这是关键的所在。人们看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文革死难者在千万种理由下自戕和他害,而蒯,是这个迫害狂群体的首领。
至于他为什么要打击刘少奇,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就像刘一度整他一样,毫无意义——唯一的例外是,如果老蒯,既不站在毛的立场上,也不站在刘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国人受难者的立场上,问题才会发现,才会改观。
4,作为一个文革英雄和文革小丑,蒯的被整和后来的发迹(据说变为款爷),既得利于毛——也得利于邓;这是他人生的一个悖论。所以,谴责邓和谴责毛,都是蒯并未做出的应有义举。这里,我们简单分析一下邓毛体制的和谐与斗法。
其实,邓改革的实质,早在中共《共同纲领》里面,就语焉不详地点到为止了;这个东西就是,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如果共同纲领施行五十年(如刘少奇所说);那么,结局为何?就是从社会主义改观成为权贵主义之今天垄断局面——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成为红色资本家——含荣氏家族和其他家族——也就是说,这个共同纲领,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的前奏。
这个东西,很多人殊感兴趣,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许装作不知),中国红色资本家群体,无论如何发展,也不会使得,抑或仅仅使得类似荣氏家族占据资本的主角和统治地位,而是红色血统和红色家族及其子弟来瓜分主要的蛋糕和蛋糕的主体。于是,共同纲领必将转化成为特权利益。这就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党的逻辑。这个说法和老蒯又有什么干系?
5,这个干系就是,毛在文革初期提出的反对特权论,其实,是他的整个反对资本主义之举的一种伪善;因为,“社会主义就是一个资本家统治的资本主义”(托洛茨基言)——现在,这个血统论统治,五百个家庭统治,也一样是“一家”统治的资本主义。
这个东西,难道是反特权吗?根本不是。所以,他们在文革早期拿起巴黎公社旗帜摇晃一下,以为可以唤起群众之平等主义意志;而这个意志,也确实被调动起来了。
其实,巴黎公社,就是一种二率悖反;首先,马克思就既反对又支持之;巴黎公社的“建构主义”就是布朗基主义和涅恰耶夫的荼毒主义和无建制主义;他们代替孟德斯鸠主义建构理论和权力监督治衡理论的一切举止,只不过,稍稍具备一点点反对俾斯麦之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这个精神,根本就是由俾斯麦本人予以认可的一种宽容;而作为暴徒和破坏者,巴黎公社成员没有任何积极性可言——而文革,恰好是重复了巴黎公社杀人灭教的传统——他们就像巴黎公社的无神论者一样,在摧毁一切,怀疑一切……于是,一群民粹 极权的运动员,在老蒯们、聂元梓们的旗帜下,乱动起来,形成了一次规模巨大的自戕和他害运动。
这个运动,最后回却到极权主义加权贵主义的原点;而老蒯们,却还在讨论什么毛如何、如之何;刘如何、如之何?七十岁快到的人,真是没啥子出息。
在来一个方面,用法国革命比拟文革的论点,俯拾皆是,含糊不清。这些中、外人士以为,凡是暴力革命,都是以暴力,作为革命手段,革命目的的,需要否定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种残酷的事实。法国革命,是在要求恢复三级会议——英国革命,是在主张挽救议会掌政的目的中,以某种继续历史的要求为目的,以或许暴力的手段开始和开展的(克伦威尔等等)——这中形制和风格,完全不同于文革。
文革,是要连原先的“弱“极权主义覆灭,制造一个“强”极权主义,为其目的。为其手段。此间,又有几个值得注意的政治要点。其一是,文革,不像法国英国美国革命,是要恢复传统,限制帝制,还权于民。
保持自治;而是恰恰相反,要剥夺一切人,哪怕是国家主席的权力和人权(尽管,这个主席的出现,并无合法性资源可寻)。再是,法国革命提出的口号和复辟时期施行的拿破仑主义,是在双向路径上开展暴力——遏制暴力,以恢复秩序,施行自由和宗教归依为之诉求;与中国文革打倒政治宗教文化存在,完全不一。
三,即便是在1789和93年的残暴革命时期,法国革命,也是以自由的倒影为现,出现了众多的群体和党派,从罗兰党人到丹东,从罗伯斯庇尔到富歇,从拿破仑到基佐类、夏多布里昂类政治文化精英……而文革,只是在完成毛一个人的意志。
所以,众多人的暴力和一人的暴力,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走向。这个走向就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走向和所谓改革开放的走向。前一个走向,可以被无数文化人和历史家否定,但是,他们无法否定,这个通过法国革命和革命—复辟走向带来的共和和民主;同样,无论西方资本如何乐意看到和投资中国市场,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他们,也无法将“改革开放”定位在自由民主的局面之上,以普世价值实现对其之肯定。
所以,任何将文革和法国革命危险类比的方式和观点,都是盲目有害的。
6,如果回顾历史,老蒯和“四.一四思潮”提倡者周泉缨之间,一直存在争执。周的四一四思潮就是肯定造反派可以掌权,可以坐天下;不单可以打天下,也可以坐天下(——毛说,为什么造反派可以打天下,不可以坐天下……);可以推行周先生眼下主张的、反对普世价值的中国模式论——而稍后时期,周君更主张支持“三个代表”,且有其系列之表述——而蒯,则主张毛的文革精神,造反精神。
其实,二者归一,不过是体现了毛作为革命异端和最大独裁者的一币两面。毛是革命者;这个革命者要来一个打倒当时国家机器和政府体制的文革;但是,这个革命,不是顺乎人意和天意之革命,而是反革命——因为他的最终目的,不是废弃反动的极权主义政治,反而越加加强了这个统治——而他晚期的回到体制之内,又充分反映了一种反对民粹甚至反对革命的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
这个体制内、外强加于人的所谓革命,使得蒯,周二人,不过是他的机会主义需要的襄助者和推行人。所以,蒯之团派和周之四一四,也是文革之一体两面。
故此,周先生参加蒯氏六十大寿的庆祝,说明,他们的战友情怀尚不可抹煞;当然,团派和四一四之间,个人友情之间和政治观点之间,尚有分歧,并未弥合。这种分歧,并不反映四一四思潮可以脱离毛之羁绊;更不可以说明,团派有任何可以对抗毛氏资源的文革论和后文革反思精神。
这是文革研究者很少予以澄清的两面一体论。周后期的民主试错论和毛氏革命论,更是他主张文革伟大论,文革民主论的反射,并无反思和检讨文革的优势。
所以,四一四思潮肯定十七年的特征,昭然若揭,起书焰灭;而肯定十七年,则是共产党反思文革的一大观点。换言之,如果你加入官方反思和否定论,那么,你的否定文革论,就是主张回到十七年论;而团派反对十七年,不过是采纳了毛打倒一切的十七年黑暗论——可是,毛自己可以这样说,毛自己同样不会、也不能说,49年的易帜,不具备合法性;镇反,土改,反右,文革,不具备合法性——毛,绝对没有这样的历史否定论。
所以,在此层面,毛自己也不是十七年绝对否定论的作者和拥护者。他只是利用反对十七年,来达到他的十七年论,而已。我们的看法是,不论蒯大富、还是周泉樱,都不是十七年彻底的否定者。
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就连很多文革烈士,也具有反文革,拥戴毛的面貌;抑或,具备反对文革,拥护刘的态度——这都是历史局限性的表现——于是,现在,又有新一种论点出现:拥护党,反对毛(我们前此业已对此看法做过说明)——这个观点就是,主张回到党的“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主张回到陈独秀的晚期共产党优越分子那里,施行忘却陈独秀建党事业的极大危害——主张回到一党天下的,开始于毛氏统战时期的所谓联合政府状态,并且对他们民主人士走进中南海不置一词——主张回到继续对蒋介石、国民党施行全盘否定的历史错读之中;诸如此类。
所以,反对毛的思潮,在今天,忽然改换成为新的红潮汹涌以前,人们主张,施行一种去毛后,挽救党的主张。
这个主张也就是肯定十七年,继而在逻辑上,肯定改革开放,并且谆谆教导国人要相信这一天的合理出现:党,终于抛弃了毛。这是中国人走不出老蒯的红毛论,也走不出周氏的灰毛论的怪圈桎梏。
7,说一些题外话,来做出一种提示。现在,文革红潮运动正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重新爆发,大有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之势头。笔者在北京几个公园,发现大唱红歌的现象糜烂于兹,不可收拾。细节发现是,那些半老不老之辈,在每每红歌唱毕之掌声欢呼声里,让在场者,(含笔者)莫不为之感动也。
这里面,笔者认为,感动之由,主要是由回忆和纪念带来的莫名之物——这个物的煽动性力量,就是人们不是在忘却记忆,而是要重复原来的物什,而规避今天的现实——再说一边,不是纯粹的记忆在抹煞和左右中国人,而是“有选择记忆”在控制和影响之——与之相比,至少,这些红歌人群,乃至最多数人群,对于什么其他颜色和花朵,根本不知道,也没兴趣。
这是一种大趋势。这个趋势在说,如果人们再度建立一个清华文革氛围,中国文革气氛;再度创造一个老蒯式领袖;他们,至少笔者看到,他们就会再次迎接这样的领袖和英雄——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毛刘之间的间性区隔,几乎等于0——而他们寄托于毛的,就像他们寄托改革开放一样,最终,只是梦想。
至于其他力量,是不是在取道、取代和换届这样的蒯式就势/旧式/救世之道,至少,现在还不可端见!这就是老蒯高调出现,人们瞠乎其后之因素。
8,最后的结局是国际性的。就像一些价值取消者,以取消树木主干来回复历史现实现象于根茎说一样(见德勒兹《千高原》);他们以为,主要的文化中心和价值主干乃至其说之结域/结构/基层,是一种可以逃逸和弥散的解域和克分子(相对于分子说)群落——这是他们解构主义后学论的主要说法——这个说法,甚至在德勒兹的原理中,也被他用到中西,东西之经济贸易结构中去。
他的意思是,这个结构和结域,正在继续施行一种内外互动论,而每每还是以西方主轴带动“第三世界”之经贸力量。
这个说法,正在被严重动摇。这就是《千高原》一书出世和德勒兹去世后,国际间热门谈论金砖四国之今天现象。
这个现象和老蒯有关系吗?或许,也有一些。这个干系就是,文革时期,法国德国之解构主义和解域主义,要来投合毛主义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在后学那里,是他们的主要根据——他们说,战争和游牧部落就是针对国家的,法制的,秩序的一种反比和逃逸;这个逃逸,是以文革一类准战争方式,来打击国家主义中心论。
这个说法,可以延展到无穷;我们只是说,文革逃逸,试错,证伪一类说法的准后学论调,当时,正是被老蒯一类假后学者,老毛一类伪后学者所利用,而大肆涂炭天下。
现在,他们要解构西方经济中心论;以一种似乎是多元化体系来解域价值论和上帝说——这个后学文革,正在今天的中国,悄然变做现实和准现实。
这就是,人们惧怕和恐惧文革复辟的真实理由。国际社会一度支持文革——现在,他们又认为金砖一类不是膺品而是宝贝——他们以另外一种视角,来迎合一种没有文革的文革,一种经济贸易媾和于极权主义式的张伯伦纳粹绥靖主义。这是世界悲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