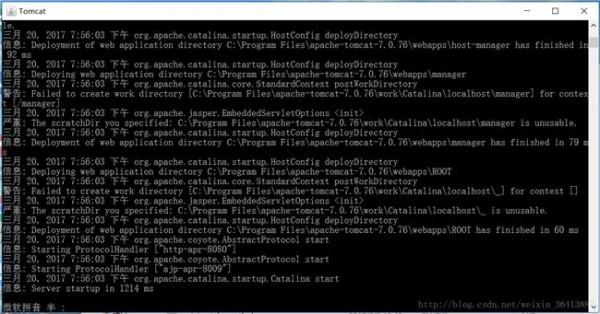沈宏非的老婆 写食?写实?——沈宏非的解构与建构
沈宏非的写食美文里,最值得回味的是这么一段:“德国咸猪手也好吃,在北京燕莎凯宾斯基饭店里的德国餐厅,可以吃到目前国内最正宗、最大型的咸猪手。德国猪手之巨,动刀之前若持之挥舞一番,餐厅四壁皆见巨大之阴影徐徐掠过,有伟人的感觉。
”(《握手言欢》)明眼人不难看出,这段是用猪手戏拟《挥手之间》中所描写的那个宏大历史场景中伟人的挥手,若干年以后,此等对经典的大胆颠覆也许会成为新的经典。
怎么写吃?前人的朵颐和创作经历不无示范之处,沈宏非也并不贸然跳跃,而是着力采撷。所以他的美食考证中,处处可见关于“吃”的经典:从袁枚的《随园食单》到汪曾祺的谈吃经验,从兰姆的典雅文笔到松尾芭蕉的幽幽俳句。
这样的文风让我们想起以抄书见长的周作人——也许五四以来的几种散文范式真的是难以逾越? 然而细读下来,饥肠辘辘就会变做微汗涔涔,《写食主义》封面的“味觉、文字、性灵”这样的广告词,也成了障目一叶;照片上拿着雪茄的这个胖胖的中年人的脸上,居然挂着蒙娜丽莎的微笑。
沈宏非经历了六十年代以来的饥饿时期,自忖是个馋人;这样的经历成为他兴致勃勃给《南方周末》写美食专栏的原初动力,可是这种理解还远远不够;贪吃的欲念几乎人人都有,为什么在沈的笔下,吃具有如此生动的姿态,如此强大的张力?如果单从个人角度来追寻,我们几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所幸,在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作者的写作方式、作品的传播途径也变成非常清楚的线索,帮助我们理解沈笔下的吃吃喝喝。
可以看到,沈出任几种刊物的专栏作者,《写食主义》几乎全由《南方周末•新生活》中的文章组成。“新生活”专栏的作者通常是相类风格的表演:有趣、机敏、漂亮、细腻,密密地漂浮在时尚上空,却又若即若离。
“风格”(style)本身成了标志,但是你很难看到统一和明确的“主题”,甚至在单篇文章里也是这样——比如有一次,连岳先生在繁重的办公楼生活里,偷了一部公家的电梯,自私地飞向木星——也许他现在还在飞着。
由这样的背景来看,沈笔下的吃喝行为具备最彻底的游戏姿态: “而一次完整的进食烤鸭的过程,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着表演性和游戏性。”(《玩鸭》) “……可惜当时的天空只有烟熏而不见鲑鱼般的粉红,要不,可真是鱼乐无穷啊。
”(《鲑鱼色的天空》) “……但见一边是徐志摩康桥下荡漾的碧波,一边是但丁的地狱里奔腾的熔岩;一边是游吟的张楚,一边是撒野的崔健;一边是韩非的峻急,一边是庄周的随便。
”(《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 专栏作者本来就要抓住眼球,“新生活”又有固定的读者群(小资?中青年知识分子?),所以沈以游戏姿态切入口腹之事,正是成功的策略;一种既轻松而又诱人吞嚼过程,在报纸两段构成令人期待的互动。
谈及游戏,从张岱,到袁枚,到周作人,到汪曾祺,不都是秉着这样的精神写文论吃?然而沈所处时代毕竟不同,非线性的多元文化形态给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角,只要看看他所拟的标题,就可以知道他美食文字中的涉猎: 《菜谱的读图时代》、《广州在吃》:(英特网术语借用) 《绵羊大尾巴的幸福生活》:(小说——电影) 《就这样被你蒸熟》、《甜蜜蜜》:(流行歌曲) 当然,也有对“经典”的挪移: 《食蛇者说》(柳宗元的文章),《论老字号的倒掉》(鲁迅文章),《可抵十年尘梦》(周作人语)。
等等。 于是,“吃”不仅仅是一个姿态,更是一种渗透在世相百态中的视角,沈宏非的文章中,从“吃”氤氲而去的诸种文化形态,简直不一而足——文学、历史、竞技、网络、音乐……这里,谈吃的人第一次走了题,走在张岱和袁枚的封闭的士大夫情趣之外,走在周作人、汪曾祺幽幽的怀旧之前;这样的走题,是沈宏非个人的一小“口”,但也许会成为散文历史上的一大“笔”。
最后回到沈的语言,用一个跟“吃”有关的比喻,沈的语言是一种有助“消化”的语言,轻松,随便,但又非常讲究,不会给人带来任何郁结: “吃喝如仪,我们飞越了黄河,飞越了长江。
将近三个小时的航程,刚好与一顿丰盛晚宴所需的时间相若。
区别在于,地面上的酒足饭饱之后,无非就想活动活动,而在飞机上,你又能干什么呢?惟一的活动就是上厕所,不过回到座位之后,却发现自己仍然以厕所里的同样姿势,坐着,嗷嗷待哺。
搞点什么活动好呢?亲爱的,让我们遭遇一些气流吧……” 这段文字中,第一句简直给人庄严的感觉(这种句式让我们想起什么?另一种经典,比如“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然而后面就越来越不象话,把休息的姿势和如厕联系起来作比,笔端也荡漾到胡思乱想。
于是,第一句的那种庄严感立刻就被打破了。这种颠覆和解构在沈文中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有意为之的策略。
在一个越来越趋于多元异质的社会,怀疑比肯定更加有效,颠覆比盲信更让人有把握,作为“生于饥饿年代”的过来人,沈对这点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写给美食的情书”并不是用最挚诚的语言造就的,其间更多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的种种特征,沈将自己的情书公之于众,也许是想让大家跟大家商量,我们在“新生活”中怎样摆脱贫乏和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