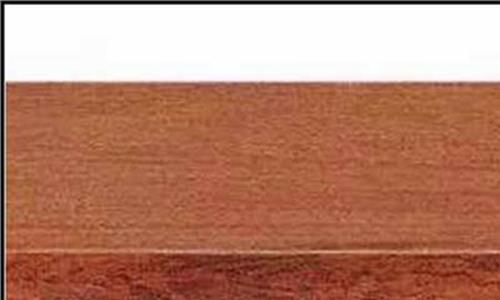王世襄何玉堂 王世襄:旧时堂前 锦灰自珍
2013年这个“十一”假期,走进恭王府乐道堂,你会邂逅一段逝去的时光。“锦灰自珍———王世襄先生诞辰百年纪念收藏展”中,这位老人弹琴,抄书,琢磨家具、漆器、铜炉,养鹰,驯狗,养蛐蛐儿、鸽子的“京城第一玩家”生活在人们眼前一一呈现。
此前的8月,为纪念即将到来的王世襄百年诞辰,《王世襄集》全套十种十四册,由三联书店出版。收入《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明代鸽经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合编本)、《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十部作品,囊括王世襄各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
家具、鸽哨、宣德炉、葫芦,还有精妙书法写就的手抄书,在眼前这些器物里,王世襄书里写的那些事情也渐渐清晰起来。而这些器物背后,是不再熟悉的旧时生活。
熬鹰猎兔,驯狗捉獾
张中行末了说,“在北京住六十年以上,见闻中学术界的人不少,还没有一个既读《说文解字》又养鹰兼斗蛐蛐的。”
甫一进入展厅,左首便可见到一幅红色剪纸。这幅名为《大树图》的剪纸曾出现在王世襄三卷本自选集《锦灰堆》的卷首,也曾出现在王世襄夫人袁荃猷《游刃集:荃猷刻纸》一书的封面上。
王世襄八十寿辰时,妻子袁荃猷特意为他刻制了这幅《大树图》。圆形树冠上,王世襄的十五件爱好像十五枚果实悬于树冠之中。漆器、家具、竹刻、绘画、铜佛、鸽子、蟋蟀、蝈蝈、大鹰、獾狗等,巧妙贯穿王世襄一生所“玩”。
“十来岁时我开始养鸽子。接着养蛐蛐,不仅买,还到郊区捉。也爱听冬日鸣虫,即野生或人工孵育的蝈蝈、油葫芦等。鸣虫养在葫芦内叫,故对葫芦又发生兴趣。尤其是中国特有的范制葫芦,在幼嫩时内壁套有阴文花纹的模子,长成后去掉模子,葫芦造型和花纹文字,悉如人意。这是中国独有的特种工艺,可谓巧夺天工,我也曾试种过。十六七岁学摔跤,拜清代善扑营的扑户为师。受他们的影响和传授,玩得更野了———熬鹰猎兔,驯狗捉獾。由于上述经历,我忝得‘玩家’之名。”在生前文字中,王世襄总结自己玩好。
“畅老(编注:王世襄字“畅安”)玩的东西都比较‘邪’。架鹰驯狗,放鸽蓄虫,即使在世家读书子弟中,他也称得上‘另类’。”文化研究者、《旧时风物》一书作者赵珩说,“其实畅老喜欢的那些很多是特别市井的,但他没有偏见。”赵珩说,当时京城世家子中,比较洋派的都是去舞场这样的地方,而王世襄喜好的东西其实有不少是挺辛苦的。“熬鹰、捉獾都很费力气,有的半夜两三点就得起床,像驯鹰为了让鹰落到手上,得把手掌裹满了布才行,一般人吃不了这个苦。”
王世襄也常常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赵珩记得常常在王世襄家中见到各色民间工匠,王世襄和他们谈匏器、讲鸽子,“聊天时候的兴奋溢于言表,就像回到青少年。”
年轻时的王世襄玩得很“野”。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后,是个玩得昏天黑地、业荒于嬉的顽皮学生,被老师洪业称作是“未知数”。他在校外的住处与考古学家陈梦家与翻译家赵萝蕤夫妇相邻。有一次深夜,陈梦家夫妇听到园外有人叫门,声音嘈杂,以为有强人到来。其实是王世襄和一帮人牵了四条狗半夜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园丁睡着了,无人应门,只好越墙而入。王世襄的玩性之大可见一斑。
“但你说他是玩儿家,我始终不太同意。他把过去不入流的东西,玩得非常精到,这是别人很难做到的。”在赵珩看来,不同于一般纨绔子弟的荒嬉,王世襄玩到追本溯源。“玩物”实际上是“研物”。
王世襄抓蛐蛐、养蛐蛐、斗蛐蛐,也写《蟋蟀谱集成》,写的关于蛐蛐的《秋虫六忆》被黄裳认为是最好的散文。张中行曾经回忆一次造访王世襄家,谈到蛐蛐罐,王世襄登高,从木柜上层摸出几个蛐蛐罐,让他看款识,摸内外皮,说必如此坚实光滑才是真的。屋内围炉摆着一圈养秋虫的葫芦器,里面有秋虫叫。打开一个看,里面立着一个大油壶鲁(北京旧称)。临辞,王世襄送他一部新出版的《蟋蟀谱集成》。回来路上张中行禁不住慨叹,真是“唯天为大”,竟能生出这样的奇才!张中行末了说,“在北京住六十年以上,见闻中学术界的人不少,还没有一个既读《说文解字》又养鹰兼斗蛐蛐的。”
“他这一辈子能干的事情很多,中学西学的融会贯通,少年时在美国学校学习,英文非常好。虽然旧家出身,他没有规规矩矩按部就班地走那个路子,中年时期又赶上我们极左的政治环境,他的青少年时代和中年时代都是被否定的。”赵珩一直认为,王世襄的中年本应该是继《国画论研究》的完成之后,做出更大的成就。可惜自1952年之后,直到80年代中期他的《明式家具珍赏》和《髹饰录解说》出版之前,竟沉寂了近三十年时间。
在沉寂的三十年里,王世襄在“三反”运动中被拘留过,被打成过“右派”。因为曾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工作,职责是追还抗战时期被劫夺之文物。但这一有功之事在“三反”中却被诬为贪污盗窃国宝,没有证据被释放,但还是不明不白被故宫辞退。赵珩说王世襄生性达观,但这件事却是他一直到晚年都耿耿于怀的事。
戴眼镜、光着腿牵一头牛,此次展出的一幅《牧牛图》是王世襄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时期的写照。牧牛、放鸭、养猪、种菜、插秧……即使生活艰苦,王世襄还是找到了玩的乐趣。“他向当地渔民学打鱼,还摆鳜鱼宴。”赵珩的父母当时也在咸宁的“五七”干校,鳜鱼一毛六分一斤,善庖厨的王世襄用14条公鳜鱼做了一桌菜:炒鳜鱼片、炸鳜鱼排、糖醋鳜鱼,还有干烧鳜鱼、清蒸鳜鱼和清汤鱼丸,其中一道“糟溜鳜鱼白加蒲菜”是王世襄最得意的香糟菜,“现在一个饭馆哪里找出14条活鳜鱼来做一个菜?”
“世好妍华,我耽拙朴”
“现在一说中式都觉得繁复为美,很少人能够体会简洁的美。”田家青说,“世好妍华,我耽拙朴”其实是王世襄对明式家具精髓的体悟。
展览中,一张“鲸背象足”的花梨独板面大画案吸引了人们的目光。这是王世襄和弟子田家青按照明式家具特点自己设计制作的画案。以明式家具研究著名的王世襄研究了一辈子明式家具,一直希望把他的思想融入在一件家具中,在2002年终如愿以偿。王世襄《锦灰堆》、《自珍集》等为人们喜爱的著作都是这张大案上完成的。中国古典家具著名学者、王世襄先生惟一入室弟子田家青说,也是在这件家具中,淋漓尽致地融进了他“世好妍华,我耽拙朴”的审美境界。
“简洁的东西是最难做的,就像写书法,比划少的最难写。”田家青说,这件画案做出来之后,陆续有不少人按这个样子做,但都仿不出那个神气。“制作古式家具,如果只是原样照仿,只要把结构做对、把工艺做精,再现其形体外貌并不算太难。难的是把握古器的风韵,令其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田家青介绍,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南方友人郭先生在其经营的进口花梨木材中开出了一块尺寸硕大的板材,质地细密,无疤无裂,十分难得。1995年,郭先生来京看望王世襄先生,得知王老已将过去一直使用的那张明代紫檀大画案交由上海博物馆收藏,自己却将就用着一张从家具店买来的“大班台”。感动之余,执意将此料送与王老,并希望田家青能帮着打造一件大案,以替代原物。
于是根据木材特点,构思设计,确定榫卯结构和工艺方案,两块木料既要得到最大限度的物尽其用,同时要让大案有时代感和艺术性。此外大案采用活插结构,所有部件都是靠榫卯“斗”合,无钉无胶。全法明式,但更加重明式特点,王世襄脑中存在多年的一张大案形象逐渐成型。
打造此案的场地在北郊,田家青记得,王先生有时候一早乘早班郊区车赶到,先与大家一块吃早饭:棒渣粥、馒头、细酱萝卜丝儿,点上自制的香油。饭后一同切磋。大案制成后,长近三米,重近半吨,王世襄特作案铭,请荣宝斋傅稼生先生镌刻于牙子的正面,以石青填色,记述了大案设计打造过程,其中“世好妍华,我耽拙朴”,田家青认为是点睛之句。
“现在一说中式都觉得繁复为美,很少人能够体会简洁的美。”田家青说,“世好妍华,我耽拙朴”其实是王世襄对明式家具精髓的体悟。“明式家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不设非功能的装饰部件。曾经有人问我什么是好的明式家具,我说,你拆不了一个部件,一拆它就塌了,就散了,就是它没有为装饰而装饰的部件。”
在田家青看来,王世襄的一个核心思想是干实事,不务虚。他记忆中王老一个生活细节见微知著。“这么多年来,朋友们来请王先生吃饭,往往去的都是比较高级的酒店,王先生其实并不喜欢。每一道菜上来,他往往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先拿筷子把菜里边做的虚的东西,什么萝卜花啊,雕的仙鹤、小桥,放的花瓣———我看得出来,他并没有真的刻意想做这件事,生活中的王世襄本是一位十分能容忍的人,完全下意识地给它挑出去。”
随遇而安,其乐不辍
赵珩感慨,我们看到这些过去的器物,之所以怀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里面装着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平淡、踏实、安静,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格格不入的那些品质。
“不是畅老发生了改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认同发生了改变,今天是一个比较正常,比较包容的时代。”赵珩觉得这20年来,或许是因为“文物热”升温,王世襄、朱家溍这些人的名字才为人所熟知、追捧,关于他们的书籍、画册出版了不少,个人经历更是被赋予了许多传奇色彩,并被誉为“奇人”“泰斗”“名家”,他们一生为文物鉴定所做出的贡献才为人赞颂。“其实,这些先生的人生经历都并非顺畅。但关键是像畅老,能做到随遇而安,其乐不辍,一直到晚年。”
“有人称他为‘玩儿家’,我总以为说得太轻浮了些。过去说‘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畅老最为擅长的木器、漆器、匏器等杂项之学,都不算显学,但在他手里却是绝学。”赵珩说。
王世襄好友、文博大家朱家溍曾说过,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有关考工、工艺的书很少,阐述制作、技法的书更是屈指可数。这是因为文人认为是工匠之事,不屑去写,实际上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想写也写不了。像专讲建筑工程的《营造法式》和专讲髹漆工艺的《髹饰录》,在传世的图书中是非常罕见的。“中国漆器有着漫长而丰富的历史,但关于漆器的著述却仅有一部《髹饰录》,而畅安先生的《髹饰录解说》也就成为唯一注释和阐述《髹饰录》的力作。他的《清代匠作则例汇编》更是一部千百年营造匠作的经验总结。或者换言之,正是有了他的《髹饰录解说》、《清代匠作则例汇编》、《北京鸽哨》这些著作,这些濒于灭绝的传统工艺才得到更广泛的关注。”赵珩说。
“对他热爱的那些器物,如家具、葫芦器等,他后来倒有了某种乐观。”北大中文系学者王风说。王风因古琴与王世襄和袁荃猷结缘,在王老后面几年常过去陪他说说话。会传统手艺的老师傅们先后去世,原先也会有担忧,但市场利益的推动,各自形成行业,有的仿制几可乱真,甚至有所谓葫芦一条街,转而作假、走私成了乱象。“我是功过难定”,王世襄曾经对王风说笑。王风觉得,那么多美好的东西,如果没有王先生在不绝如缕的时候接一把手,结局可真不好说,他就是那根“缕”。
“他不是那种怀旧的人,有的东西没有希望也就放弃了,譬如说美食。”最直接的影响是不下厨了,因为食材不对,什么味道都不对。王风记得有时王先生留饭,就到周围小馆子,每次都当仁不让地点菜,并不征求意见,然后详细交待厨师该如何做。
前几年的时候也还有坚持,赵珩记得东直门外十字坡开了一家点心铺,叫做荟萃园,汇集了旧京许多老字号的传统点心,王世襄专门打电话给赵珩父亲。“王世襄的话是不会错的。”果真,那时荟萃园刚刚开张,确是很地道,像奶油萨其玛、翻毛月饼、奶油棋子儿之类,都很不错,当时店铺内还悬挂着畅老为荟萃园的题字。“只可惜昙花一现,不到两年就歇业了,有的东西找不回来了。有好的食客才有好的厨师,就像有好的观众才有好角儿。”
“畅老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态,我现在慢慢步入老年,也开始体会到了。我们说‘这个东西没有老味儿’,狭义上讲的是味道口味,但英文是taste,有一个时代的烙印和氛围在里面。”赵珩说,肯德基麦当劳可以标准化,但中国传统的很多东西,都是个性化的,没法做到标准化。
“其实我们今天怀念畅老,并不是说今不如昔,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遗憾。”赵珩感慨,我们看到这些过去的器物,之所以怀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里面装着那个时代的生活状态:平淡、踏实、安静,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格格不入的那些品质。
譬如王世襄还在世的时候,赵珩曾经听王世襄和营造学社另一位还健在的罗哲文老先生聊营造学社的事。王世襄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经梁思成介绍,在营造学社做助理研究员。抗战期间,营造学社迁到四川重庆李庄,大伙儿穿着背心,在唐代遗留下来的建筑物上做测绘。“那时候物质生活多艰苦,但是能苦中作乐,勤奋敬业。”
俪松居长物故事
花梨木琴案
王世襄在《自珍集》中曾介绍这一花梨木琴案,并将此案放家居类之首。
1945年从重庆回到北京,这张琴桌是王世襄最早购得的黄花梨家具。原本是一件明式平头案,为给夫人袁荃猷弹琴觅得此几,并在古琴大师管平湖指导下如法改制。袁先生当时跟管平湖先生学琴,琴案供两人对弹为佳。师生对坐,两琴并置,传授者左右手指法,弟子历历在目,边学边弹,易见成效。于是两端面板各开长方孔,是为放下琴首和下垂轸穗。如果不是因为改制,王世襄说已经编入《明式家具真赏》而随所藏之79件明式家具入陈上海博物馆矣。
袁荃猷弹琴时,王世襄常伴左右,如此近60年,自称“琴奴”。而围绕这一琴案,也有很多雅事。王世襄记载,管平湖先生受聘音乐研究所之前,常去他家,而和袁荃猷同时学琴的,还有郑珉中先生,师生弹琴,均用此案。1947年10月,在京琴人在芳嘉园王世襄家中小集,签名簿记录有管平湖、杨葆元、汪孟舒、溥雪斋、关仲航、张伯驹、潘素等二十余人。南北琴家吴景略、査阜西、詹澄秋、凌其阵、杨新伦等人也都曾用此案弹奏。更有传世名琴在此案上弹奏,唐琴汪孟舒先生之“春雷”,“枯木龙吟”,程子荣先生的“飞泉”,王世襄藏的“大圣遗音”等。
瘫子制獾钩
有的器物不经描述不知道作用为何,譬如此獾钩。獾钩是王世襄“文革”后所剩不多的玩具之一,钩子棒子用处在于,獾被狗擒后,必张嘴乱咬,此时正好用钩子钩其上颚或下颌,并棒击獾鼻梁,使其立毙。制钩者是上世纪初德胜门外一位人称“瘫子”的著名铁匠。此獾钩王世襄记载是京剧名家程砚秋之父容爷在瘫子处定制所做。容爷与其弟荣三都是驯狗养鹰高手,此物为荣三所赠。
《秋虫六忆》节选
蛐蛐罐犹如屋舍,罐底犹如屋舍的地面,过笼和水槽是室内的家具陈设。老罐子,即使是真的万里张和赵子玉,也要有一层浆皮的才算是好的。精光内含,温润如玉,摸上去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多年的三合土原底,又细又平,却又不滑。沾上水,不汪着不干,又不一下子吸干,而是慢慢地渗干,行话叫“慢喝水”。凑近鼻子一闻,没有潮味儿,更没有霉味儿,说它香不香,却怪好闻的。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香”罢。万里张的五福捧寿或赵子玉的鹦鹉拉花过笼,盖口严密到一丝莫入,休想伤了须。贴在罐腔,严丝合缝,仿佛是一张舒适的床。红蜘蛛、蓝螃蟹、硃砂鱼或碧玉、玛瑙的水槽,凝似清水,色彩更加绚丽。这样的精舍美器,休说是蛐蛐,我都想搬进去住些时。
记得沈三白《浮生六记》讲到他幼年看到蚂蚁上假山,他把他自己也缩小了,混在蚂蚁中间。我有时也想变成蛐蛐,在罐子里走一遭,爬上水槽呷(音“虾”)一口清泉,来到竹林抹啜(音“戳”)一口豆泥,跳上过笼长啸几声,悠哉悠哉!
蛐蛐这小虫子真可以拿它当人看待。天地间,人和蛐蛐,都是众生,喜怒哀乐,妒恨悲伤,七情六欲,无一不有。只要细心去观察体会,就会看到它像人似的表现出来。●王世襄
采写:南都记者 李昶伟
本版图片均为南都记者李昶伟摄(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