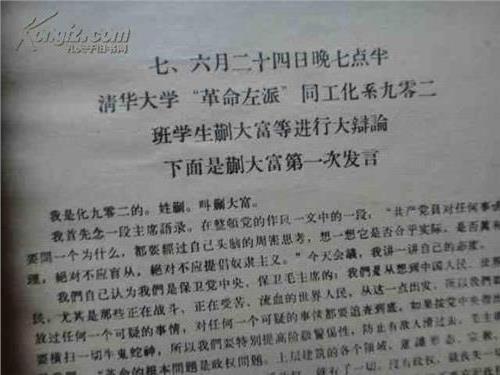蒯大富访谈录《岁月流沙》揭秘文革往事(3)
后来我们四个人,就轮流给总理汇报。我们从七点多讲到十点多,又讲了三个小时。我讲完之后,又向总理保证了我所讲的这些话的真实性。周恩来说,谢谢你啊,我马上向主席报告。然后他站起来,说,我请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带你们吃夜宵,吃完你们再回去。后来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人员,带我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我们狼吞虎咽,吃完就回学校了。
这时离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只剩一两天了。现在看就很清楚了,就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决定整刘少奇。可能他感觉材料还不够充分,所以让周恩来到清华,来找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的材料。当时中央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开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到北京了,所以当天晚上江渭清和谭启龙也来了。周总理带两位第一书记一起来,现在看,也许是让他们起个旁证的作用吧。我呢,主要谈的就是王光美和工作组怎么整我们,怎么把我们关起来,然后大会斗、小会斗的情况,等于切切实实地告了一状。因为都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我记得特别清楚。第二次谈话和第一次在清华谈是一样的,基本上光让我讲,他们只是听。总理就问了工作组怎么对待你们的?就是说把你们的情况详详细细地跟我们说。这两次谈话当中,他都没有任何倾向性的诱导,可以说是很公正地听我们的陈述。
没几天,8月5号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出来了,毛泽东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其实就是等于公开号召要打倒刘少奇了。我自己体会啊,这些和我之前向周恩来的汇报,有很直接的关系,其实就是为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提供材料。
创建清华井冈山
8月4号晚上,在清华大学东大操场召开了万人大会。这实际是中央全会的一个现场会,当时参加中央全会的那些中央委员,除了几个去北大的,其他的都到清华来了。周恩来在那个会上,宣布为我平反。他说:对蒯大富同学,还有刘泉同学,还有刘才堂同学,我是主张平反的。“蒯大富”后来怎么那么出名呢,就因为是周恩来宣布平反的,这就出了大名了。
不过,我当时已经让工作组批得太臭了,虽然周总理给我平反了,但是那次平反在学校其实并没起到太大作用。就在周总理宣布平反的会场上,有些人就公开提问题和喊口号,说蒯大富就是反革命,不应当平反,会场上就那样。后来,很多人就退一步说,蒯大富即使不是反革命,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然,学校里也有不少反工作组的同学,不同意工作组压制不同意见的做法。可是我平反后,即便这些同学也不太愿意跟我来往。包括我后来想成立组织、拉队伍非常困难,因为没人敢跟我干,也没多少人敢接近我,我在学校里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力。
因此,平反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外校的学生来往比较多些。这就要说到“三司”了,其实三司不是我成立的,我也不是什么司令。因为一司、二司都已经成立了,后来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就说要成立三司。三司1966年9月6号成立,是朱成昭拉了一帮当时各大学叫“东方红”的组织,联合起来成立的,基本上都是被工作组迫害过的一派,是当时的少数派。三司成立的时候,我们清华井冈山还没有成立,它也没有中央文革的背景。
但是很快,中央文革就支持三司了,这和它的主体是文革初期反工作组而被迫害的背景有关。中央文革让我专门找三司各参加单位的学生,从9月17号到20号吧,在中宣部小礼堂,就是老北大红楼那儿,接见我们,召开所谓“少数派座谈会”,前后在那儿谈了四天。[2]中央文革是以张春桥为首,还有王力、关锋、刘志坚等几个人。这是三司和中央文革关系密切的开始。
之后,朱成昭、韩爱晶他们就鼓励我成立一个组织,说你干革命没有组织怎么行?我说我在清华被整得太臭了,学校里没人敢跟我跑。他们就说,我们支持你。我听了他们的鼓动,动员了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组织。9月23号,我们宣布成立清华“井冈山”。成立大会在清华的礼堂召开,也就几十个人。不过,地院来了几百人,北航也拉来几百人,全部靠外校的人来壮声势。
进入十月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三司立刻发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誓师大会。当时开这个誓师大会,并没有中央文革的授意,只是紧跟形势,关键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非常对我的路子,就是批判工作组压迫群众,我们这派都是被工作组压迫的少数派嘛,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大会筹备的时候,给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陈伯达、陶铸、江青、康生等都发出了邀请。[3]以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这个大会,表示对我们的支持。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哪。
10月6号的大会我参加了,韩爱晶把我推上去念那个大会誓词。这次会上呢,张春桥看见我说:蒯大富,过来过来。他把我拉到主席台另一边,介绍给江青,说:江青同志,这就是蒯大富。江青说:你就是蒯大富啊?这是第一次见江青,也没说什么话,等于打一个招呼。
从那以后吧,三司在社会上就名声鹊起,我也成了风头人物,一度是三司三人召集小组的成员,于是社会上开始称呼我“蒯司令”。我们清华“井冈山”在学校里面就逐渐抬起头了,好多人参加了,井冈山迅速壮大。在校内,贺鹏飞和我们没形成对立的两派。他们在我们心目中是很神秘的,有高干子弟的背景,而且还是那么高的位置,我们也不大接触他们。他们早期一直掌权,在我们开始成立组织时,还是贺鹏飞在领导清华。10月份陈伯达讲话,提出高干子弟不要当群众组织的领导,所以他们就自我罢官了。有段时间清华大学就没人管了,处于无政府状态。清华大学没有出现夺权,也没形成正面冲突,等于他们退出清华运动了。我们在校内则逐渐得势。
对于原来的校党委,我们没有过多关注。蒋南翔当时已经被打倒了,在我们那时的眼里,就等于“死狗”啊。他也没什么活动,感觉上好像他们根本不在话下,不把他们当回事了。我上台后也没有直接斗蒋南翔,当然,这和我心里对他一直比较佩服也有关系,当时我也曾经当着好多人的面说过这个话。三司成立以后,有些人开始介入了批斗老干部。但我当时对这事并不明确,没怎么介入。我和其他老干部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和刘少奇、王光美有关系。
那张著名的“群丑图”其实不是我们搞的,作者也不是清华的,好像是北京戏曲学校的。但是“群丑图”是在清华的报纸《新清华》上发表的,大概是投稿投到我们那去了,或者是作者在我们学校参加运动。那时期也乱,各校学生混在一起。不过,我当时挺欣赏的,觉得画得挺生动。当时怎么界定画谁不画谁,这个我没参与。大概凡是报纸点过名的、打倒的都画进去了。
11月份,我还到上海去了一次,当时全国不是到处串联嘛,我在北京太忙,还哪儿都没去过,就想乘中央没有下令停止串联之前出去一趟。后来,我叫了几个同学坐火车到上海去了一次,大约总共也就十几天。
当时,全国都闹得很红火,大家也串来串去的,但是我还没有想过要成立全国性的组织。因为我知道中央反对成立全国性组织。有个什么“全红总”嘛,工会系统的,当时就给中央抓了反革命,遭到严厉批判。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想法。
骗斗王光美
1967年1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发生了骗斗王光美的事件。此前,因为我们要求王光美回清华做检查,周恩来批评了我。他说,主席指示: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面对面做检查,要背靠背的写检查。我们也不敢再提出这个问题,只能等中央部署了。
骗斗王光美具体的策划过程,我并不知道。我们学校电机系二年级为主的几十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捉鬼队”,为首的叫李振言。他们策划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开始没跟我讲。那次是1月6号行动的,李振言是在6号白天才告诉我,说我们想把王光美从中南海揪出来。我当时真认为是一群孩子胡闹,根本不相信他们能干成。他们说:老蒯,你给我们几辆车,我们就能把王光美骗出来。我说你做梦呢,刘少奇搞白区工作的,那么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你想骗就骗了?他们就说,你给我车吧。我说给车没问题,因为清华当时在我们手下有几十辆车。他要一个吉普,要一个卡车,要一个小车,我都给他了。他说要试试。我说,那你试吧,我也不指望你试成。结果捉鬼队骗王光美,没想到真骗出来了。
他们搞这个也是很周密的。你不由得一定会上当的。他们先找师大一附中的人,把王光美的大女儿刘平平控制下来,不让她回到中南海,还扣留了在师大女附中的二女儿刘婷婷以及在四中的儿子刘源。然后他们先冒充交警,就是西单那个交通中队,给王光美打电话,说你女儿刘平平出车祸受伤了,送到北大医院了。接着又冒充北大医院医生给王光美打电话。在假冒医生和王光美通话的时候,还让刘婷婷出来说了一句话:“妈妈,姐姐受伤了”。这就没法不相信了,先是公安机关,又是医院,还有自己女儿打电话。所以那个简直是不能不相信了。就这样子,他们冒充交警、冒充医院打的电话,全是冒充的。但因为刘婷婷被说服了,站在我们这边了,跟我们一起骗她妈呢,不由得王光美不相信。后来刘婷婷在《鲁豫有约》的节目中谈这个事,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
当时刘少奇也去了医院,我们的人都看到了,他们没敢抓。虽然大街上批判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很多,而刘少奇真到跟前的时候你也不敢抓。谁知道水有多深啊?毛泽东假如不同意,那我们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嘛。但是,他们还是把王光美带回来了。他们回来后,在化学馆给我打电话说:老蒯,王光美被我们抓回来了。我开始还不相信呢。他们说真的,在化学馆呢。我一听就说,好,告诉广播台,马上通知批斗嘛。
当时很匆忙,也没什么准备。在清华西大操场,体育馆那儿有个台子。就把王光美押到那个台子上去了。当时外地来清华串联的学生很多,大喇叭一嚎,大操场站得满满的。1月份北京多冷啊,那么多人全部站在那。王光美说冷,意思她很冷嘛,她出门的时候也没穿好衣服,就给她找了一件军大衣。她说脚也冷,有一个女同学就把棉鞋脱给她穿上了。
批斗会还没开始呢,孙岳秘书就来了,他就是周恩来找我谈话时做记录的那个秘书,我认识他。周恩来把自己的车也派来了。孙秘书说:总理听说这件事后,立刻就派我来找你。我就问他:总理同不同意我批王光美?他说:同意,但是总理要我告诉你,有几条指示:不能打;不能侮辱;斗完以后立刻让我带走。我说那行,可以。当时我就在会场用大喇叭宣布,说总理同意我们斗王光美,但是不能打、不能侮辱。我问王光美:打没打?王光美说没打,我说侮辱你没有?她说没有。但是第三条斗完带走我没有宣布。
1月6号斗王光美那次,因为没准备吗,有些同学问什么问题,王光美也不回答,有的问题或者说回答也就是反驳,根本就斗不下去,所以后来就不斗了。会后就把王光美带到我们的办公室,逼着王光美写四条保证。第一条内容是承认清华师生揪斗她是革命运动,第二条是保证以后每个星期送一份检查过来,第三条是什么记不清了,还有一条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生活上揭发刘少奇,要王光美这样写。王光美前几条都接受了,最后一条当中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揭发刘少奇她也都同意了,但是从生活上揭发刘少奇她不同意,她一直不同意,就僵在那里了。这时候孙岳秘书就在旁边催我,说赶快让我们把人带走。
这过程中,还发生两个插曲。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周恩来电话中字斟句酌地说,你们斗完了没有?我说斗完了。他说:斗完了就让孙岳同志带回来。我说马上就让孙岳同志带回去。周总理的电话放下时间不长,江青也亲自打电话来了,要找我。江青说:蒯大富啊,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我说:是啊,她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还。江青在电话里嘎嘎直笑,一直在乐。她说:蒯大富,你不准打啊,不准侮辱啊,还有总理不放心,叫我给你打个电话,让你赶快把王光美放回来。我说:我一定执行。我和江青就通过这一次电话。
我觉得,总理是怕他打电话,我不听。他就让江青再给我打电话。我们的人逼王光美的时候,我没有露面。接完这两个电话,我就进去了。大家发现我进来,就让开一条路。王光美看到我,很陌生的眼光,她把我斗成那样其实还根本不认识我。我说,王光美你认识我吗?她说不认识。我说,好啊,你差点没把我斗死,你还不认识我?她说,哦,蒯大富同志。她站起来要和我握手。我没握,说坐下。她就坐下了。我说群众批斗你、让你写保证,你为什么不写!你赶快写,写完回家。让我唬了一下,当时“生活上”三个字也没有划掉,后来她就签字了。我立刻就让王光美走了,她很快就上了总理那个车,是辆苏联产的吉斯牌老式防弹汽车,和孙岳秘书一起走了。王光美在清华前后也就押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晚上,周恩来接见七机部“九一六”[4]的时候,就批评我。他说,清华的同志把王光美骗去斗了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光明磊落嘛,我们不搞彭罗陆杨的手法。这就是指我们把王光美骗出来的方法,是彭罗陆杨的手法。当时有些小报说我讲过一句话:“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我连“怀疑一切”这种话都没说过。什么“怀疑一切万岁”的大字报,是我一个同学写的,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这在理论上很难站住脚嘛。那时也传说是我的话。
中央文革的马前卒
总体来讲,中央文革这些人的讲话我们特别爱听。他们的讲话煽动性比较强,比较直白,不像总理讲话政策性比较强。在这之前,9月26号的时候,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见我们三司头头讲话的时候说,清华和一些学校,好多大字报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还是国家主席嘛,我这个总理还是他任命的嘛。那我们就很清楚意识到,就是不要把矛头指向刘少奇。我笔记本上有很详细的记录,后来都被法院收走了。
总理对批刘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态度,他不主张批刘,至少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也不主张批刘。我当时是这样理解的:总理不主张批刘,是因为中央不到时机,还不能公开。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肯定是迟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报刊也开始暗示,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老是这么个提法。实际大家都清楚是指谁了。清华井冈山批刘少奇,在全市刷大标语,公开点刘的名,是12月份开始的。这主要是受到张春桥的影响,张春桥和我谈话以后呢,我认为时机到了。
张春桥对我一直还是不错的,对我特别关心。1966年的9月份,张春桥等在中宣部小礼堂接见了我们四次[5]。接见完以后,他给我们打气,说:现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流毒还很深,还有不少学校的同志仍然受压制……表示对我们特别同情。后来也是他带我去见的江青。
12月18号,他通知我到中南海西门。他在西门的传达室单独接见我一个人,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跟我讲了一些倾向性很强的话。他说,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他虽然没有说出“刘少奇”三个字,但是所谓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两个人,肯定是指刘少奇、邓小平。他说,他们能不能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他们的反动路线批倒批臭,不要半途而废。我当时很激动嘛,我说,首长对我这么信任,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一定要给中央文革争气。
后来在审判所谓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时候,不是让我上去揭发张春桥吗?我揭发的这件事确确实实是真事。张春桥找我谈,实际上要我把刘少奇的名字公开到社会上去。张春桥对此是很明确的。当年我不能确定,但现在可以确定,是毛泽东授意让张春桥找我的。王力在1991年前后,亲口告诉我,张春桥找我谈话是毛泽东的意思,是主席的意思。[6]
当时为什么张春桥只找我谈这件事,我以前还没细想过。当时就是觉得他对我特别信任,另外一个就是我毕竟是受到刘少奇直接迫害的嘛。从我个人讲,所谓“国仇家恨”是一致的,反刘少奇我是最坚决的。在对刘少奇的事情上,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清华井冈山总部开会的时候,我们总部的二把手唐伟就提出来,说中央没同意公开呢,你这样上街合适不合适啊?他还是基于总理讲话的精神,就是毛主席不同意大字报上街,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批斗。因为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行动推迟了几天。我当时很坚决,认为打倒刘少奇这肯定不会错的,何况还有张春桥的鼓动。所以到了12月25号,不管有没有不同意见,我一个人就独断专行,拍板决定上街。我们就大张旗鼓地干起来了。当时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对我意见比较大,比如唐伟就辞职不干了。
清华当时组织了5000人上街,事先我们开了动员大会。我说,刘少奇现在很猖狂,不投降。北京刮起了所谓的“12月黑风”,“联动”,也就是高干子弟吧,提出打倒中央文革等等。所以我们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点名打倒刘少奇。当时动员的口号就是:反击12月黑风复辟!刘少奇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2月25号那天,我们在天安门集合,然后就分五路,到天安门、王府井、大栅栏、西单这些地方游行宣传。那天风很大,天气很冷。我们准备了很多大字报,很多传单,到处散发,到处刷大标语。这次行动呢,正好符合毛主席文革的战略部署,毛主席可能是想公开,但又不好由自己提出来。而从群众组织的角度提出来,很符合毛主席的想法。
大约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大标语就铺天盖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兴,我们才刚刚见过面没几天,12月30号她又亲自到清华来,表扬我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江青说的“毛主席向你们问好”,我不能断定就是毛主席这次确实让她带的话。反正她经常这样说: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走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一仗打得太漂亮了,就是打到中央文革、打到毛主席的心窝里去了。这是他们最想干的事,我们干了。所以江青同志到清华接见我们。12月30号,当时清华井冈山的报纸有篇文章,题目叫“清华园春来早”,专门记载江青接见我们的经过。
江青那次来,还要见刘涛和贺鹏飞,我就广播通知刘涛和贺鹏飞到清华静斋。静斋是留学生楼,他们一会儿就来了。他们见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们开始谈话的时候,江青让我出来了。她跟刘涛他们讲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过过后她对我说了一句话:“老子是老子,儿子是儿子,老子不革命,儿子还会革命的,不要为难他们”。江青嘱咐关照的这句话,留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个掌权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整过他们,没整过贺鹏飞,也没整过刘涛,而且对他们还比较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