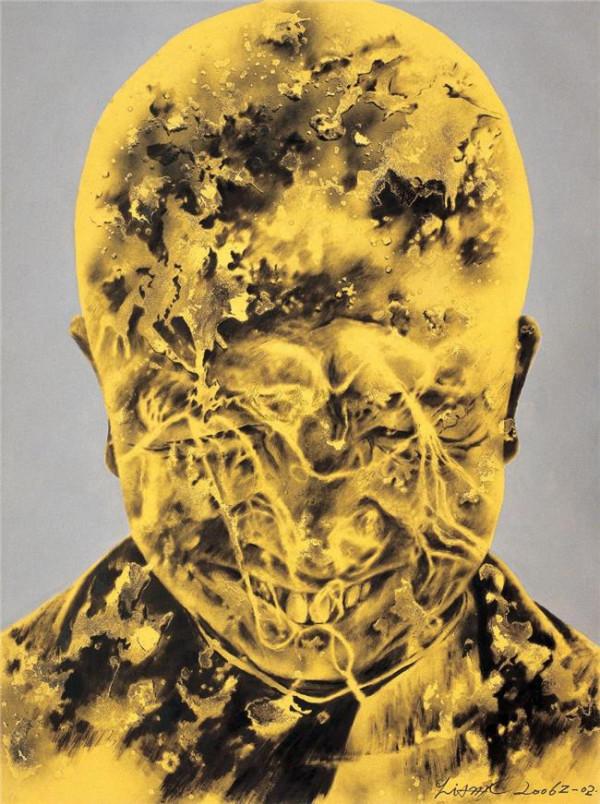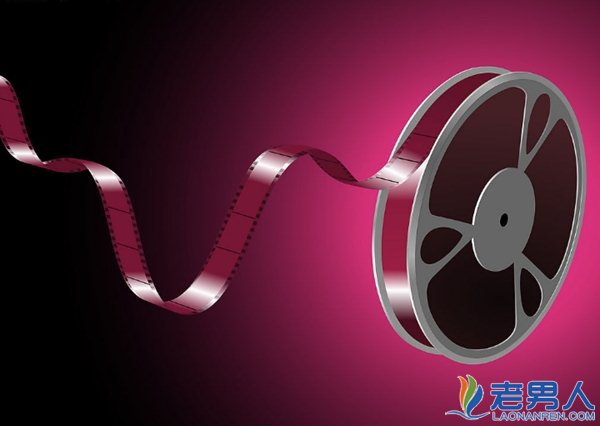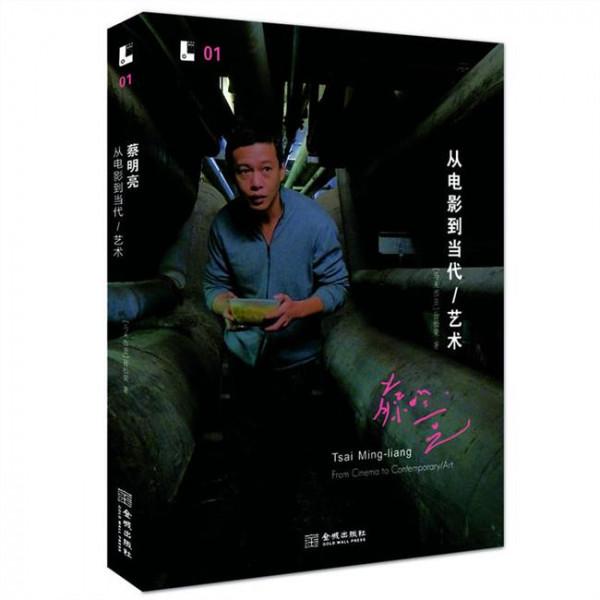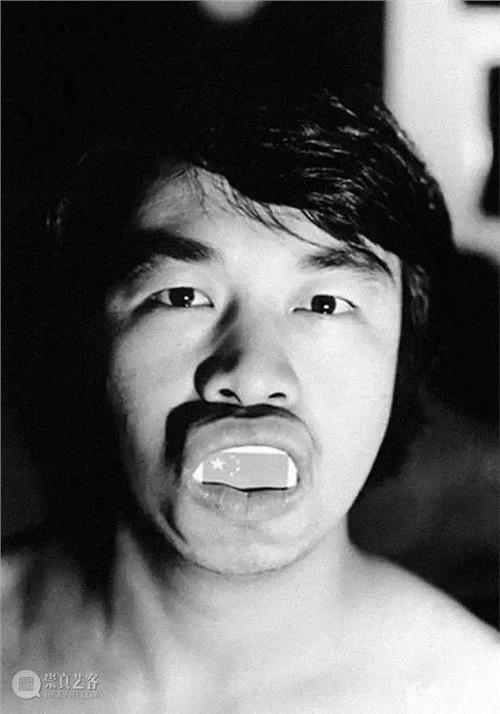栗宪庭看懂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的评论家栗宪庭 谈画家村流变
金燕:您是当代艺术的评论家,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想约您谈谈北京艺术部落的形成和发展。
栗宪庭:这要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聊。真正的艺术村落的形成要到九十年代,但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前兆,这是跟整个社会背景有关的,那时候开始出现下海潮,民工潮,个体户,也就是说开始出现自由职业这样一种现象。以前一个人如果没有单位的话是难以想象的,没法生存。
但那个时候,人开始可以脱离单位而独立生存了,这是一个大的社会背景。那个时候许多北京大学生毕业后不愿意服从分配回到家乡,就飘在北京,很多艺术家就飘在北大和清化附近。
当时我们《美术报》做过一次报道,称他们为“盲流艺术家”。因为这个报道的关系,开始认识了一些人,比如张大力、高波啊,他们都是工艺美院的,牟森是北师大毕业的,知道有这样一拨人,毕了业不想回去,漂流在北大清华附近。还有一些人已经是在职了,可是愿意在北京呆着,就以进修的名义在那里混。
金燕:为什么会聚集到那里呢?是因为那里的文化氛围吗?
栗宪庭:不仅是文化氛围的原因,最大的便利条件是可以在学生食堂吃饭,总比在外边饭馆吃饭要便宜。这也是基于生存的很重要的客观原因。
金燕:有没有寻找心理上的归属感的因素?
栗宪庭:我想象不到艺术和这些大学有什么归属关系。可能也还有群体感的因素,因为他们做的艺术和大学生比较聊得来。他们对整个社会的看法,对自由精神的认同都是有比较一致的认识的,交流起来比较容易,那里聚集了很多漂泊的灵魂(笑)。
金燕:后来是怎样发展成为村落的呢?
栗宪庭:《美术报》解散以后,当时我们《美术报》的几个人,包括丁方、田彬也开始成了漂泊一族了。田彬第一个找到后来成为圆明园艺术村的那个福缘门村,看见那有很多空房子,而且挨着圆明园的福海,可以游泳,觉得环境很好,就搬到那去了。
丁方紧接着也搬过去了,方力钧那时跟我们来往比较多,也搬过去了。他们定下来之后给我打电话,我和廖文两人就骑着自行车从后海跑到他们那里,一看,不错,一个破院子,三间房,顶多50平米,中间是堂屋,田彬和方力钧两人各占两边一间。真正的圆明园是这样开始的,后来就有些人来北京投奔到那。我也介绍过去不少人,包括鹿林。
金燕:听说鹿林是你从山东叫来的。
栗宪庭:那是我到南京做一个杂志,在南京街上看见徐一晖,我说跟我来北京吧,徐一晖就拎个塑料袋子装两件衣服,衣服口袋里插一根牙刷,就跟我走了。路过山东的时候,下车去看看鹿林。鹿林正在做装修,一听就激动了,扔下手里的工具就跟着跑来了。他们后来就去了圆明园。逐渐地,人多了起来,新闻就炒了起来,很多人慕名而来。高峰的时候就是92年至93年。渐渐开始有画廊、画商、记者频频出入那里。
金燕:94年的时候我到圆明园,很热闹,很有乌托邦的感觉。
栗宪庭:94年开始有一些人陆续来宋庄,因为到高峰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画不下去画了。像赶庙会一样,圆明园成了旅游的地方。为什么会选择宋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原因,就是因为张惠平有个学生是这个村子的人,提供了信息,说这个村子有很多空房子,农民进城了,房子就荒废了。
他们就过来看,一看周边环境还不错,有潮白河,那时桃花也正在开,觉得很理想。所以决定在这安顿下来。中间我也来看了两次,觉得不错。很大的院子,灰砖的房子,花格子窗已经变成赭石色,我从小住四合院,对这种院子有种很奇怪的情感,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只是想住农家小院》,说了我来这里的过程。
在圆明园的时候方力钧、张惠平、岳敏君几个人关系比较好,总在一起吃饭,集体请个保姆做饭,像食堂一样,所以就一起约着在宋庄买了地买了房子。
金燕:好像95年的时候才有很多人搬过来。
栗宪庭:95年,由于圆明园解散,就突然搬过来好大一批人,因为人都不知道该往哪去,不像最早的一批那样主动,有点被动和盲目。当时圆明园的一部分人去了西坝河,比如伊灵啊,王庆松啊,后来又跑到这边来了。
金燕:当时还有一个东村?跟圆明园是什么关系?
栗:那个要晚多了,跟圆明园没什么直接关系。那是94年开始的,当时在美院附近混的很多人在外面租房子,张洹啊,马六明啊,朱冥啊。他们搞行为艺术的聚集在那里。
金:东村西村(圆明园画家村)好像都是以大学周边为根据地。
栗:圆明园是这样的,东村跟大学没多少关系。当时圆明园在西边,他们就自称东村,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纽约也有一个东村,东村挨着SOHO,还有格林威志,也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