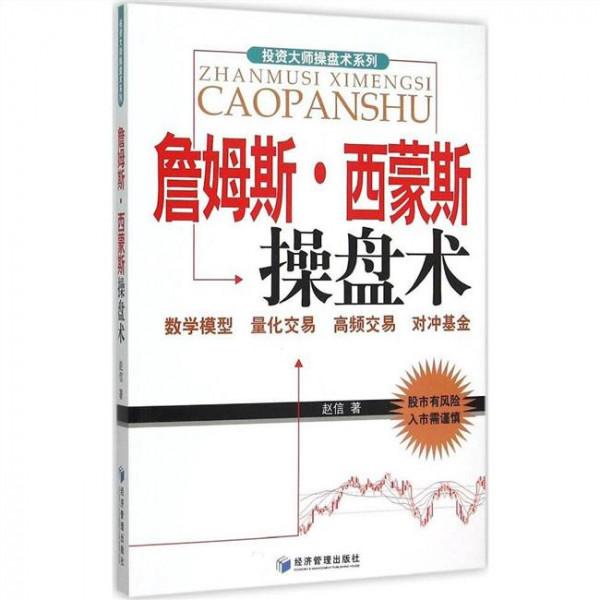西蒙斯对冲基金 全球对冲基金之王:西蒙斯跟你谈谈数学、常识和人生
詹姆斯·哈里斯·西蒙斯,美国著名数学家、学者、投资家和慈善家。1982年,西蒙斯创建了文艺复兴科技公司,这是一家私有的位于纽约的投资公司,目前管理着150亿美元的资产,西蒙斯作为该公司的CEO掌管大局,目前该公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
(注: 本文译自2014年美国数学协会举办的AMS上西蒙斯的发言,很多翻译相对口语化)
我将谈论我的人生和我经历过的不同旅程,一些是关于数学,一些是关于常识,另外一些是关于好运气。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会回答一些提问。
从我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一直喜欢数学。我不把它作为数学,而仅仅是一些数字然后从中获得快乐。但是我发现了芝诺悖论,这是我作为一个小孩的思想的证明。我在大约四岁的时候,既不知道那是谁的悖论甚至不知道悖论是什么意思。
但是当从我父亲那里,让我恐惧的知道一辆车可以耗尽所有的汽油的时候。我说”哇,汽油不可能被用完,你可以用完一半,然后你可以用完剩下一半,然后再剩下的一半,你不可能用完所有的汽油。”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没有意识到这样你的车也开不到哪儿去。(笑)
我的家庭医生知道我是一个聪明的孩子,他对我说“你知道吗?聪明的犹太男孩,你将来应该成为一名医生,那是一个伟大的领域。”但是我最不想成为的就是医生。所以我说“我真的不想当医生,我想做一些像工程学,或者数学或者那类的事情。
”我其实在八岁的时候并不知道多少。然后他说“你做那些事情根本赚不到钱。”但是,你知道,对一个八岁的小孩来说,不赚钱似乎不是什么很大的障碍。我并没有思考怎么去赚大钱。我只是不想去做医生这个看起来很好的选择,同时对那些有可能成为我的病人的人将是非常不幸的因为我不会做的很好。
但是我喜欢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圣诞节期间,在布雷克花园用品店做一个补充库存的男孩。他们雇了几个小孩子,所以我得到了这份工作。供货男孩工作在一个地下室,在这个特定的地方寻找并且把东西搬到地面上去,同时把东西搬走。
但我不是一个好供货男孩,因为我无法记住东西在哪儿了。它似乎没有任何韵律,也没有任何逻辑或者秩序。他们也不是按照字母顺序类似的东西摆放的。你只需要记住东西在哪儿。负责经营的两个人,他们意识到我是一个失败的供货男孩。
但是因为我已经在那里了,他们就说,“好吧。你可以扫地。”我喜欢这工作。我有一个大扫帚和锯末,我可以把木屑在地板上,用扫帚清扫,以保持地板清洁同时在思考,我喜欢这个,也非常喜欢做这份工作。
到了最后,圣诞节已经过去,也该我离开的时候了。这对夫妇让我坐下来,和我道别,同时问我打算做什么。我想那时候我14岁。我说,“哦,我要学数学。我想我要去麻省理工。”他们笑得非常,非常厉害。我敢肯定,他们认为这孩子甚至找不到干羊粪在哪儿,他要去麻省理工学习数学?但是,我做到了。可是我从来没有回去见他们,然后说“看,我做到了。”
我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数学,同时我认识到,我可以成为数学家。但是当我学习了斯托克斯定理的时候,我真的有了一种顿悟。我猜你们都是数学家,所以你们可能都知道斯托克斯定理:你沿着对一个东西沿着边界积分,然后你对它求导--和你对整个曲线内部积分是一样的。
它一般化了积分的基本定理,同时对所有维度都适用。我认为这个定理是我认识的最美妙的事物。它真的让我欣赏数学。它让我想成为--进入微分几何这个我逐渐学习并意识到它的存在的领域(注:西蒙斯是世界级的数学大师,1976年,他获得美国数学会的范布伦奖,和我国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发现了“Chem-Simons几何定律”)
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是波士顿的一家叫做杰克和马丽恩的熟食店。恐怕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那时候是个很不错的地方,总是开到很晚。作为大学生,我们经常深夜甚至凌晨两点去那儿聚餐。你们知道,年轻人能一天到晚的吃东西。
但是经常的,辛格和沃伦.安步罗斯(MIT的两位数学家)也在那里。我想大家都知道辛格,安步罗斯是一个老家伙,那时候应该已经50岁了。他对我来说太古老了虽然他是个很好的老师。他们会出现在那里然后工作。 他们会走到一个隔间。
喝咖啡然后做数学。然后我想,我的上帝,多么美妙的生活。这些是成年人,他们也这样做,还穿着正装。有时他们也会穿着普通的户外服装。我对自己说,这样的生活太棒了。凌晨两点,一边吃汉堡一边讨论数学,显然这就是我要的。
我从MIT毕业,我是提前毕业了但是另外在研究生院又呆了一年。我是1958年毕业的,这就是58的来源。大卫在哪儿?他总是混淆这些日期。 我的确做了一件事情,可以作为一个我毫无常识的例子。但是这也最后也证明人有时还是需要有些好运气。
在那时候,摩托车刚刚开始流行。你知道,意大利的品牌,Vespa或者是Lambretta, 这是你可以有的两个选择。于是我和一个南美哥伦比亚来的MIT的朋友,他不是数学家,我们决定开摩托,首先是搞到摩托车,我们还没有车,我们甚至也不知道怎么驾驶摩托车。
但是我们觉得应该不会很困难。我们要开摩托车从波士顿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去(观众笑),是的,他们都以B开头。你知道,从Boston到BuenosAire。
我们搞到了摩托车,另外一个哥们也加入了我们。我们走了一半路,花了七周的时间,到达了波哥大(哥伦比亚首府),我几乎死掉,离死非常接近了。我想这些我从来没有告诉我妈妈。如果我母亲对于这趟旅行的危险性有任何丝毫的理解,她肯定会因为某些原因不会让我去的。
但是她的确让我去了。所以我也到了那儿。关于这个演讲的一个主题是你的合伙人和你的工作伙伴的重要性,这两个家伙,这个哥伦比亚男生和他的朋友,先后成为我的商业风险投资上的第一批合伙人,我马上就会提到。但是我还是很幸运因为这件事情回头看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常识。
我在麻省理工读了一年研究所,我想我在那里呆的时间够长了,我应该去伯克利去见陈省生,那时候最伟大的几何学家。同时接受合适的微分几何教育,因为这是我喜欢的。所以我去了伯克利,同时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奖学金。但是问题是陈没有去伯克利,陈省身那年应该是去伯克利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建议我应该去伯克利,但是也许是知道我要来,他那年去了另外的地方(哈哈哈),我猜他只是在学术休假或是类似的事情。
所以我没有见到陈。但是我和科斯坦特一起工作了。
有人告诉我波特. 科斯坦特今天来了,他在这里吗?……不,他不在这里。我想我没有真的看到他。好吧,我在那儿和一个叫波特. 科斯坦特的人一起工作。但是我去伯克利的第一件事情是我结婚了。我去那里的一个月之内就结婚了。然后有了一个婚礼,我们也受到了一些结婚礼物,是些现金。所以我----我们有了一些钱。然后我想,这些钱只是放在那里,我们应该做一些投资。
我那时候对投资一窍不通,但是我知道我可以投资。所以我去了美林证券,那时候我21岁,我告诉他们我要开一个账户,有两只股票我认为可能会非常棒,我想买这两只股票。所以我就开户买了股票。但是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一个月之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股票既没有涨,也没有跌,什么也没有变化。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无聊于是我回去证券公司说“有没有什么更活跃的,你知道,你有啥建议吗?”他说,“哦也,大豆,你应该买大豆。”我听过大豆,但是我从没有吃过。
实际上原来大多数人都没有吃过大豆。但是猪,牛等需要大量的吃大豆。但是我说“好吧,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他说“当你买5000 蒲式耳大豆,这是一个期货合约。我们的人告诉我大豆的价格将要飞涨,你可以赚很多钱。
”我说OK,然后就买了两份大豆的期货合约。它们的价格的确变动了,上涨了,我赚了一些钱,然后又下跌了,我又亏了钱。我把两份合约都卖了,我又有点紧张然后又买了一份合约。同时,我每天早晨从伯克利到三藩市来回往返以便观察大豆市场。
多早呢?早上八点钟就已经出门了,我的意思是,对一个研究生来说,那已经很早了。大概一周以后,我做出了一个我人生中最明智的一个决定,我在这个很好的时点意识到,我想我或者去写论文或者去交易大豆但是我不可能同时做两件事。
同时我有了一小部分利润。我获利平仓了。直到几年以后时机来临的时候我才又交易大豆,然后我就一直工作下去。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同时做两件事情,你不能一边写论文,一边交易大豆,无论如何,我不行。
我完成了我的论文,这是一个很好的经历,是的我写的论文。非常遗憾波特没有在这里。但是我得到了一些结果给我的导师看然后他说:'哦,这些结论非常有趣,非常好!'他也建议了一个关于和乐群组的开放性的问题。这儿有人知道和乐群组是什么吗?也许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和乐群。
总之,它是一个和流形的联接相关的群组。比如说在切丛,你移动切空间时,你可以平移然后总是可以回到你初始的地方。如果已经证明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都成立,那它就是一个线性变换的线性组。
最近已证明,有一个不可约流形的所有可能的候选乐群组列表,你不可能把它写成另外两个黎曼流形的的积。这个列表只包括可传递的单位球面上的组。因此,任意一个这些组,你可以取球面上的任何点,在这个切空间把它带到任何其他点。
所以它是可传递的。这的确是一个好问题。但是,为什么它们在球面上都是可传递的?我说,“哦,我想试尝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不要那样做,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因为那就像向火焰上投掷汽油。
但是,我将要去研究这个问题。嗯,或许是一个奇迹,我的确完成了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论文。我也很高兴在这个过程中我和辛格有一些互动,因为他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我们谈了一些或互相写信。然后,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邀请我去了麻省理工,成为摩尔讲师。
但是,好吧,我现在是一个MIT的讲师,但是我内心仍然有一种,我不知道,做一些不同的事情的冲动。当我在哥伦比亚,在我的那次摩托之旅时,我们去了波哥大,我和我的朋友看到了哥伦比亚,一个非常让人激动的国家。似乎你在那里可以做任何事情。
所有的东西都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制造出来。我在那个有个非常聪明的朋友,实际上是两个。我就说,你们知道吗?你们应该开始做一些生意。他们说不知道做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那好吧,那我会到哥伦比亚来,直到我们发现一个生意我才会离开。
不是因为我的确有钱去投资这个生意虽然最后我的确有了一点钱,在那里待了两个星期后,我们找到了一个生意,他们说他们会做那个。他们其中一个人的父亲出了一半的钱,我说,那我将会从我爸那儿也搜刮一些钱,我也投资了一点。
当然在那两个星期以后我回去了MIT。虽然这些事情花了一点时间才发生,但是第一年之后,我就决定我要搬到哥伦比亚去在那个工厂工作,你想,这多让人激动,这也是我另一个疯狂的想法。但是因为那个工厂还没有弄好,在这期间我接受了另一份工作,大概有两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在一个工程的地方,某个工程公司。
我放弃了摩尔讲师的职位。那时候计算机才出现,我的工作是用计算机计算贝塞尔函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贝塞尔函数当然我后来学会了。他们需要计算贝塞尔函数用来制造天线。反正那是我做过的最繁琐的,可怕的工作,就是整天计算贝塞尔函数。
然后我就开始怀念学术界了,我一直和波特还有辛格,还有所有这些家伙是朋友,所以我就对辛格说:“我想我犯了一个错误。”然后他说:“好吧,我们会把你放在波特的合约里。”波特是在哈佛的一个伟大的数学家,那时候,如果你有一个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合同,合同通常非常松散,你可以用那个合同雇佣你想要的人。
所以我就在博特的合同里,然后我就回去哥伦比亚对他们说,我会让我的两个朋友运营那个工厂,我只是作为一个小投资者。
然后我就去做数学的工作。就像戴维提到的,我那时候在研究极小簇。极小簇是具有最小的面积或体积的流形,取决于它们相对于其边界的维度。所以一个肥皂泡通常是一个在二维空间的极小簇——不是一个肥皂泡,而是如果你拿一个线圈去蘸肥皂水,你会得到一个膜。
这将是一个最小的面积。所以我只是研究那个课题,基本上从第一定理开始。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非常分析化的。但我试图了解这些几何的东西,同时慢慢的研究并取得进展。
哈佛给了我一个助理教授的职位,所以我在哈佛待了两年,一年在波特的合约里,另一年是作为助理教授。但是实际上我不喜欢哈佛。我不知道这里也许有任何人来自哈佛来吗?--是的,我看到有人举手了。好吧,也许那时候如果你在那里,我可能会喜欢哈佛多一点(听众笑),我甚至都不认识你。
我不知道,那是一个沉闷的地方,同时它也在工厂之外。我觉得我又需要有一些改变。在普林斯顿有一个地方,称为国防部研究所的一个地方或是国防研究所的一个分析分支,他们现在仍然很强。
在那里,他们会雇用数学家。它是非常秘密的,高度机密的地方。他们的工作是密码和解密。事实上,在那些日子里,你不能说他们在做什么。所以我们只是——东西。但是现在他们的工作可以被允许谈论。我不知道密码和解码什么的,但我知道他们付很高的工资,同时你可以花你一半的时间做数学研究——最多一半,而另一半时间,你必须做他们的工作,这听起来很好了。
然后我就搬去了普林斯顿。我喜欢那份工作,我热爱关于那份工作的一切。我学会了使用计算机。我首先学会了编程,我以前跟本不知道怎么去写程序,也没有任何类似的技能。但是非常幸运在那里我可以向别人学习。我发现我喜欢算法,总是想着在计算机上测试它们。
有时候你可以用这个算法破解密码,虽然多数时候,它不工作。这个工作令人兴奋。我喜欢那里的人同时我仍然在研究极小簇的课题。我在两年之后,也许在第三年,我解决了这类关于极小簇科目的著名问题,如戴维所说的,我证明了你可以平滑的填充——在欧氏空间中的一余维。
所以在欧氏空间中,你可以有低一维度的边界,你也可以有低两维的曲线,类似三维空间中的一维曲线,不管怎样,如果你要填充,我证明了你可以平滑的无任何任何奇异性的填充,直到七维空间。
所以你可以有六维的曲面,七维的空间和五维的边界。我证明了这个定理可以成立。你也可以做一个统一的证明。但在再增加一个维度之后,我的证明就不成立了,我提出一个反例——但最后发现我不能证明它是一个反例。
它可以局部稳定,但可能没有全局稳定性,所以它是一个美丽的东西。你用一个三维的球穿过它本身,现在你得到一个六维度的东西,在一个实际上是八维空间中的七维球里面。
总之,边界有一个顶点和一个奇点。但是它的确是体积最小化的,从六到七维空间中的体积。这是个不错的结果,我发表了这篇论文,我所知道的关于最小簇的知识都写在了这篇文章里。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一切都很好。就象戴维说的,后来我获得了威伯伦奖,这也是我几年后想得到的。我为他们(国防部)做的工作也很好。这很美妙但如果你还记得,这是越南战争。你们都知道,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还经历过。
虽然就我所知,我不知道我们做的工作和越南战争有任何关系,.但是实际上,上帝才知道他们怎么利用了我们的工作成果,因为我从来就没有看到任何密码消息,我们也没有任何权限去接触那些东西.我们只似乎试图破解密码.
但是我不喜欢战争. 我老板的老板在华盛顿,他是一个名叫麦克斯韦尔.泰勒的将军。他被送更高层降职,管理着国防分析学院。他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文章,一个杂志的周日文章关于“在越南我们做的如此之好,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
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只需要拭目以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结论。嗯,我的意思是我不这么认为,我确信也有其他人不这么认为。所以我也给时代杂志写了一封信,说不是每一个为泰勒将军工作的人都认同他的观点。
实际上,我认为整件事情非常愚蠢(笑)。在那封信上的措辞比我说的要优雅但是表达的就是这个效果。我确信他们急切地发表了那封信。虽然我没有从我的上司那里听到什么,大家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我从我的朋友那儿听到了很多。
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一个年轻人把我找出去,告诉我他是新闻周刊杂志的记者。这个杂志现在应该还在,但是那时候,它是两大新闻周刊之一:它和时代杂志。他在为新闻周刊做一篇一个为国防部工作的人反对战争的故事。
他说:“我没有很多的读者因为.....但是我不知道我可以采访你吗?”好吧,我那时候29岁,从来没有人请求采访过我。所以我想,哦,你当然可以采访我。然后他就做了那个采访。在采访中我的底线是这么表达的:“国防研究院的规则是你必须花一般的时间为他们的事情工作,然后你可以花一般的时间做你自己的课题。
我的算法现在是----我在他们的工作上花费了我一半的时间——但战争结束时我可以花费所有的时间在数学数学上,我会弥补回这一切。
这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这是我在做什么。'是的,没错,因为——即使这不是真的但是很也接近真实了。无论如何,我做了我那天唯一明智的事情。我告诉我的老板我接受了这个采访。虽然更明智的事情是我在接受采访之前就告诉他,但是我没有,我在之后才告诉他。
他说:“你接受采访了,你说了什么?”我说我告诉他们我的一半时间在研究另一半时间做自己的东西等等。他说:'我必须给泰勒将军打电话。'他的老板。他打了电话。
我记不太清楚了他是当着我的面打的还是在我离开房间以后打的。但是好像在一微妙之后他就告诉我:“你被解雇了”。我说。你知道,我的工作头衔是永久成员....(笑)....这套衣服的永久成员。他说:“以前这个职位通常都是临时的,让我告诉你永久和临时成员的区别,一个临时成员有合同,一个永久的成员没有。
”所以我没有人站住脚,他们也许给了我一个星期的遣散费,我不记得具体的交易了但是也许他们可能更慷慨。
好吧,我就那样了,没有了工作。我有一个妻子,三个孩子然后还待业。但是你知道,我证明了这个定理,我知道我能得到一个学术职位。所以我不是真的在害怕。被解雇实际上让我觉得兴奋。我认为这是个好的结果。当然你不应该让这成为习惯。
你不应该让被解雇成为习惯但偶尔有一次也许是有益的。无论如何,就像戴维说的,我得到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市分校的一个系主任的职位,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最好当开除别人的人而不是被开除的人。那个系并不强,他们有一个伟大的物理系。这是一个非常新的大学,我有了一段美好的时间搭建一个系。
然后我遇见了杨振宁,那个著名的物理学家,他那时也在那个学校。我们成为了朋友,也有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互动。几个月后,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告诉我他那时候在做什么。我对物理一窍不通,但是你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我想我应该去那儿听一堂课。所以我坐下来,他给我一个充满方程的黑板。但是我我一点都不明白,我一点都不懂物理。但是你知道,我看了又看---试图看起来尽可能的聪明。最后我感谢了他就下楼回去了。
我们第二年,第三年又重复了同样的事情。但是在第三年的演讲当中一些事情发生了,他似乎给我演示了相同的方程。它们变得熟悉。然后我意识到,我说停,停在那儿。他说,“为什么要我停下来?”我说因为你试图发明的数学,是30或40年前就已经完成的。
他说,“什么?”你知道,他在做的是规范场理论,他用的是束同时他们有关联。但是我认为他不知道你还可以有个东西叫做平移还有乐群等等其他东西。他正在痛苦的试图在一个连接的束里建立一个平行变换。
我说,你知道吗,数学家已经解决了那个问题。他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一类的东西?”我说““嗯,因为这些数学看起来很美,自然的它就被发现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是刚出来的数学。
那时一个美妙的时刻。然后他组织了一个讲座,包括了这个学院里的一些成员,还有粒子物理家。这基本就是一个翻译研讨会,因为我们说这个,他们说那个,杨甚至写了一个专业词汇表。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这些事情的书。
但是这是我所遇见的最聪明的一群学生,还有他的整个教师团队。所以,你知道,我必须——但它是伟大的。他们最后给了我一本很厚的字典,因为我的拼写太差。他们给了我一个几乎重达100磅的东西作为一个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