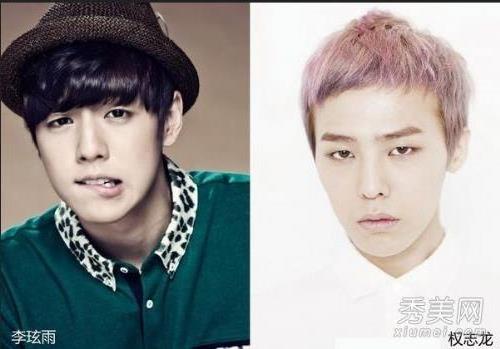徐复观形而中学 韩星:徐复观形而中学探微
摘要: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徐复观与现代新儒家其他同仁同途殊归,反思批判学界以西释中,中话西说,试图重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其“形而中学”是以先秦儒学的心性之学为思想渊源,与后来程颢、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一脉相承发展而来,“心的文化、心的哲学”是其主体。

他所说的“心”是通过修工夫确立的“本心”,是建立人生价值以及道德、艺术、认知的根源,是人之为人的主宰。心的文化具有人文性、实践性、现实性,是生活化、大众化﹑社会化、和平的文化,也不抹煞思辨的意义,可以统合形而上与形而下。

形而中学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下的“形而上学”,它居于道器之间,通过修养工夫使天道落实到生命实践之中,并开出道德、艺术、宗教、知识等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性的差异。形而中学有经典的依据,已经有越来越的学者认同与阐释,对于中国文化和儒学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徐复观;中国文化;主体性;形而中学;心的文化;生命实践
一、徐复观形而中学的思想动因
徐复观身处国家民族分裂,社会动荡不安的20世纪,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自身衰微和西学东渐的冲击,怀有一颗“感愤之心”,1944年往勉仁书院拜谒熊十力为师,悟其师“亡国者,常先亡其文化”警世之言,乃潜心研读中国文化典籍。

到台湾后,从政治圈转向学术界,希望通过中国思想史、儒学史的研究,对中国文化、儒家思想进行重新诠释,揭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找到救治时代病症的良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他与唐君毅、牟宗三等海外学者一起推动儒学现代化研究,被称为第二代“新儒家”领军人物。
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这一思潮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兴起作出了独特的贡献。1958年,他与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联合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成为新儒学思潮在港台地区崛起的重要标志。
在学术上,徐复观先生不肯研究纯哲学,觉得太空玄,也不愿意单纯考据,觉得太死板,因此,他选择了中国思想史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他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影响,加上他独有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使他更关注现实生活,无意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做思辨型、书斋型的学者,而是通过思想史论、时政杂文,致力于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学术与政治之间思考和探索,力图发掘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把儒家政治理想与民主政治追求结合起来,把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以建设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中国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
与其他现代新儒家一样,他对近代以来知识界不遗余力批判中国文化、肆意诋毁中国文化极为不满,以为目前中国所需要的一种精神自觉的运动就是要对中国文化有重新的再肯定。不过与其他新儒家学者相比,徐复观的学术成就不是对新儒学理论做多少阐发,而是比较多、比较系统地通过对中国思想史、儒家思想史的深入研究和解读,揭示中国文化的深层底蕴,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在他看来,“今日要论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之地位,与其从和西方文化有相同的地方去看,不如从不相同的地方去看”[①],许多谈中国文化的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有的甚至仇视中国文化;即使在爱护中国文化、所得很精的哲学家当中,亦有很多人没有把握中国文化的“真面目”,“这些年来谈中国文化的人士,不论站在正面或反面的立场,都忽略了文化性格上的不同,而仅拿同一的尺度去夸张附会。
凡说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这是拿西方的文化做尺度去衡量中国文化;凡说中国文化是超越的,这是拿中国的文化尺度去衡量西方文化。
殊不知以一个尺度去衡量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恐怕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②]他指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发轫之初,其动机已不相同,其发展遂分为人性的两个方面,而各形成一完全不同性格。
”“不论好和坏,中国民族统一的性格,是在汉代四百年中由儒家精神所陶铸、所定型的。儒家精神,二千年来,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正面的或反面的,浸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实际生活中。”[③]因为中西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若盲目比附西方形而上学,不仅不能发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反而会误导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陶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尽管他与现代新儒家的其他同仁有着大致相近的文化观和思想趋向,但在对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和儒家精神的把握上又有最大差异。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说:“中国历史文化中道统之说,……乃源于中国文化之一本性”。
关于这个中国文化的“一本性”,他们认为“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也就是以心性学说为儒家道统的本原。“古文尚书所谓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固是晚出的。但后人之所以要伪造此说,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为中国道统之传之来源所在,亦正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
”“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道德实践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
”[④]以心性之学的“一本性”为基础,在思想体系的构建上,从冯友兰、贺麟,到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等人大都援西入儒,以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为思想资源,以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改铸和重塑儒家哲学,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体系。
冯友兰吸收、融会近代新实在论理论和逻辑方法等基础上对宋明程朱理学加以发展,提出了“新理学”。以《贞元六书》为标志,以真际实际两世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境界为骨架,构筑了一个完整庞大的新理学体系。
贺麟在吸收、融会近代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基础上对宋明陆王心学的发展,提出了“新心学”体系。唐君毅也有良好的西方哲学的训练,经历了由西学而儒学的道路,阐释儒家人文精神,分析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宇宙万事万物看作都是求超越的过程,生命存在不仅是为存在而存在,乃是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灵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从现实的生活逐渐向上求更高的价值,最后止于天德与人德一致的最高价值世界。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主要构造者和集大成者,他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渊源、流变以及精髓进行创造性的阐发,完成了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强调道德主体的挺立对于完善人格的意义,并通过良知的坎陷而转出知性主体,由内圣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外王,又分疏道统、学统、政统,揭示儒家文化的多层次性。
现代新儒家把儒家形而上学步步深入,发挥到了极致,正如林安梧所评述的,现代新儒家“就是通过整个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的整个传统,重新去验证它,而这样验证的方式基本上就是把整个当代儒学接到宋明理学的陆王心学,而把陆王心学往上提,通过熊十力到牟宗三把它提到一种超越的层面,比较形式面地来谈这个道德本心,而最后往上提,几乎把它提到一个超越绝对的地步”[⑤]。
这样的结果是在新儒家思想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其形而上学的过分追求,使得其思想体系局限于逻辑与思辨的精致的象牙之塔之中,与现实人事疏离,缺乏对现实的沟通与融涵。
徐复观不同于他的师友们,当其它人致力于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构建的时候,他却拒绝对儒家的义理作形而上学的探求,而是本着“中国文化的研究主要应当归结到思想史的研究”的原则,精心地对中国文化的演变历史进行梳理,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进行探究。
针对现代新儒家主流,徐复观先生批评道:“有如熊十力以及唐君毅先生﹐却是反其道而行﹐要从具体生命﹑行为层层向上推﹐推到形而上的天命、天道处立足﹐以为不如此便立足不隐。没有想到﹐形而上的东西﹐一套一套的有如走马灯﹐在思想中上从来没有稳过。
熊﹑唐两先生对中国文化都有贡献﹐尤其是唐先生有的地方更为深切。但他们因为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弄颠倒了,对孔子毕竟隔了一层”[⑥]。在他看来,“这种比附多系曲说,有没却儒家真正精神的危险”[⑦],“所以拿西方的形而上学来理解儒家的思想,尤其是混上黑格尔的东西,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增加两方的混乱,无半毫是处”[⑧],他批评现代新儒家以西学的方式来构建儒家形而上学体系的努力,“硬拿着一种西方形而上学的架子,套在儒家身上,如‘新理学’等说法,这便把儒家道德实践的命脉断送了”[⑨]。
徐复观的这种思想被学界概括为“消解形上学”[⑩],或“离开形上学”[11],其实在我看来正好是他反思批判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以西释中,中话西说,试图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努力。
二、徐复观形而中学的思想渊源
徐复观的形而中学是在对先秦原始儒家深刻把握后阐发出来的。他考察中国思想的源头,特别是孔子,发现孔子的思想并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路。《论语》孔子有许多关于“道”的论述,具有形而上的意蕴,但“孔子追求的道﹐不论如何推扩﹐必然是解决人自身问题的人道﹐而人道必然在‘行’中实现。
行是动进的、向前的﹐所以道也必是在行中开辟。《论语》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有上下浅深的层次﹐但这不是逻辑上的层次﹐而是行在开辟中的层次﹔因此﹐这是生命的层次﹐是生命表现在生活中的层次。
‘下学而上达’(《宪问》)﹐应从这种方向去了解﹐否则没有意义。”[12]他阐发孔子的天命观说:“天命对孔子是有血有肉的存在,实际是‘性’的有血有肉的存在。这不仅与周初人格神的天命,实有本质的区别;并且与春秋时代所出现的抽象性的概念性的道德法则的天、天命,也大大地不同。
……他之畏天命,实即对自己内在的人格世界中无限的道德要求、责任而来的敬畏。性与天道的融合,是一个内在的人格世界的完成,即是人的完成。
”[13]他自己的看法是:“孔子乃是在人人可以实践、应当实践的行为生活中,来显示人之所以为人的‘人道’;这是孔子之教,于一切宗教乃至形而上学,断然分途的大关键。
”[14]这就是说,孔子是在人的生命实践中显示儒家的人道,孔子的思想与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不同,成为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分途的大关键。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不是像西方哲学家那样是人为地在斗室里构建出来的,而是在自己生命成长、人格提升过程中,在性与天道的融合中完成的,所以它具有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维度,但不是宗教神学也不是形而上学,由此形成了中国思想形而中学的基本特质。
他又说:“中国文化,主要表现在道德方面。
但在很长的时间中,对道德的价值根源,正如其他民族一样,以为是在神、天。到孔子才体认到道德根源乃在人的生命之中,故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又说:‘为仁由己。’这些话都表明价值根源不在天,不在神,亦不是形而上的,否则不能这样‘现成’。但孔子并未说出是在生命中的那一部分,亦即是未点明是‘心’。”[15]后来经过《中庸》到《孟子》的发展,才最终点明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