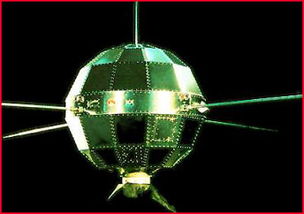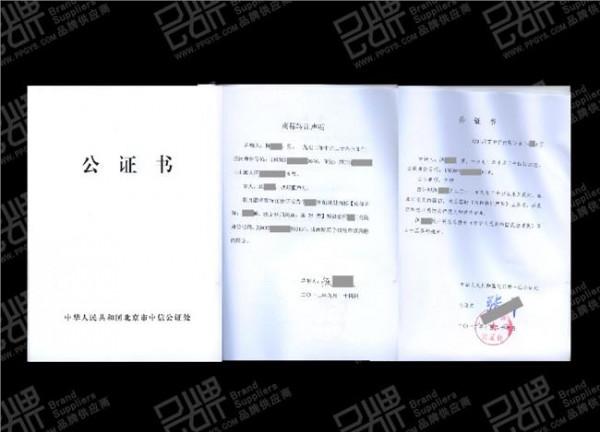于坚尚义街六号 刘春:关于《尚义街六号》
这是一首关于青年时代的生活与友谊的诗歌,全诗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阅读时不会遇到丝毫理解上障碍。和几乎所有同龄人一样,我最初接触到于坚的作品是他创作于80年代的《作品39号》、《作品52号》、《尚义街六号》等被人们广为传诵的篇章,它们与《有关大雁塔》(韩东)、《你见过大海》(韩东)、《中文系》(李亚伟)、《卡尔·马克思》(尚仲敏)、《瞄准》(京不特)等一道,把诗歌从“朦胧”艰涩造作中解放了出来,显出率性、自然,有原汁原味的生活质感。
尚义街六号,这座“法国式的老房子”无疑是中国诗坛最为著名的建筑物,出入其间者表现出来的贫穷中的乐趣令人向往不已。
《尚义街六号》这样的口语诗也是于坚最为擅长、影响最深入人心的风格,它语言浅近,内容生活化,并呈现了许多极富幽默感的细节,人们从中既可以感受到文学的魅力,也能察觉日常生活诗意的一面。
这首诗语言虽然平实浅近,它的创作时间却扑朔迷离,在一些版本中,写的是1983年,一些版本写的是1985年3月,更多的版本标注着“1984年6月”。2009年6月3日,我从刚刚收到河北《凤凰》杂志上读到于坚的随笔《这是一封信》,文中提到了这首诗,写作时间又变成了1985年6月。
有时候,甚至同一本书所标记的时间都互不相同,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于坚的诗》,在《尚义街六号》一诗后面注明的创作时间是1984年6月,而书后附录的“于坚文学年表”中,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则为1983年。
好在不管是哪一年完成的,都不影响这首诗的品质。——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文坛,有一些诗人作家故意做假,将自己的代表作写作时间推前,以期为自己在文学史中争取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而于坚的影响,不需要搞这些小动作。
为此,2009年6月9日,我专门去信向于坚求证,很快得到于坚的回复:“《尚义街6号》1985年3月是对的,我还有原稿,时间出入主要是一般发表不注明时间,所以编诗集时只是凭记忆。其他诗歌也有这种情况。”
《尚义街六号》完成后,似乎曾经在《他们》和《高原诗辑》上发表过,但反响只限于小圈子内。获得更大的影响是在1986年11月《诗刊》头条位置发表之后,口语诗在全国范围内掀起风潮,于坚从此成为当仁不让地“第三代诗人”的元老级人物。
这首诗没有人们习见的象征和隐喻,凭着洋溢其间的出众自如的语感,使得这首内容“普通”的诗歌具有了深刻的诗性光芒;加上字里行间屡屡可见的机智与幽默,恰好印证了于坚1984年的短诗《我的歌》中的一句:“像上帝一样思考,像市民一样生活。
”讨论于坚作品的文论,鲜有不提及此诗的。这首诗也证明了:真正的口语诗写作,不是泛泛而谈,不是蜻蜓点水,不是“口水”,而是从生活的土壤里沉淀、淘洗出金子的写作。
从诗歌平实的表述方式,我们可以猜想到这首诗是的写实程度。诗歌里提起过不少人,吴文光、老卡、李勃、朱小羊、费嘉等,都是于坚当年的朋友,在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人“聚啸山林、诗酒风流”的洒脱。而诗中所写,也都是发生在当年的真实故事,包括这些人的去向都是真实的,比如朱小羊和吴文光先后去了新疆,李勃家在北京,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费嘉则是一个颇有才华的诗人……
于坚是如何看待《尚义街六号》和自己的写作呢?在给我的邮件中,于坚这样写道:“这个诗最重要的东西是幽默感。在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已经完全没有幽默感,铁板一块。不仅仅是日常生活、小人物,同时也有其他诗人写这些,但以调侃的口气写的并不多见,也就是我吧。
王朔们是在我这么写以后很多年才出现的,但已经玩世不恭了。另外,我强调日常生活,就是将日常生活神圣化。文革使中国生活声名狼籍,生活世界被理直气壮地摧毁着。重建常识、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就是在今天也非常重要。
我并非所谓世俗的诗人,我其实比那些故意追求的神圣的神圣得多。这种神圣来自对汉语本身的信任,语言本身就是神圣的。尤其是汉语。……我的神圣而不是被某些诗人故意赋予的所谓神圣,神圣在许多诗人那里,只是从西方学来的观念。
我的神圣是汉语本身的神圣,起源性的神圣。拒绝隐喻,就是要回语言被意义的陈词滥调遮蔽了的神圣性、纯洁性。我其实是把我那些朋友当作经人物、仙人来写、他们在我心目中决不是小人物,而是我生活世界中的天才朋友。
我调侃的恰恰是那时代把天才视为庸人。这种神化日常生活,李白在酒中八仙歌中就做过了,只是时代风气不同,他的时代殷实,所以他喜欢夸张。而我是在二十世纪为了掩盖真相而夸张成性的时代中回到事实。世俗化可以用于我之后的那些诗人,我并不世俗,我其实是升华了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神圣化了。”
我相信,于坚上面这番话,对很多诗人和诗歌批评家,会有醍醐灌顶的作用。我们只知道诗人写世俗生活,却不知道他为何而写;只知道有很多诗人用口语写作,却不知他们之间的区别;甚至是于坚提出的那句著名的“拒绝隐喻”,很多人的理解也仅仅限于修辞方式,却不知诗人强调的是回到语言被意义的陈词滥调遮蔽了的神圣性和纯洁性之中。看来,要理解一个诗人,仅仅阅读他的作品是不够的,还需要善于倾听他的心声。
尽管正如诗歌所说,“大家终于走散”,但“尚义街六号”这座“法国式的老房子”已成为中国诗坛最为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常常被人提到,“很多年后的一天/孩子们要来参观”。我就是诗中写到的“孩子”之一。2001年10月,我去西双版纳旅游经过昆明时专门去找了一趟,遗憾的是在原址我只看到一排卖窗帘的低矮店铺。这个时代不需要诗意,它更相信钞票。
记得当时在昆明和雷平阳喝酒时,雷平阳要邀约于坚,不料后者恰好不在家,于是见面的机会延后了5年。2006年6月,在长沙举办的当代诗歌名家麓山诗会上,我们才得以见面。记得于坚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办的扬子鳄诗歌网站不错,纸版还出吗?我回答说,这几年诗坛有个趋势,就是民刊与官刊似乎无甚区别了,扬子鳄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定位,又不想接受赞助,出了5期之后就未再出版了。
在那次诗会上,于坚的光头是最受与会诗人青睐的背景,许多诗人拉着他要合影,我自然也不会免俗,但事实上,最终我们都没有收到相机持有者寄来的照片,等于是白“秀”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