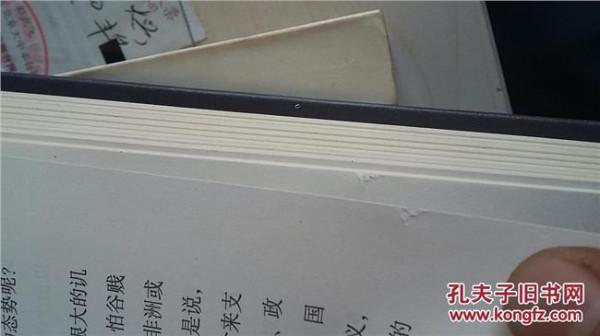杜维明儒家与自由主义 论争、对话与融合: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张力
原标题 [论争、对话与融合: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张力]
唐宏站,男,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本文出自博士论文《“自由”之思:宋明儒学的哲学精神谱系》。 博士导师:湖南大学教授章启辉 通讯评委:武汉大学教授吴根友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何卓恩 自从晚清民初“自由”的理念通过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传入中国,儒家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和对话就已经拉开了激荡人心的序幕:维新变法所引发的“宪政”和辛亥革命所推动的“民主”两大思潮席卷中国。
由于当时维新派、革命党与顽固派、保守派正处于政治上“你死我活”的斗争状态,因而,论战无法跨越政治立场的“鸿沟”,思想和理论上的对话也不可能在一种平和理性的状态中进行。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情形大有改观。随着一大批接受了“欧风美雨”洗礼的知识分子回国,保守派也丢掉了政治立场的包袱而逐步走向“文化建设”的阵地,思想和理论界的论争和对话达到了全新的高度。
在当时最为著名的两场知识分子的论战中,如果说“问题与主义之争”主要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展开,那么“科玄论战”一定意义上就是以新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大思想阵营间展开的激辩。
“科玄论战”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分别属于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两大阵营。
张君劢明确提出“人生观是自由意志的,科学对人生观无法解释”。他说:“科学之中,有一定原理原则,而此原理原则,皆有证据。”而人生观“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同为人生,因彼此观察点不同,而意见各异,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
张君劢先生认为,中国儒家的观念,如“万物之有”,“致知穷理”,“心之同然”,“形上形下相通”等等,都与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有着“同条共贯之处”,因此,“在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足以导致中国现代化的基本方法”,“这种新的思想方法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
”对于张君劢将人生观的解释和诉求归诸哲学或玄学的理路,丁文江等人斥之为“玄学鬼”。
他们站在推崇和发扬西方科学理性的立场,对张君劢的“自由意志人生观”进行了激烈批评。 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第二次大的论争发生在港台新儒家与集合在《自由中国》、《文星》等杂志的雷震、殷海光、张佛泉、李敖等“西化派”知识分子之间。
其中,尤以徐复观和殷海光两人之间的对话影响最大,成为学人关注的焦点。 1952年,牟宗三先生在香港《自由人》杂志上发表《一个真正的自由人》,指出哲学上的“逻辑分析”和“纯技术观点的自我封闭”及其在理论上的局限与在现实社会中的困境,展露与揭示含藏在现实的人性人伦中的客观意义与文化意义,强调“事实界与价值界都须正面而视,逻辑域与道德域,无一可废”。
随后,殷海光撰文对牟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情绪化的攻击,并在《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自由日谈真自由》。
在批判“国家自由”的观念以外特别批判和反对“意志自由”。由于“西化派”知识分子不断推波助澜,有“勇者型的新儒家”之称的徐复观先生站出来予以积极回应:“我一样认为仅靠道德不能解决政治问题;道德的自由不能代替政治的人权自由。
并承认实现政治上的自由,为实现其他自由的先决条件。但我不觉得道德一定要和政治隔离,道德自由一定要和政治自由隔离。
”此次论战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后来,殷海光承认与新儒家的对垒是“大大失策的事”,且对自己所执持的逻辑经验论做了批判,并声称须就“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一问题下功夫进行研究。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逐渐受到广泛质疑,越来越多的学人转向试图会通中、西两种文化。其中,把自由理念与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并体现出较强思想原创力的最早应是孙中山和熊十力,如孙中山对“国家自由”的强调和对自由与纪律关系的辩证诠释,以及熊十力先生所言“古代儒家政治理想,本为极高尚之自由主义,以个人尊严为基础,而相互协和,以成群体。
期于天下之人人各得自治,而亦互相联属也。
春秋太平之旨在此”。而在儒家和自由主义之间不断深入开展对话的现当代学人,则以周德伟和杜维明两位先生最为勤勉不懈,他们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也是最具代表性的。 作为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巨擘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第一位中国弟子,周德伟先生在《西方的自由哲学与中国的圣学》一文中经过细致分析指出:中国圣学“仁法”、“治法”、“义法”观念与西方三千年前产生之“自然法”、理性法观念以及十九世纪西方大法理学家萨维尼的思想理念完全相通;孔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与苏格拉底“确认吾人之无知乃智慧之起点”相通,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名言已充分肯定了人的自由创发能力,“过则勿惮改”的教诲则可适用一切试验及研究程序。
更重要的是,以圣学中“克己复礼为仁”、“义者利之和也”以及对夏殷周三代之礼“损益”的态度,与西方自由哲学比较来看,后者尊重传统、以经验为准绳而非高举理性独尊之大旗推到一切,重视各种自发生长的制度而非人为杜撰的“乌托邦”。
这与圣学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而圣学中对“正名定分之礼”突出地位的强调和“以礼节之”、“隆礼重法”等言述与哈耶克推崇“法治之下的自由”亦可相互印证。
杜维明先生在题为《儒家与自由主义》的长篇对话中,汇集了“哈佛儒学研讨会”花了两年时间讨论有关问题的想法和思路,涉及西方基督教、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各种理论思潮,深刻切入诸多基本议题。
在这篇可能是近年来有关儒家与自由主义对话的最有价值的文献中,杜维明先生还特别强调了儒家内部的思想教条(如“学孔子”之类论说、官学的确立等)与对这种教条的反对(明代思想家认为“学做人”最重要、王阳明对已上升为官学的朱子之学的批评),认为“在儒家传统中,充满了讨论、论辩”,“严格地说,没有不可讨论或引发争论的教条”。
因此,儒家传统“有非常强烈的开放精神,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最后,他还就儒家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及其掌握的文化资源包括“主体性、为民请命,民族性、文化历史传承的信念和使命感,还有超越境界”等等进行了分析,并对古代中国皇帝、官员、职位与公私的界分做了提示。
在现当代儒学研究的百年征程中,“基于文化会通的思想原创”可以说是一项最具难度和挑战性的工作。
因为它要求研究者既对中国儒家传统有“致广大而尽精微”的认知,同时也要求对滥觞于古希腊而在近现代西方诸国形成波澜壮阔之势的自由主义学理有深刻而全面的把握。
这是一项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依然有不少东西方学人发扬中古时期鸠摩罗什、唐玄奘和近世徐光启、利玛窦等伟大先贤的精神,寸积铢累,循序渐进,取得了极为宝贵的成果,其中尤以徐复观先生“文化自由主义”或曰“自由—保守主义”的思想理论形态和美国汉学名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对宋明新儒学自由传统的新阐发为最突出的典型。
总之,儒家与自由主义的论争、对话与融合,呈现出两者之间存在的巨大张力。
这种张力既显示了两者的差异,又对两者的会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论争、对话中,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儒家传统不断寻求自我更新的艰难求索,以其所取得的丰富成果向我们指示了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