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出狱满一年 称适应社会比适应监狱还难
华容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家陪伴父亲。找到共同关心的话题并非易事,于是他们有时会一起看电视,看影碟,在其间找到一些交流机会。某个周末的晚上,父女俩坐在客厅一起看一部著名的监狱题材的美国大片——英语对白的《肖申克的救赎》,它讲述一个银行家蒙受杀妻之冤,用了19年时间掏开一条悠长的暗道,重返自由世界。片子是一位记者朋友特意给佘祥林寄来的。佘祥林眼睛不好,电视画面勉强看得清,字幕却是一片模糊。

华容有时会给他讲解影片对白。他告诉女儿:“你不用讲,全都看得明白,我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影片中有一个叫布鲁克斯的老头,坐了50年的牢,对重返社会深怀恐惧,获得假释后,他甚至无法适应最简单的工作和生活,只能在一家小旅馆的房梁上凄惨地自缢,以求解脱。这一幕,深深刺痛了佘祥林的心。

看完《肖申克的救赎》,佘祥林家整整一天都笼罩在压抑的气氛中,这是一年来未曾有过的。
华容今年19岁,身材瘦小,言语不多。因为家庭悲剧的压力,她15岁就中途辍学,南下广东打工。女儿是懂事的,佘祥林看得出,从自己出狱那天起,已经七八年没见的华容就在努力营造一些亲热的气息。然而,11年脱离社会的狱中生活,已很难让这位父亲跟上年轻女儿的思维。

华容曾经染过红头发,在佘祥林的反对下染回了黑色;她喜欢韩国的青春剧,是超女的粉丝,而她的父亲只知道“超女”这个字眼,甚至都叫不出李宇春的名字。
父女俩都刻意避免回到过去,“她不问我监狱的事,我也没问过她打工的事。”

华容对父亲的评价是:从心态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孩子。
28岁到39岁,佘祥林在看守所和监狱度过,他说那是自己的黄金年龄。11年里,国家不可能停下来等待一个蒙受了冤屈的囚犯,相反,佘祥林出狱后发现,“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说起过去一年的处境,一字一顿地用四个字来概括:举步维艰。“适应社会,适应城市,真的比适应监狱还要难得多。”
28岁到39岁,佘祥林在看守所和监狱度过,他说那是自己的黄金年龄。11年里,国家不可能停下来等待一个蒙受了冤屈的囚犯,相反,佘祥林出狱后发现,“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阶段。”
“我这一生,怎么遇到的都是急转弯。”佘祥林时常陷入这样对命运的诘问。
适应自己的“罪犯”身份,这是他所经历的第一次“急转弯”。
在监狱里,对于自己的冤情,佘祥林只是私下和一个比较要好的狱友说过。“平时怎么可能和别人说,谁会相信啊?你必须把自己当作罪犯。”按规定,犯人每个月都要写一两份思想汇报。汇报的内容,无非是表达自己认罪服法、认真改造的态度。
佘祥林后来告诉朋友,写那些思想汇报的时候,他有时会难以自持,因此摔断了好几支钢笔。
仅仅表现出努力改造的姿态是不够的,离开监狱监管者的视线,佘祥林还要在言谈举止上“扮演罪犯”——以前从不骂人的他,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也要满嘴脏话,还要学会撇着嘴角说话,斜着眼睛看人。
刚回到自由世界那几天,佘祥林有点受宠若惊,“每个人都对我友好,都对我微笑,这让我不习惯。”他甚至不知道把自己的手和脚放在哪里。偶尔走到外面,他还是习惯于轻声说话,人贴着墙根,头低得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我还算不错呢,没有在街上见到警察马上立正。”佘祥林自我揶揄着。
雁门口镇上,有佘祥林的一个狱友,刚放出来的时候住在一所学校附近,每天早晨八点学校一打铃,这位狱友就产生条件反射,赶紧穿戴整齐,几乎就要冲出房间去集合了。
佘祥林说起过去一年的处境,一字一顿地用四个字来概括:举步维艰。“适应社会,适应城市,真的比适应监狱还要难得多。”
摆脱不掉的阴影
4月6日中午,在胜利四路的一家小餐馆,佘祥林和朋友点了一份干锅鸡。另一桌坐了七八个人,随后也点了一份。第一道干锅鸡,服务员端给了那一桌,佘祥林显得很生气,他质问服务员:“你看他们人多,他们有钱,就给他们先上菜吗?”他表达愤怒的方式并不暴烈,只是直盯着对方,声调略有提高。
菜上来了,佘祥林喃喃自语:现在的人怎么利益心那么重?
餐馆厨房抽油烟机的声音稍微有些大,这让佘祥林很烦躁,“我很怕吵闹。”
那顿饭接近尾声的时候,佘祥林伸手拿起牙签盒,牙签盒却突然摆脱了他手指的控制,佘祥林急忙反手去抓,塑料茶杯被他的右肘轻轻一刮,翻转起来,半杯茶水洒了一身。佘祥林因二两白酒而微红的脸突然阴下来,反复嘟囔:“我怎么连这么轻的东西都拿不住了?”
过了一会儿,他拿着塑料茶杯起身走向饮水机,刚要接水,茶杯竟也鬼使神差地脱离掌心。
佘祥林坐回座位,足足半分钟时间,他双手抓住头发,一言不发。
“我是不是身体要完了?”他猛地站起来,推开椅子,“下午回家!哪也不去了,今天太怪了。”
回家时,路过长江边的码头,他告诉身边的朋友,路边那个算命的老头算得非常准。“许多人劝我信教,我不信,但我信命。”佘祥林接着发出一声叹息,“可是,算准了又能怎么样呢?”
到了宜昌后,佘祥林的心事变得愈发沉重,他几乎每天只吃一顿饭,“吃不下去,没这心思。”出狱时,他体重差不多有150斤,现在只剩下130斤。
“睡不着,每天最多睡两三个小时,这样的状况已经有十几年了。睡着了也是挺可怕的事,会做各种各样的梦,全是噩梦。”佘祥林说,梦里出现最多的是母亲和女儿,母亲全是12年前的样子,女儿也是。在梦里,幼小的华容头发散乱,满脸泥污。
哪怕是撞上一根飘浮的鸡毛,都有可能让佘祥林陷入深思。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听到年轻的母亲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他居然能怔怔地坐上好久。
为了分散精力,没事的时候,佘祥林就拿着笔在纸上胡乱写字、画画,那些内容自己都看不懂。他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画警察。事实上在入狱之前,他的工作也是一个类似警察的角色——京山县原马店派出所辖下的治安巡逻员。
在宜昌新家的多数时候,佘祥林需要独自面对雪白的四壁。他时常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往阳台方向走,会有一个决定,往厨房方向走,可能就会冒出一个相反的念头。
佘祥林觉得自己的脑袋里一直存在着一场战争,它甚至要延续到餐桌上——佘祥林喜欢吃辣椒,喝白酒,这些可以缓解腿部病痛,但这样的饮食习惯又会伤害眼睛。那是长期监狱生活留下的后遗症。
“腿上的关节平时就别扭,阴雨天会疼得直咬牙;眼睛在武汉确诊为眼底黄斑,问起是否会瞎,专家说得很吓人:好好保养可能会有转机。”佘祥林笑称,眼睛管天,腿脚管地,现在他的“天”和“地”都快完了。
高兴时,佘祥林会轻声哼唱几句《说句心里话》,那是他记忆中的新歌。即使是这样的哼唱,在他的生活中也极少出现,更多时候,他像被漩流裹挟的一片树叶,那漩流的名字,就是焦虑。
人群让他焦虑,工作让他焦虑,情感让他焦虑,自身让他焦虑。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融入社会,成为普通人。一年过去,这个进程却缓慢得像蜗牛爬行。
在秦发等朋友看来,佘祥林是那么积极、努力地融入新的社会,而令人担忧的是,他也因此显得心情过于急迫,精神压力巨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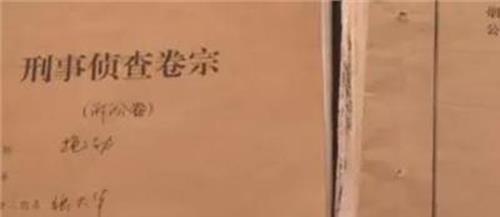
![佘祥林案分析 直播中国:专家关注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图文]](https://pic.bilezu.com/upload/7/df/7dfac615a0eb84cbe2b78335cbfff195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