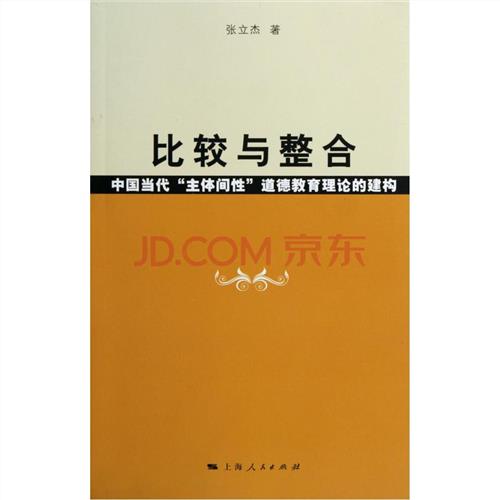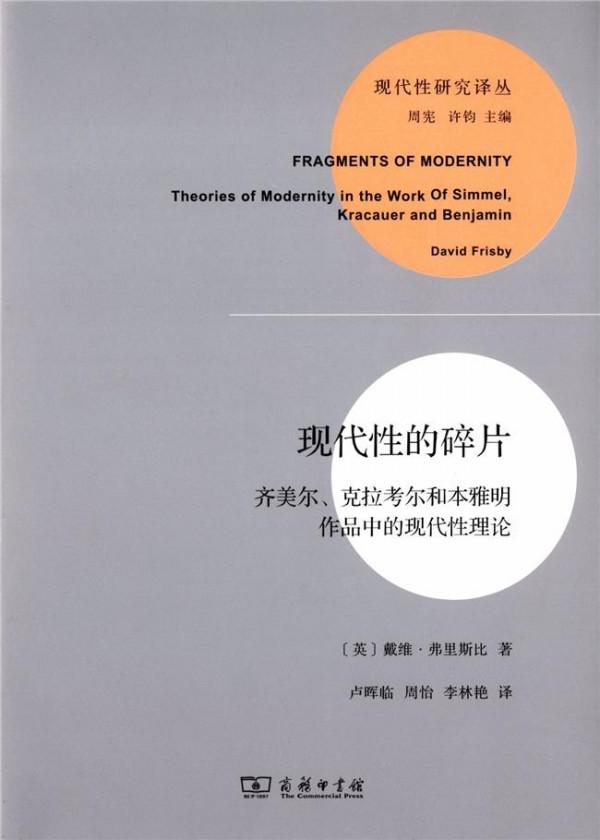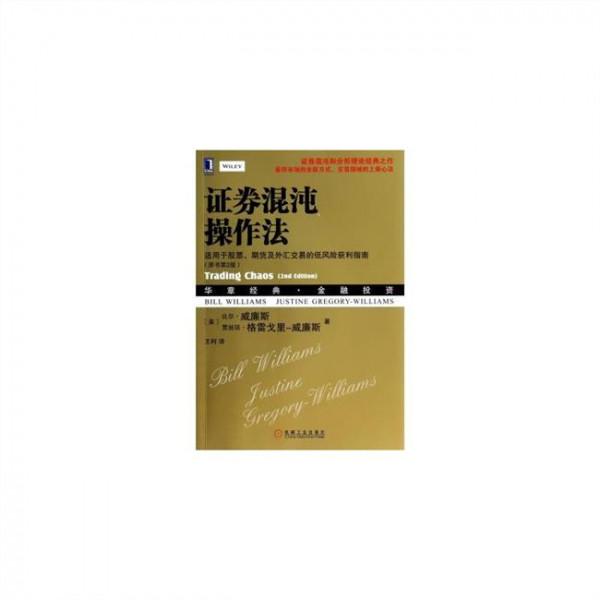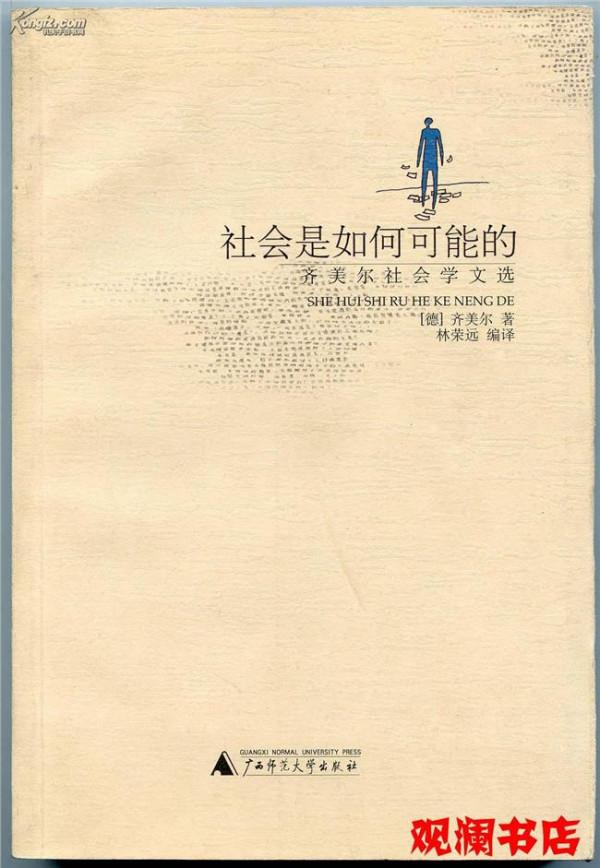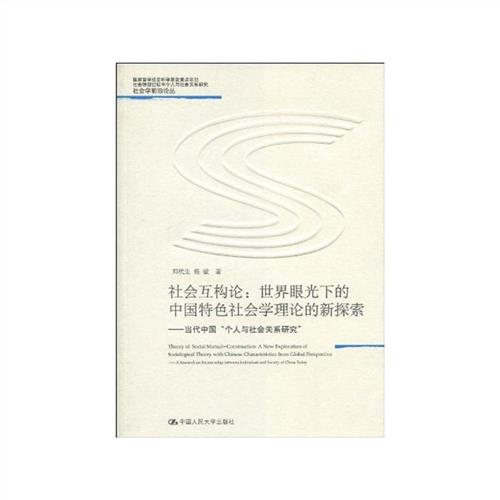舒茨陌生人 《陌生人》与《返乡者》——舒茨对生活世界的诠释
他发现自己最终作为一名返乡者回到了一个并不属于他的世界。他从此被囚禁于日常现实之中,如同被囚于牢狱之中。他在此受着最为严酷的狱卒的折磨。而这一狱卒,就是自知其界限的常识理性。
《社会学研究》2011年5期,24000字
■孙飞字
1944年所作的《陌生人》
(Stranger) -文中,舒茨关注到日常生活之外的行动者的形象。作为“我群群体”最大之确定性的日常生活,对于作为他者而存在的陌生人来说,却意味着意义危机。在常识世界之中的“我能够再做一次”这样的状态,所表达的其实是一个稳定的日常生活所能够给予行动者的确定性——是行动和行为二者之间的统一。
只有在这一状态之下,行动者才可以做到“照常思考”。而在陌生人的世界中,这一状态变成了危机。在此状态之中,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历史一社会性质被清晰地解释出来:“文化模式不再作为一种手头的、经过验证的方法系统而发挥功能;它表明,它的适用性只限制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
对于生活在常识世界之中的人而言,震惊( shock)只是从一种次级意义域跃迁到另外一个意义域时所经历的状态。而对于陌生人,震惊的状态则是一种时时经历的“常态”。由于陌生人并非“其社会环境的中心”,所以他自身的文化模式就变成了碎片状态:“矛盾,散漫,并且缺乏清晰性。”在此状况下,陌生人所处的新世界,并不能够为他提供一种针对我群群体的保护机制;恰恰相反,这一世界乃是一种迷宫的形象。
这一陌生人的形象并非是没有家乡的。实际上,家乡在陌生人的形象中是一个必然的存在因素。在舒茨的讨论中,家乡首先被理解成了日常生活的代名词:“家中的生活遵循着一种有组织的模式;它有其精心定制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可靠方法。
这些方法包括一组传统、习俗、惯例以及各种活动的时间表等等。只要遵循这一模式,就能够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问题。没有必要去定义或者重新定义情境,因为它们都已经发生过若干次,也没有必要寻找新的方法,因为旧方法已经尽如人意。
家中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表达与诠释图式,统领着我和其他的圈内人的行为。我可以确信,使用这一图武,我能够理解他者的意图,并让人明白我自己。圈内人所采用的关联系统表达出了一种高度的一致性。我总会有机会去预测他者对我的行动,以及他者对于我的社会行动的回应。我们不仅可以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也有相当的可能来准确计划更遥远的未来 ”
然而,这一家乡的形象,遭到了舒茨的好友古尔维奇的强烈批评一在一封致舒茨的信中,古尔维奇将舒茨的这一世界总结为“确定性、形式化与类型化”。在这一家乡之中的“行动类型”与“生活方式”正是现代官僚/科层体制的特征,也即舒茨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实际状态”而在古尔维奇看来这一点正是浩劫形成的原因之一
在这一“西方文明实际状态”所带来的浩劫之中,舒茨的思考开始有了一个实质上的“照面”——流亡。因为流亡者的性质“并不允许他们(自身)被简单地形式化”,所以流亡者与陌生人不同。在陌生人那里的家乡之形象,正是流亡者亟欲逃亡的对象。
陌生人仍有家乡,而流亡者则不同。在给舒茨的信中,古尔维奇明确表示,他们作为犹太知识分子所被迫离开的那个“文化家园”,不仅意指欧洲地理上的家园,更指向胡塞尔在1935年题为“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演讲中所点画出来的、使得欧洲知识分子“具有一种家乡意识”的欧洲哲学传统。与同为流亡者的汉娜·阿伦特一样,古尔维奇和舒茨也都认为,这一可作为其家乡的传统本身已经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