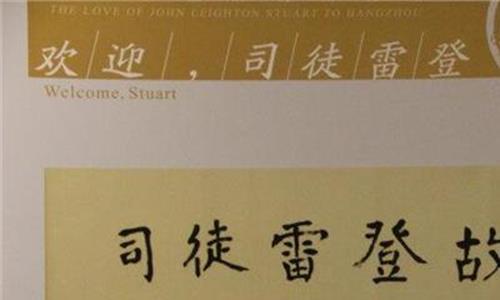司徒雷登的后人 真实的司徒雷登 他曾是燕京大学的灵魂
真实的司徒雷登 他曾是燕京大学的灵魂
北大人物
北大人物
司徒雷登,1919年担任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的校长,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
由于毛泽东那篇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出生于中国、时常以中国人自居的美国人司徒雷登成为某种政治较量下的惨败化身。但就是这个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失败的替罪羊,曾是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也曾满怀深情服务于中国。在历史的吊诡中,真实的司徒雷登也许被遮蔽了。

校长人选,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
1918年,出生在中国杭州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在南京踌躇满志地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2个生日。他有理由踌躇满志,因为从他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以来的活动以及收到的效果,不仅让他所隶属的美国南北长老会对他刮目相看,而且也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也是在这一年,位于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筹划酝酿已久的合并初步达成了一致。在当时别的人看来,出任这所还是将来时的燕京大学校长的最合适人选,已经是非司徒雷登莫属了。

当年“学生志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拨•史庇尔(RobertE.Speer)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
”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事布鲁克曼(F.S.Brockman)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于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1918年的下半年,美国南北长老会正式向司徒雷登下达了命令,让他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但是司徒雷登本人对于这项任命却并非心甘情愿,在他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实在不愿意去。我对金陵神学院的工作十分满意,在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已经得心应手,而且正在从事几项写作计划。”
包贵思女士(她是冰心先生的老师)在她写于1936年的《司徒雷登传略》中回忆:“那时的燕大是一无可取。我们很局促地住在城内,没有教员也没有设备……学生不到百人,教员中只有两位中国人(陈在新博士与李荣芳博士)。许多西方教员不合于大学教授的条件。”更要命的是“常年经费有一半是落空的”。
虽然司徒雷登对于这突如其来的任命并不情愿,但是他并不是个畏惧困难的人,同时,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并对中国有深厚感情的美国人,他认为创建一所新大学,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司徒雷登接受了聘请,但是同时约定:他不管经费的事情。
寻寻觅觅,选定燕京大学新校址
1919年春天,司徒雷登正式走马上任,出任燕京大学的校长。6月份他到达北京,遭遇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尴尬。那时候,五四运动结束不久,但是学生运动依然还是此起彼伏。在6月2日、3日、4日,学生游行示威的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前后有一千多名学生遭当局逮捕。
按照计划,司徒雷登应于6月8日跟学生们正式见面,算是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不巧的是那一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没有被捕的燕大学生,都满怀热情地跑到大街上去欢迎英雄们的光荣出狱,谁还顾得上这位上任之初的司徒校长。
不过,让司徒雷登头疼的不是这突如其来的尴尬,这种局面对于熟悉中国形势的他来说,也许是在意料之中。
虽然一开始曾经约定他不负责经费的问题,但是他一旦坐上校长的位置,这个问题就会来困扰他。在他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回忆到:“当时学校一点现款都没有。”而学校当前的情况却需要更换一个更适合发展的校址,不然燕京则没有办法发展。
根据司徒雷登的学生韩迪厚回忆,1919年的秋天,司徒雷登接手的燕京大学是这样的景象:那里有五间课室。一间可容一百学生的饭厅,有时用这间大屋子开会,也有时用来讲道。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浴室,一间图书室,一间教员办公室。另有网球场和篮球场。此外刚弄到手一座两层的厂房,原是德国人建的,可以改作课堂和实验室。
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来。那个不负责经费的约定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他开始在老朋友哈利•卢斯博士的帮助下募捐资金。募捐资金难免遭逢尴尬和白眼,但是司徒雷登觉得,即使募捐不成,那么也要和对方交为朋友,以便之后燕京大学的道路能够更加顺利。不过,他曾经感叹:“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一类。”
如今美丽的燕园还在,只不过已经更名为北京大学。司徒雷登是怎样找到了这个地方?又是如何把它变为燕京大学的新校址呢?在他的回忆录中,司徒雷登记载了他寻找校址的过程:“我们靠步行,或骑毛驴,或骑自行车转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块适宜的地产。
一天我应一些朋友之约到了清华大学堂,其中一位朋友问道:‘你们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我看了看,那块地坐落在通往颐和园的公路干线上,离城五公里,由于那里公路好走,实际上比我们察看过的其他地方离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这里靠近那在山坡上到处集簇着中国旧时代一些最美丽的庙宇和殿堂,并因此而著名的西山。”
司徒雷登看上了这个地方,他找到了这块地当时的主人———山西督军陈树藩。在和陈树藩交涉的过程中,司徒雷登显示出一如平常的那种非凡交际能力,结果,这位督军仅以六万大洋的价格把这块地让了出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为奖学金。
建立哈佛燕京学社,让学校跻身世界一流
过去的大学校长,往往把学校内知名教授的数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燕京大学初创时期,司徒雷登请到了刘廷芳和洪业两位名师,在他们的协助以及影响之下,一大批学术大师纷纷奔赴燕京,到上个世纪20年代,燕园之内已经是名师云集,国文系有顾随、容庚、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铎等人,历史系有陈垣、邓文如、顾颉刚等人,哲学系则有张东荪等名宿……名师出高徒,雷洁琼、冰心、费孝通、侯仁之、王种翰等等,都是那一时期的学生。
而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则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上世纪初期,司徒雷登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霍尔(1863-1914年)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并声明遗产中一部分用于研究中国文化,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来执行这项计划。
起初遗嘱执行机构选了美国的哈佛大学和中国的北京大学,但司徒雷登设法成功地说服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合作,于1928年春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司徒雷登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弄得我十分紧张,心里为自己事业的前途担忧,连吃的东西也顾不上看一眼。”
我们可以注意司徒雷登在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后所说的那句话,在说那句话的时候,他完全是以一个中国人自居并为此感到欣喜。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不仅把燕京大学看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更是把它看成是中国事业的一部分,认同这所大学是“中国人的大学”。
有一件事特别能够体现燕京大学以及司徒雷登在当时中国的影响。1935年,那时候的燕京大学已经享誉国际,当时对于政府的一些部门来说,它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有一次司徒雷登发出了这样的抱怨,蒋介石知晓之后,立即为司徒雷登在南京励志社安排了一次演讲。
那次演讲,蒋介石临时有事未能参加,但是在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率领下,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张群、何应钦、陈诚在内的各院、部和三军负责人近200人出席了这次集会。在这次演讲中,司徒雷登把燕京大学的种种状况介绍给当时的官员,以至于此后的燕京毕业生在应聘政府职员的时候,政府部门都不得不对他们青眼有加。
司徒雷登对于学生更是像一个慈祥的长辈,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后来学生逐渐增多,但他依然努力做到这一点。当时燕京有个规定,未名湖里禁止钓鱼,但是有个学生忽视了这个规定,正当他手持鱼竿在未名湖畔悠然自得的时候,一个慈祥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来:“这湖里面的鱼不错吧?”
宽容学运,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从这里发出
对于当时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司徒雷登表现出了比很多大学校长更大的宽容。1934年,北平学生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纷纷南下请愿示威。燕大的学生在爱国方面一向不甘人后,也参与其中。学校无法解决,只好连电催促正在美国募捐的司徒雷登返华解决问题。
司徒雷登返校当日,正是南下请愿的学生们北上返校之时,大会上校长的话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司徒雷登先是沉默了二三分钟,然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大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么?他们回答我说,燕大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大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司徒雷登也在考虑着是否把他经营了许多年的燕京大学迁往后方,但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决定让这所大学留在北京。他迅速地在燕园升起美国的星条旗,以表示此处属于美国财产,又特别在大门上贴上公告,不准日军进入。
司徒雷登本人并不认同共产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抗日刊物以及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依然在燕京大学里正常地得以出版。由于司徒雷登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中,抗日救亡的呼喊得以在这个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中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主席在重庆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就满脸笑容地对司徒雷登说:“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仿佛就是一体。那所由他的朋友们捐赠给他作为居所的庭院,位临未名湖,冰心先生给它起了个诗意的名字:临湖轩。但是司徒雷登并没有一个人独享它,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地点,所以,很快地这座庭院成为了燕京大学的标志。每年的6月24日,燕大的学生必定来到这里,给这位受他们尊重的校长祝贺生日。1926年6月5日,司徒雷登的夫人在这所庭院离开人世,她的墓地成为了燕大校园中的第一座坟墓。
出任大使,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
他本来应该一直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校园里,但是在1946年,他作出了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选择。在他即将离开北平的时候,在某个中美联谊会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他突然发现了已经认识了多年的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他的即席发言中,他把自己与胡适作了一番比较,他说:“他幸运地辞去了出使国外的使命(指胡适辞去了驻美大使的职务),返回了北平当大学校长,而我却要离开这最可爱的城市和那令人满意的事业,去从事一项前途未卜的使命。
”不过,燕京大学校友林孟熹对此则有不同的回忆。
林孟熹曾就司徒雷登出任大使请教当时燕大政治系主任兼校务委员会成员陈芳芝,陈芳芝回忆说:“在离开燕园赴南京就任前夕,司徒雷登曾经对他说:‘出任大使是为了谋求和平,而只有在和平环境下,燕京大学才能生存和发展。’”
但是长于治校的司徒雷登对于政治显然没有对于教育那样了如指掌。他想一碗水端平,因此得罪了他过去的老朋友蒋介石,以至于1950年司徒雷登的75岁寿辰,当时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请示蒋是否以蒋的名义赠送鲜花,蒋冷漠地回答:不必了。
随着南京的解放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彻底失败,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踏上回美国的飞机,离开这片他曾经生活了几十年并曾经深深热爱过的土地。在飞机上,他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在那里面,司徒雷登完全成了一个美国对华政策失误的替罪羊。
而在大洋彼岸的这一侧,毛泽东主席则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这位老人再也支撑不住,一下子中风卧床不起。在他身边的,只有过去一直支持他的秘书傅泾波。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王公的后人,在司徒雷登卧床不起的日子里,体现出他一如既往的君子之风,像一个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恐怕也只有他,能够体会司徒雷登此刻心情的荒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