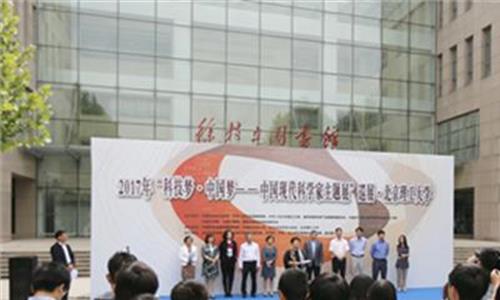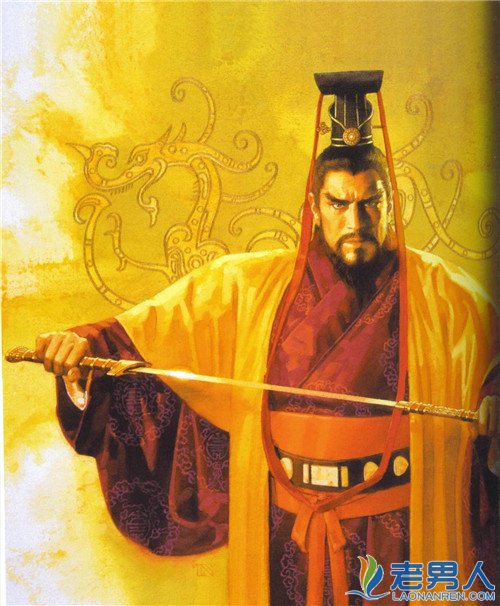走读周有光 走读历史名人 | 初识周有光
说来自觉汗颜:如果时光倒退十几年,我对“周有光”竟是一无所知。
我最先认识的,是周有光的夫人张允和。
我与她仅有“一面之交”,准确些说,是70分钟。本来约定只聊一刻钟的,没想到时间会过得那么快。若不是有客人来,我已经忘了时间。

见面的第一句话,她用浓浓的南方口音说:“咱俩是同志!”
我不解。
她嫣然一笑:“我最喜欢紫颜色,多子多孙啊!你也穿的是紫颜色。所以咱俩是同志嘛!”
那是2002年5月19日。虽是初夏,天气已经热得很了,所以我穿的是一件紫色的短袖衫。她的衣服果然也是紫色,但紫得很不一般。我对衣料不在行,说不出她的上衣是什么料子。似乎是一种丝绒,动静之间,会有奇妙变幻的光晕在闪动。那衣服的样式更不一般,是一件中式对襟小褂,配上精致的黑色扣襻,有浓郁的古典韵味。

她整个人都有那样一种古典韵味。比如她的头发,几近纯白,细致地编成辫子盘在头顶,用几个发卡随意一别,便显得那么与众不同。我不太会形容一个人的容貌,所以借用别人的一句话:“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我想作一点小小的更正:这句话去掉“年轻时”三个字,也许要更准确。因为我在见到她的时候第一次认识到:“美”是无须用年龄来限定的。

我还想说的是,“美”未必完全表现在容貌上。允和的美也很有些不一般。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琢磨透这“不一般”的感觉究竟来自何处。但很快我就明白那原因了:她始终在笑。微微的、淡淡的,是如同孩童般纯真的、极其具有感染力的笑,使任何人都会不由自主地随之绽开笑纹。
她说了好多故事。有趣的,幽默的,动人的,曲折的,哀伤的……她始终在笑着说,我也始终在笑着听。我们都沉浸在故事里了,所以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消逝。直到有新的客人来了,是事先约好的,我才意识到自己待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不得不告辞。
拜访张允和的缘由,是我前不久刚刚去过苏州她家的老宅。
那是出于一位朋友的建议。她知道我正在写关于名人故居的东西,听说我要去苏州,告诉我:“你应当去九如巷的张家看看。”
见我对九如巷和张家一无所知,她很认真地说了许多事情,使我觉得的确很值得去看看。
九如巷在苏州老城靠南一些的地方,张家位于胡同中部,并不难找,因为这只是一条短短的巷子。但是进入张家的院子后,会发现这里另有一方天地:小小的庭院洋溢着一片绿色,草木丛中时而探出数枝盛开的花朵,连空气似乎也比外面清新了许多。
接待我的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自我介绍说,姓张,名寰和;耳朵不太好,说话需要大声些。
有一点使我感触颇深。这些年来,名人也好,名人的子女或亲属也好,我多少也接触过一些。热情的、随和的、认真的、冷淡的,高傲的、充满警惕甚至敌意而毫不客气地让吃闭门羹的,各种各样的态度基本都曾遇见过,但是,像张家这样,对一个陌生的来客没有任何戒心,完全敞开大门、敞开心扉,以最纯洁无瑕的心情迎接每一位客人的,并不多见。
与张寰和——包括后来与张允和——谈话的感觉,犹如熟悉的朋友或亲属之间的闲聊,十分轻松。
于是,张家的情况,就在这轻松的闲聊中慢慢向我展开了比较清晰的
轮廓。
张家原籍安徽合肥,可算当地名门望族。祖父张树声为晚清重臣、淮军名将,先后任直隶按察使、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山西巡抚、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贵州巡抚、广西巡抚、两广总督、署理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等,这一大串令人眼花缭乱的职务,恐怕还未说得完全。
父亲张冀牖未入仕途。辛亥革命后举家前往上海,后来迁至苏州。五四运动后,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于1921年变卖部分家产创办了著名的乐益女子中学以及一所男子中学——平林中学,自己担任这两所学校的校主,此后男中未能持久,则全力办好女校。他与蔡元培等人交往颇深,聘请了许多思想激进的各界人士来校任教,如侯绍裘、张闻天、叶天底、匡亚明等人。中国共产党在苏州的第一个当地组织——苏州独立支部就是在乐益女中秘密建立的。
现在该说到张寰和这一代人了。
张冀牖先后有两位夫人。第一位夫人陆英,21岁嫁到张家,生有14个孩子,其中5个夭折,留下4个女儿、5个儿子。她36岁那年因拔牙引起血液中毒,不幸逝世。第二位夫人韦均一,生有3个孩子,但仅有一个儿子活下来。这样,张家就共有10个孩子了。这姐弟10人虽然同父异母,却感情极深,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并非是同一个母亲。
张寰和很仔细、很认真地在我的本子上写下了这些兄弟姊妹的名字和情况。
张家四姐妹。从左至右: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摄自张允和家庭相册)
大姐元和,1907年生,喜爱文学,尤擅昆曲,现定居美国,仍以研究昆曲为最大嗜好;二姐允和,1909年生,现在北京;三姐兆和,1910年生,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四姐充和,1913年生,曾在美国耶鲁大学担任书法及戏曲教授,现定居美国。
接下来是6个弟弟。大弟宗和与二弟寅和已经去世;三弟定和,1916年生,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作曲家,现住北京;四弟宇和,1918年生,是张家唯一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为南京中山植物园研究员,现仍在南京;五弟寰和,1919年生,继承父业担任“乐益”校长,始终从事教育工作;最小的宁和,1926年生,家里人为了纪念一个早年夭亡的六弟,称宁和为“七弟”,他26岁时便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后为比利时皇家乐队成员,现在国外。
屈指算来,眼前的张寰和应当是83岁的老人了,但他并不显得苍老。他笑着说:我觉得自己很年轻——上面还有那么多的姐姐哥哥,我怎么能说自己“老”呢!
十姐弟的名字有一个特点:女孩子都有“两条腿”,注定要跟人家走;男孩子都有“宝盖头”,应当留在家里。但是,实际上只有张寰和是唯一“留守”苏州的。
十姐弟原有“小名”。女孩子依次叫“大毛”“二毛”“三毛”“四毛”,男孩子则叫“大狗”“二狗”……。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和”字:和美、和谐、和平、和睦。所以虽然“毛(猫)狗同‘笼’”,却从不争吵,相处得好极了——张寰和说:这是二姐允和总结的。
我注意到,虽然张家姐弟男孩居多,但张寰和的话题却始终围绕着几个姐姐,尤其是二姐允和。比如,几个姐姐的婚姻,就大都与允和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说:将来你见到二姐,她一定会告诉你她是怎样当“媒婆”的。后来张允和果然说到她是如何为姐妹决定婚姻大事的——她说:只可惜四妹没请她这个“媒婆”,自己嫁了个“洋人”。
大姐元和迷恋昆曲,以致由戏及人,爱上了著名昆曲小生顾传玠。但是,由于二人家庭背景相差悬殊,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很难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犹疑难决的元和向二妹倾诉了自己的心事,允和当即回信:“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
”元和终于下了决心,用当时上海小报的话说,是“张元和下嫁顾传玠”。顾传玠自己也开玩笑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实际上,他们婚后感情极深。二十多年前顾先生去世,后来元和特地为他印制了一本《纪念册》。而元和本人虽已年逾九旬,仍在痴迷地研究昆曲。张寰和说到这里,进里屋取出一本元和饰演杜丽娘的《身段影集》,那些照片还是她92岁时拍的。
说来也巧,正说到元和的事情,邮递员送来一封国外来信,张寰和笑着说:“正是大姐来的,说的还是昆曲的事!”
在他看信的时候,我发现墙上悬着的条幅居然是沈从文的手笔,写的是李白诗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2002年的张寰和。他背后墙上的条幅是沈从文的手笔。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惊讶的,文学大师、著名学者沈从文本来就是张家三姐兆和的夫婿。而二姐允和却在他们那段姻缘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允和在与我聊天的时候学沈从文——她称他为“沈二哥”——的湖南腔调,拖着长声说:“‘媒婆’!沈二哥就是这样叫我的——‘媒婆’!”她笑得弯了腰。
而为姐姐和妹妹的婚事积极奔忙的张允和,自己的夫婿却来得很从容,那就是周有光。
张家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叶圣陶说过:九如巷的四个才女,谁娶到了都会幸福一辈子。周有光就是“幸福一辈子”的人之一。他与张允和并肩走过了将近70年的人生之路,那可真是一段悠长的故事,需要舒缓精神,慢慢道来。
由于战乱动荡,张家姐弟陆续走出家门,天各一方,甚至有数十年中断了音讯,但这九如巷始终是他们眷恋的地方。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系全家人感情纽带的,是一本特殊的刊物——《水》。
受父母影响,姐妹都喜好文学,于是组织了一个“家庭文学团体”——“水社”。几个弟弟看着羡慕,也组织了一个“九如社”。相比之下,还是“水社”显得更加兴旺,她们的社刊《水》办得红红火火的,连“九如社”的成员也不由自主地参加进来了。
《水》的“发行范围”虽然只限于张家的成员以及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但办得十分“正规”,大家都踊跃地为它投稿,并十分积极地刻版、油印、装订、分发,忙得快乐而有趣。直到1937年,因战乱的影响,全家人离散各地,《水》也就被迫停刊了。
要说一个家庭刊物也并不算什么稀奇,据我所知,一些文化人的家庭同样有过以孩子们为主体的家庭墙报、家庭“报纸”什么的。但《水》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停刊近60年之后,居然又更加红火地复刊了。那发起者,就是张允和。
这真是一份十分有趣的刊物。用“自封为主编”的张允和的话说,是“世上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1995年,复刊后的第一期《水》,只印了25份,但它的读者越来越多,传阅范围已经穿越了国界、远及欧美。著名作家巴金先生也是它的忠实读者之一,每期必看,甚至在自己的住址有变化的时候还及时打电话通知“编辑部”,以免收不到。著名出版家范用称《水》的复刊为“本世纪一大奇迹”。
从第七期开始,已是“二八年华”(对自己88岁的戏称)的张允和“退居二线”,改由“副主编”张兆和主持。由于后来张兆和身体欠佳,从第十三期起,《水》的“编辑部”从北京移至苏州,由张寰和继续主持。
张寰和送了我一本2002年4月30日最新出版的“复刊第十九期”,是用复印纸单面“印刷”的。封面照片是位于苏州书院巷的江苏巡抚衙门旧址,由张寰和摄影。我在来他家的路上刚刚经过那里,但不知道那正是他们祖父张树声当年任职的衙门。这刊物虽然只有26页,内容却包罗万象。有关于张树声、张冀牖的生平介绍,有政论文章,有诗词歌赋,有日记摘抄,有报刊文章汇编,有绘画作品……
我随手翻去,最先看到的是周有光写的那篇《走进世界》。文章针对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历史性的大事,由《桃花源记》的“世外桃源”谈起,说到中国传统的“出世”思想直接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巧妙地把加入世贸组织的“入世”与走进“尘世”的“入世”结合起来,阐述了“入世”的重要与必要。
他说:“人民进入世界,才是真正的‘入世’。……从‘入世’之难,我们看到了自己离开世界还有多远。……走进世界,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只有认真学习地球村的交通规则。”
这篇文章虽然不长,但视角独特,笔锋犀利,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位97岁的老人笔下。这使我更加迫切地希望尽快见到那“二姐”夫妇。
张家姐弟现在北京的有三位:二姐允和、三姐兆和与三弟定和。我向张寰和许下了一个诺言:回到北京后,逐一拜访他们,把他们近来的状况用相机拍下来,让他们姐弟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见面”。
不过,我的诺言未能实现。
我首先试图与张兆和联系。但是,家人在电话中把我误认为是沈从文的“追星族”,很客气地拒绝了。我也理解他们的苦衷:张兆和近来发现有脑萎缩的迹象,身体很不好,受不得外人打扰。
张定和的夫人倒是答应我上门采访,但是也告诉了我一个特殊的情况:他因身患癌症多年,近来身体情况很差,经常夜不能寐,因此睡无定时,说不准什么时间有精力见客。第二天我冒昧前去,张定和的夫人请我进屋后,很抱歉地说,定和昨晚又是一夜未眠,刚刚躺下睡着。我请她不必为难,待下次再来无妨。
唯有与张允和的电话联系最为顺利,当她听说我刚从苏州回来,十分高兴,说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因为她是“家庭妇女”,随时都在家里,即使明天上午便去也可以。但她刚说完又想起了什么:“喔哟!明天上午10点还有一位客人呢。”我连忙说不要紧,我只需要15分钟,拍几张照片就可以。——我已经意识到,对上年纪的人是不应过多打扰的,不能因为自己的拜访而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没料到的是,第二天这15分钟竟变成了70分钟。
张允和给我说了许多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比如她是如何在盛夏暑热中出生,由于一声不吭而差点被当成死婴,只有老祖母不相信,让人用喷烟的偏方抢救。足足喷了一百袋烟;在所有的人都失去信心的时候,她突然鼻子嘴巴动了动,活过来了!
还有,她是家里最爱哭的“小二毛”,有时天不亮就开始哭,一哭起来就不得了,没完没了。她还说了当年在乐益女中的时候听张闻天讲都德的《最后一课》,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清楚地记得张先生的教诲:做人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人,真正的人是“放眼世界”的人。
她接触过许多有名的老师,比如在上海光华大学时,教国文的老师是钱锺书的父亲。她还说到在大学时因为性格开朗活跃,而被选为女同学会长。在女同学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田汉专门为她们写了一出全是女人的戏,她演一个资本家的丫头。那时她已经是南国社的成员,一次临时演一个女工,田汉说她鼻子高,不必再装假鼻子了……
看到我在苏州九如巷拍的照片,她高兴极了,问我:“看见那无花果树了吗?看那一大丛蔷薇还在吗?我最喜欢那蔷薇了,还写过一首诗呢!”
我请她把那诗抄在我的本子上:
蜂蝶艳阳天,
桃李争芳研。
蔷薇浑不语,
开遍小窗前。
我给她的钢笔不好用,总不出水,那个“窗”没有写好,她又仔细地重新写了一个。
张允和早年曾经当过编辑、任过教师,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被迫停止了工作。所以,她总说自己是个“家庭妇女”。实际上,她是当过“官”的,那个“官”,就是昆曲研习社的社长。
受父母的影响,“小二毛”从小就被保姆抱着去戏院听昆曲,耳濡目染,也成了个昆曲迷,不仅看,还要自己演。到了北京后,加入了俞平伯任社长的昆曲研习社,她是个少不了的“积极分子”,所以被“委任”为“联络组长”。
到了1964年,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研习社解散了,直到15年后才得以恢复,她就是那时候当上了社长。第一次开会的时候,这位社长特意穿了一件紫色的上衣。她在发言中说:“我今天为什么穿这件紫色衣服,就是希望我们的昆曲艺术能子孙万代,永远流传下去。”
昆曲源自昆山,昆山属苏州所辖,作为一个苏州人,喜欢家乡的戏曲是很自然的事,而张允和岂止是喜欢,简直是无条件地痴迷,仅她写下的《昆曲日记》,竟有50万字。研究昆曲和编辑《水》,是她晚年最感兴趣的两件大事,到了“二八年华”的时候,她又开拓了新的天地:开始写书了。
她说,写书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由于她的书引起了很大反响,引来许多媒体采访,“名气”之大不亚于著作等身的周有光。她笑言道:我比有光更有光,成了老明星了!……
我们的谈话是在周有光的小书房里进行的。在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始终埋头在打字机上工作。我悄悄问张允和:“周先生大概不太爱说话?”她笑着说:“哪里哟!他很爱说话呢。只是我说得太多了,让他插不上嘴。”她并未夸张,据说周有光的口才是很有名的,他们的老朋友聂绀弩曾写过一首诗打趣他:“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蔫头蔫脑话三千。”只是今天他没有找到表现的机会。
说到写书,张允和说要送我几本。她的腿不大好,从沙发上站起来有些困难,歇了歇才起步。在她去取书的这段时间,周有光大约是怕冷落了我,主动转过身来和我说话。
周有光曾说:“张允和是合肥人,她的普通话是‘半精(北京)半肥(合肥)’,我的普通话是‘南腔北调’。”他的“南腔北调”与张允和的“半精半肥”一样,都很容易听懂。但是,我的话对他来说就太难听清了,因为他的耳朵聋得厉害,所以他一再鼓励我:“请声音再大一点点。
”那场面一定很滑稽:我肆无忌惮地“猖狂”大叫,而周有光则微笑着颔首倾听。我们讨论的是关于听力的问题,只聊了几句,张允和回来了,周有光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扣上眼镜,又回去工作了——他的眼镜镜片是活动的,可以很方便地抬起来、“扣”下去,看上去很有趣。
张允和一下子送了我三本书,是她自己写的:《最后的闺秀》《张家旧事》和《多情人不老》。准确地说,最后一本书是她与周有光合写的,那书的装帧很有意思,不分前后,两面都是“封面”。前半部分是张允和写的,横排本;后半部分是周有光写的,竖排本。她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很认真地题词:“光中先生惠存;允和;2002—5—19。”
最后她说:“等夏天过去,天凉些了你再来。我还有好多好多故事呢!有意思极了,好玩得不得了!”
我说:“如果您愿意,由您说,我来记,把那些好玩的故事都写出来好不好?”
她很高兴:“那好啊。等今年夏天过去,天气凉些了,你一定要来。我还有好多照片呢。下次来拿给你看。”
然而,我们的约定没有实现。这年夏天极热,张允和居然永远地去了……
本文选自《走读周有光(修订本)》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本书传主的评价:
我有一句话,看了你这个书以后,我就写在上面了。我说:“同类书中,此书写得最好。”尤其你创造一种你的写法,你的风格。真是了不起。
──周有光对作者如是说
编辑推荐:
本书以作者与传主周有光及其家人十五六年的交往为基础,以作者历时九年、行程近万里的对历史的实地考查为脉络,以对话访谈、图书文字作品、展览实物、历史图片、作者实地摄影照片、手绘画作等大量史料为依托,既遵循了周有光人生历程中的主要时空地点的变换,又逐步展现了作者边走、边读、边写、边想的独特风貌。
本书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对于理解和研究周有光及其人生经历与成就都有较好的学术价值的参考;对于了解和还原中国近现代百余年的社会文化历史,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成长史、生活史,也提供了一个史料较为丰富的窗口;同时,本书也是对周有光先生逝世的纪念。
内容简介
本书传主周有光(1906—2017),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语言学家。他成就斐然、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他的一生,历经了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历史。他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无论他生命的长度、成就的高度、思想的广度和影响的深度,都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奇迹。他是资中筠、葛剑雄、黄永玉、易中天等众多名人共同尊崇的智慧大家……
这是一部构思精巧、史料珍贵、与众不同、图文并茂的周有光传记。作者十年磨一剑才得以写就本书,经传主周有光先生生前亲自审阅并为书名题字,开卷有益。
作者简介
陈光中1949年9月生于大连;1966年随父母迁京,就读于北京八十中学。当过学生、插队知青、铁路养路工人、蒸汽机车技术员、计算机工程师、文字编辑。现为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博物馆学会会员、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喜文字,好摄影,偶习绘画。写过若干小说、散文、评论,画过些许漫画、插图。著述颇丰,包括:长篇传记《侯仁之》、《走读鲁迅》、《走读周有光》,以及《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共八册)、《北京胡同》、《走读京城角落》、《走读京城人物》,等等。部分作品在中国香港地区、中国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