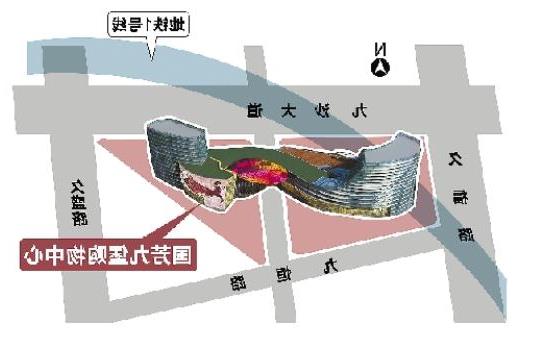张瑞芳河南 张瑞芳给我这个小人物提示:向中央反映
今年是张瑞芳100周年诞辰。我想将这个“历史轶事”写出来供大家分享,以此纪念她的百岁诞辰。
我当年参加由张瑞芳主演的《李双双》摄制组,奔赴河南郑州、陕西西安等地,后来,又来到福州市郊,在那儿补拍若干镜头,然后由制片部门派人专送上海技术厂洗印,如技术上没有问题,大队人马即可班师回沪。所以在福州这几天,大家轻松愉快地等待着上海的消息,自由自在。而在这几天里,张瑞芳却很忙,无论观众和官员见到她这个大明星时,那股狂热劲儿就别提了。有时,她也不得不参加一些应酬,我们也就一并沾光。

那天晚上,当我看完福州方面招待的由尹桂芳主演的越剧后,心情格外舒畅。回到福州饭店,看见先回一步的照明工小郭神秘兮兮地将一个信封高高举在灯光下左照右看。我好奇地问他:“看啥?”没想到他一惊,然后朝着我挤眉弄眼说:“大明星给你的信。

”我一听好生奇怪,张瑞芳为何给我写信呐?嘴里却说:“给我的信,你看什么?”随之一伸手把它抢了过来。急忙将它打开,究竟写着啥?没想到,抽出折了三折的一张纸中间,用钢笔端端正正地竖写着:向中央反映。我赶忙又折上,塞进自己裤袋。小郭追问我写的啥?我灵机一动,因为我是学置景的,就推说是张瑞芳写给我她家的地址,让我回上海到她家里装纱窗的事。

我心里想,她为啥突然给我写信呢?不,这不是信,前面没有抬头,后面没有落款,就这光秃秃的“向中央反映”五个字。这在旁人眼里有可能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可我心知肚明。
这要从1961年夏天到达河南林县太行山地区说起。由于我穿着乡下母亲缝制的土布衣衫,在别人眼里有点土里土气吧。在七八十天的外景地朝夕相处中,大家从不熟悉到熟悉,从点头打招呼到开玩笑,渐渐融为一体。我1958年才进厂,又是第一次出远门,对于我来说,一切都既新鲜又陌生。

有次在途中,制片主任吴承镛(当时我认为他是摄制组里的最高领导)问我,前面是山,山后面是山还是云?我仔细地看了好长时间,回答说,前面是山,山后面还是山,再后面的后面,可能是乌云了。
没想到站在我身后的小郭大声地说:“阳光四射,哪里来的乌云啊!”引发了车上几十号人的一片笑声。还有与我一起进厂学摄影的计鸿生,他说我的穿着,很像当地的青年农民,给我拍了有生以来的第一张实景照。
但我不会想到,在这说说笑笑的旅途中,张瑞芳也在悄悄地关注着我。感觉上,她好像让我接近她,可我对她很疏远,因为在我心目中,她是大人物,满口说的普通话。我本来就不太会说话,说出来的话唯恐对方听不懂,又加上各种因素,产生了心灵上的自卑。
在电影厂里有些大学毕业生也自称为“小三子”,那我在他们大人物眼里,连小八腊子也不如了。所以有时从营地出发到景点,或从景点回营地,张瑞芳常喊我:“小黄,帮我拿点东西。”当我转身时,已看到有人勤快地替她拿上了,我就绝不会与他人争着去拿。
有时替她拿上什么(如帆布做的折叠凳或她的毛衣外套等)与她一起走时,她总是与我拉着家常,问这问那,问东问西。这样一来二往,她不仅了解了我的家境,更了解了我家乡农民的苦难。
当摄制组来到太行山区,得知当地的农民把桦树叶都啃光了,而当地干部却宣称,这好比南方人吃蔬菜。像我这样出身的人,看到这些情景,听到那些粉刷太平的言语,早已习以为常,并不当一回事;可张瑞芳却为此生气叹息:“这样下去,中央怎么知道实情啊?”
在太行山地区完成了外景任务后,摄制组并没有回沪,因厂里的摄影棚全被《红楼梦》剧组“大观园”布景占用着,所以赶往西安电影厂去拍内景。西行的列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有一次停车的时间特别长,只听到车厢外一片混乱声。
有人说,难民们将列车包围了,解放军在清理中。车内的人心有些躁动,我在车厢旁边的走道里漫无目的地走过来又走过去,偶遇上了张瑞芳。她请我进了她的软卧包厢,那天正是1961年的国庆节,周恩来总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今年是我们国家困难的“第三年”。接着周总理的讲话声,我听到她忧心忡忡地说:“三年了,可能要更乱了……唉,中央知道下面的情况吗?”——她处处关心着国家大事呐。
所以当看到“向中央反映”这五个字,我心里很清楚,而且无比亲切和激动。她的态度是明确支持和鼓励我,让我将切身体会的家乡事向中央反映,而且我还认为她写着的“向中央反映”,就是向毛主席反映。
补拍的镜头,技术厂通过了,摄制组大功告成了。
我从福建回沪后,兴奋地闷头扎进殷家角上影附近的集体宿舍,我写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认为满意为止。可《李双双》的影片正在做后期结尾工作,我从此很难见上张瑞芳了。即使有时在食堂远远见到她,可她不一定能见到我,何况她身边围着的不是秦怡、上官云珠,就是赵丹、孙道临、康泰等一批名人,他们在说说笑笑谈着事呢。
在那种情况下,我怎么敢上前与她打招呼,道出“写信给中央”这种没头没脑的话题呢?但我又天天想着去找她,有时还到号称“亚洲第一摄影棚”的东侧二楼202会议室去找她。
如果见到她在里面开会,我会找一个适当的地方等她,在方便的条件下上前与她打招呼。可遗憾的是,没有一次见到过她。我还向厂里团委书记张远明打听,张瑞芳她有没有在202开会。当时我是置景车间的团支书,而且他又知道我正和她在一个摄制组工作,向他打听一些情况,他也不会想太多。
我找张瑞芳的目的,是把这封写给毛主席的信给她看,请她修改。同时想了解,她写给我的纸条是否还记得。我认为信寄出之前请她过目,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焦急地想要找张瑞芳。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突然想到她的先生严励在文学部工作。那时我年轻,又容易冲动,一下子被自己的灵感所激奋,就来到了创作二楼去见了他,并说明了我的来意。我对他说:“我向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他正要伸出的手缩了回去,疑惑地打断我的话:“什么,向党中央毛主席……”幸好,我预先做好了准备——我想在她的先生面前,不应该为她保密吧?所以我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从裤袋里取出张瑞芳写给我的纸条递上去。
他接过后仔细认真地看过后,把纸条还给了我,收下了我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他还朝我说,她很忙。我连说,不急不急。
但没想到,在第二天的中午时分,我刚从食堂里吃完中饭回到集体宿舍,就听到外墙玻璃窗上的敲击声,接着就听到我师傅的声音:“锦元在吗?”我应声走出宿舍大门,我师傅告诉我,文学部严励找我。我一听,顾不上招呼道别,急急忙忙奔去找严先生了。
一进他的办公室,他请我坐,可我并没有坐下,而是问他,张瑞芳同志看过啦?他说,她看了,提两点意见:一是抬头改一下,改成周恩来总理;二是文字上能否压缩一下。严先生还朝我嬉笑着说:“一字不漏地传达哦。”我听后,高兴地向他点着头,口中语无伦次地说着:“好,好,谢谢张同志,谢谢严先生!”
我满怀喜悦匆匆返回宿舍,打开一看,没有一字改动。我心里想,抬头改一下很容易,把毛主席改为周总理,但在文字上压缩,对我来说很困难。在厂校名义上读的是高中语文,可那点文字水平,我没有压缩的功底呀。所以我又看了几遍,把抬头改好后,认认真真地抄了一遍,一个字一个字地数了一下,只比原稿少了几个字,我想这肯定不符合张瑞芳的要求。
我想到了厂校老师潘培元。就在当天晚上,上完夜课后,他往徐家汇方向去乘车,我与他同走几步,对他说,我写了一份材料,当作一篇作文,请帮我在文字上修改修改。他连说好好,接过材料后,塞进了手拎的公文包里了。我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消失在暗淡灯光下,心里无比的兴奋:这下好了,文字压缩有希望了。
但没有想到,第二天一早,我在食堂吃完早饭,还不到八点的上班时间,就听到电话总机间小吕在广播喇叭声里传出清脆悦耳的声音,说潘培元找我。
我立即去了他的办公室。潘培元是南京人,说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他见到我,脸上表情有些紧张地朝我摇着头,嘴里说着:“我我……这、这是大事情,不是改改文字而已。”他继续摇着头,以对农村情况不了解为由,就把信退还了给我。
可我有些倔强,幼稚地说:“正因为是大事,所以才请老师帮忙,在文字上加工,压缩一下。”他听后,想提高嗓门但又控制着情绪,激动地又压低了声音,一字一板地说:“这、不是文字!是内容!涉及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带着不悦取回原稿,离开了潘老师办公室。
正当我要下楼时,迎面碰上了李长弓。我心中一喜,眼睛一亮,他是我的前辈,对他了解的人称他为秀才,是海燕厂大导演郑君里的助理。他见到我,常主动与我点头微笑打招呼。突然有一天,他把有关写作方面的理论书籍,包括怎么写通讯报道的小册子等送给我。
在我的印象里,他为人热心,非常健谈,烟瘾很重。今天碰巧见着这位秀才,我喜出望外,我想:请他帮忙,他不会拒绝的吧?我把遇上困难的事情简要地说了一下,他很乐意地和我下了楼。
来到了食堂,已经是上班时间了,这个时候的食堂静悄悄。我和他坐在饭厅的一角,他看完我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后,原先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沉默地连抽三支烟以后,面无表情地问我:“你怎么想到写这封信的?”当时我心里想,在他面前我应该保密的。
所以很自然地说出了我写这封信的动机:因为我家在农村的遭遇无处申诉。他听后仍不说话,又取了一支烟,划上火柴,点上烟后,一阵吞云吐雾,然后慢悠悠地朝我说:“想也不敢想的事,而你写了。当年的右派,也不过只是一句话的事。”他又抽了一根烟,思索了一会儿,突然又朝我轻轻松松笑着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今后一切都会好的。”意思我明白,他和潘培元一样,奉劝我别写这封信了。
可我并没有听取他俩满腔热情的劝阻,也并没有使我左右为难,因为张瑞芳“向中央反映”五个字,从我自身的利益考虑,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激起我无穷的精神力量,我要坚定不移地朝着她指引的方向去努力。于是,我又一次认真仔细地一字一句重抄了一遍——
尊敬的周总理:
我家在江苏启东少直公社五大队十五小队。四口之家(父母、两位弟弟),另一个弟弟尚在襁褓中就送人了;还有一妹,十来岁在伯父母的关爱下寄养在他们上海的三儿媳家里;我本人二十来岁,在海燕电影制片厂,刚从三年学徒转正为一名置景工,月薪36元。
从报纸上宣传来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形势一片大好。可我由于工作的关系,亲眼目睹安徽、河南、陕西等地,包括家乡的农民普遍存在着闹饥荒的严重问题,有的地方在闹事,火车有时也开不动;有的地方,树叶也吃光了;有的地方到处都有要饭的人——这一切都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
可我江苏启东县,是你总理于1958年12月31日亲自签发的农业社会主义先进单位,粮棉连年双丰收,是名副其实的先进单位。但我不懂的是,为了全国一盘棋,当地的农民照样闹着饥荒,对我家而言,春二三月,青黄不接之际,饿肚子还算小事,家遭惨剧,有口难言。
在大跃进年代,家中的住房被毁,将零星木料用来炼钢,大的木料被一些干部占用,营造他们自己的住房,我的家人无归宿之地,住在人家破旧的柴房里,夏天受蚊虫叮咬之苦,冬天饥寒交迫。
我回家向当地干部为父母追讨住房,他们推说是上届干部做的事。我找到县里官员,他们又推说是下面干的事。数年来,我的家人在疾苦中挣扎。
我大弟受到严重的刺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常常破口大骂地方官为“强盗”“国民党”,有时见着他们甚至上前行凶。父母为了避免意外发生,从铁匠铺里打造了铁链,将他锁在家中。得知如此情况,我同妹妹一起回家,带着他来沪住院治疗,仅一个月花费500多元。
医生也说,完全自费怎么吃得消。获得医生们的同情和许可,照顾我们看门诊,只要讲清病情就可配药,还得到了海燕厂领导的关怀,垫付了所有的住院费用,包括后来门诊各种费用的借款,拖欠厂互助基金超千元。
仅靠我的工资收入,债务也难以还清,更谈不上为父母建房了。尊敬的总理,你是日理万机,操劳着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的大人物,我实属无奈,才来打搅总理,求助于总理大人。
此致 敬礼
黄锦元
1962年某月某日
给周总理的信,在春节之前寄出了。那时的春节,假期只有三天,虽然已经上班了,但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中。真没有想到,那么快就收到中央给我的回信了。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的记忆里,既模糊又很清晰地记得两件事:一是在厉行节约的年代里,用一张正面贴着白纸的旧报纸做成的大信封,整个信封又长又宽,上面还有一个好大的浓而鲜红的繁体“厅”字。因为第一个字是中字,好似宝塔尖,厅字仿佛是塔座,竖插在殷家角传达室外墙上简易透明的信箱里,好像顶天立地的一座红色宝塔。
扣人心弦的就是这条红色落款——中央某某厅,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眼球。二是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拿着沉甸甸的信封,激动地回到了集体宿舍,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信封,里面似乎是空的,左摸右摸,最后从信封里面取出一张薄薄的便笺,上面写着“信已转人民日报农村工作部”。
字体很小,很淡的一行竖写着的钢笔字。我感到懊恼,又无知,认为我费了那么大的精力,居然那样给我草草回信!
所以,既不看抬头,也不看落款,情绪低落地把它捏成纸团扔了。在豪华的信封里,我认为装着的是一纸空文,真是外表好看,腹中空。而且我苦恼地想着,这如何向张瑞芳汇报呢?
正当我一筹莫展之时,团委书记张远明来找我了。那天是星期天,我一个人在宿舍里,我知道他已成家,但在上海是单身,家属在武汉。我很高兴地欢迎他的到来,忙搬凳子招呼他坐。他说,他今天是代表美术党支部书记盛云清、厂工会主席汪永根,也就是代表党政工团来找我谈话的,然后提纲挈领地说:一是我有什么困难就去找他们,二是不能随便向中央写信,意思是中央内部斗争很复杂。
张远明与我谈话以后,我思想负担很重,又为中央给我不可思议的回信而闷闷不乐。
有一天,遇上李长弓,他悄悄地问我,中央给你回信啦?我朝他说,别提了。接着我就拉着他走了几步,诉说我内心的苦衷。可他的分析却是完全与我相反的结论,这又使我精神大振。他简要地说了两点:一是回信的速度之快,在春节前寄出、春节后就收到回信,说明中央对我这封信的重视;二是我的信转人民日报,对人民日报而言,如同接到圣旨一般。
所以他连说,好事,好事!他轻轻拍着我的肩膀说:“你是有福之人。”接着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又似乎从内心深处呼出地说:“愁神去,喜神到啊。
”我觉得他这句话里,还含着当初看到我的信时的担忧,果然他说出了:“若把这封信转到上影组织上,那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他才爆发出关爱我的感慨,可见他的为人多么的真诚。
于是,我不得不把真情告诉了他,凑近他耳语了一番。他高兴地“啊”了一声,说我原来有尚方宝剑。我请他绝对保密,他就爽快地哈哈笑着:“对你这件事我可以保密,可她与周总理的关系,你们小青年不知道,我们老一代电影工作者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只要她去北京,总要到总理家里去,邓颖超大姐见到张瑞芳称她小芳,像干女儿似的。”李长弓用问话的口气对我说:“你知道吗,有人在背后说她是通天派,在电影生产遇上问题,电影局领导常派她去北京说情。
还有,周恩来在1949年上海第一次文代会上为张瑞芳在大会纪念册上的题词是‘为少找麻烦多做工作而养好身体努力!’这句话看来很普通,朴实无华,其实好似从浩瀚的宇宙中概括而成的。张瑞芳当然知道这句话有深刻的内涵,但她是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什么都不顾的人。”这时我才恍悟,她要我把信写给周总理的原因了。
李长弓朝我笑笑,又认真又肯定地说:“不久你将会收到家乡的喜讯了。”
果然不出李长弓所料,我记得刚过完元宵节,接到了父母的来信,告诉我住房已经赔偿了。这封信是我伯父替我父母代写的,最后附上一句:“侄儿,落实政策虽好,但潜藏着危险,能否告假回家一趟。”见到家书,既高兴,忧愁又涌上心头。
我即日启程,急急忙忙往家赶。若在今天,两个小时就可到家了,可在那个年代,乘长江轮又转长途车,等船等车,又路经乡村小道,受尽苦情,花上20多小时才到家。只见父母他们乐开了花,政府出资购买赔偿住房,比自己原来的还要宽敞、明亮。父母还告诉我,当年被毁的住房作价400元,作为弥补数年来的精神损失费。看到的,听到的,对一个家庭来说,尽是喜事。
可我伯父不知怎么知道的:家中所获一切成果,都是由我向中央写信而得到的,用他的话说,“这是惊动了天,震动了地方官,闯下了祸”,将来他们若把我家里人在农村的表现随便抓一些问题,把材料往我厂里一送,很可能,轻则批评教育,重则被开除。
我一听,伯父的话不无道理,这无形中给了我精神上的压力。有一天在食堂午餐后,碰到了严励先生,他捧着碗点头示意我,我就与他上楼去。我把从老家回沪后的忧愁和喜悦向他做了汇报,请他转告张瑞芳同志。
没想到进了他的办公室后,他顾不上吃饭,就把张瑞芳的态度告诉了我:要我别怕,农村问题,中央已有定论,将共产风、瞎指挥风、浮夸风、吃喝风,定为四风,你家里的事就是受“四风”之害的严重后果的典型。听到张瑞芳这么说,我的心放宽了许多。
以上经历的一切都说明,张瑞芳鼓励我向中央反映情况,她的这种魄力,这种大无畏精神,常人是很难做到的。翻开她的人生画卷,不难发现她的一身正气是长期养成的,她有明辨是非的革命斗志,在复杂的黑夜世界里,为追求光明,1931年年仅13岁的她离开温暖的家,在严酷的环境中,去学习、去演出,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参加抗日战争和反蒋斗争,并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一生是为真理而奋斗的一生。
她对我的关爱,体现她的大爱,她心里永远装着人民,时时处处牵挂着国家大事。正如一位业界资深人士如是评说——她是“具有特殊魅力的表演艺术家与高尚人格的革命家”。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鲜活人物于2012年6月28日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她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