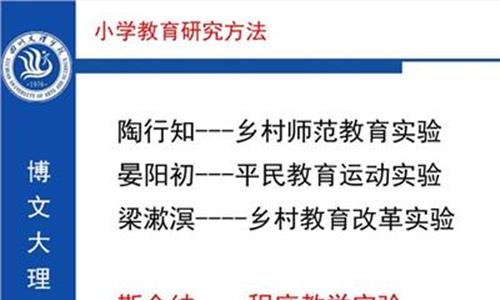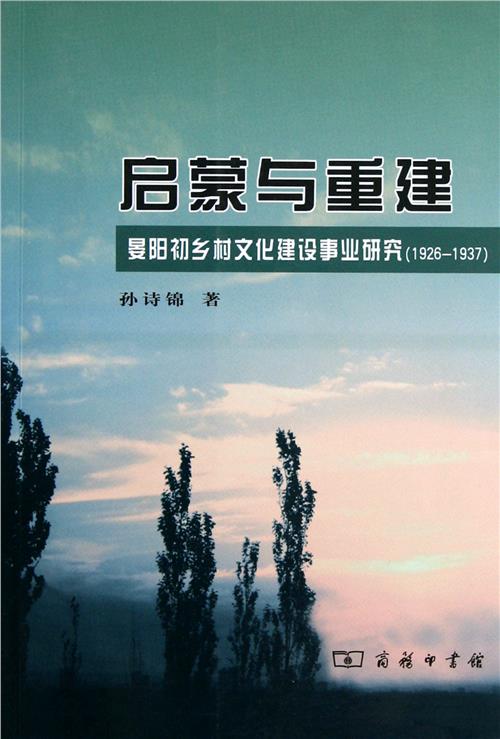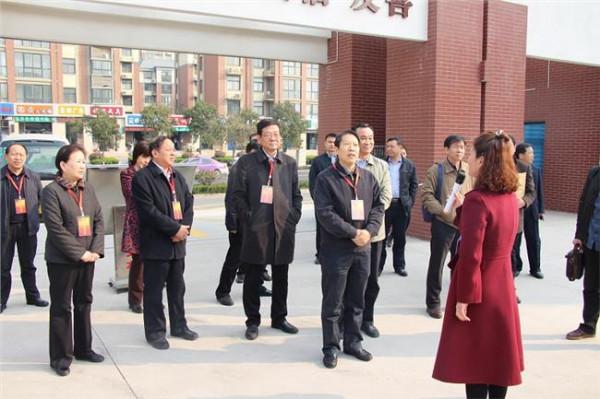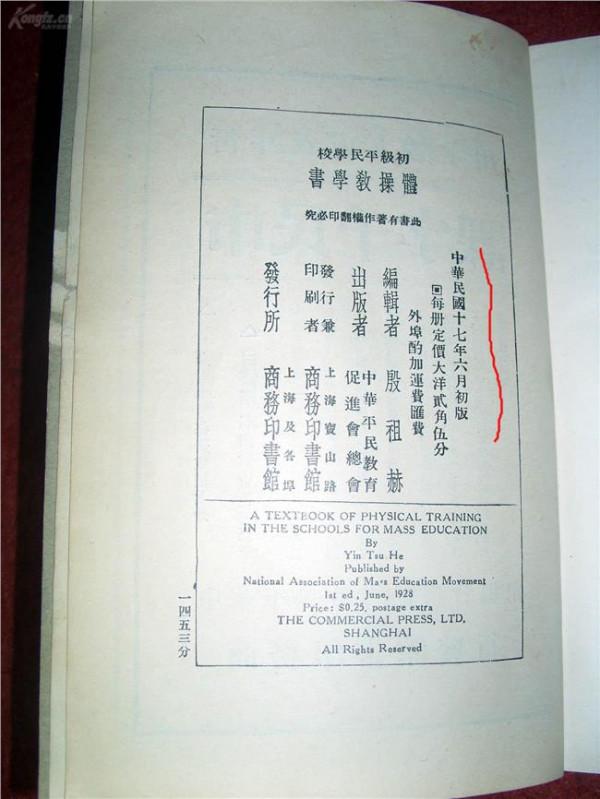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棵成长中的树
动手写这本书之前就决定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应当以一个群体出现。
NGO是一个太过丰富的存在,我不可能全景式地展现,只能在一部分组织里采访一部分人,之所以这样表述乡建学院,不是因为他们所从事的新乡村建设正高调登上各类媒体的头条,在我最初这样决定的时候,乡建还是一个只在小圈子里使用的词;更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都知道“三农”是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指望几个年轻人在农村几年就能改变什么根本不现实。

吸引我的是乡建学院的那些人,那些背景、经历、想法各不相同的年轻人,他们怎么走到一起,并且,这些个性迥异的年轻人形成了一种特别的氛围。
在我的眼里,乡建学院就像是一棵树,一棵有着自己的生命和呼吸的树,每个人都是这棵树上的一片叶子,当我按照这些“叶子”出现的顺序写下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也是在试图搞清楚为什么会长出这样的一棵树,这棵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命。同时更加关注的是:这棵树将长成什么样子,“叶子们”会有怎样的未来。

乡建学院的故事要从温铁军讲起。
原以为温铁军担任院长的乡村建设学院就不是一个NGO,直到看了一份温铁军与村民交流的纪录,从中得到几个让我比较吃惊的信息,发现乡建学院是个民间组织,而且处境似乎非常不好。

我看到的是温铁军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首期农民夜校上的录音整理稿,学院就建在这里。三年前村子里的农民集资39万买下了一所废弃的中学,与《中国改革》杂志社、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晏研会)、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合作办起了这所学院,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温铁军任院长。

在那次讲话里,温铁军说“以中国改革杂志社名义出的这三万块钱,其实是我的个人存款。到第二年我们增加一倍,三家单位各出六万,拿的还是我个人的存款”,后来,乡建学院农民学员回乡成立合作社,又拿出了自己的钱做启动资金,每个合作社五千到一万不等。
温铁军之所以把自己出钱的事情拿到会上说,是因为老百姓觉得学院办了快两年没看到什么回报,“有这样那样的说法”,温老师说“这个说法让我心里面有点伤心”,并用反反复复地讲在学院长期工作的几位年轻人多么难、多么不容易,我看温铁军用非常动情的语气谈到来自香港的小仙在华北平原上感冒发烧的冬天,谈到脚部骨折打着钢钉一瘸一拐的小潘,好言相劝请求乡亲们将心比心,“希望父老乡亲们能多一份同情,多一分理解”。
温铁军的那个讲话苦口婆心,又有点委曲求全的味道,还一再给翟城父老陪不是,因为“学院种瞎了乡亲们给的好地”,又掏钱又坐蜡:温铁军算是被乡建学院给“拉下水”了。
邱建生:用什么照亮心灵
邱建生,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主任,理事,法人代表。2003年7月来到学院,晏研会总干事。 邱建生就是那个把温铁军拉下水的人,一提到这事,连他自己都笑:“温老师也这么说,他是被我拉下水的。”
朱小娥:我不理解他,但我支持他
朱小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后勤助理。2003年8月来到学院。 我对朱小娥说,除了邱建生之外你是在这个学院待得最久的人,她说我错了:“邱建生总出去有事,我才是在这里时间最长的人。”
袁小仙:最根本地做一件事
袁小仙,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助理,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4月来到学院。 袁小仙曾经有过多年在国际和地区间NGO工作的经验,我想请她介绍一些与NGO有关的情况,她的回答让我出乎意料:“NGO本身不是中国特点,有世界性的东西。而目前在中国,太把它神话了、美化了、道德化了,而且好象也太热了,成为一种时髦,有点像是新茅坑大家都想蹲一下,不利于它的发展。”
潘家恩:淬火激情
潘家恩,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副主任,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定州示范区协调员。2004年4月来到学院。 比一个人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团队,比一个团队更重要的是你这个团队是否有自己的文化。
黄志友:赤脚走在土地上
我在来学院之前,就听到了许多“传说”,听说这里有个极端环保主义者,热爱所有的生命,甚至害虫,认为大自然中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为保护院子和菜地里的草跟同事吵架。这些传说里的主人公就是黄志友。
2015年
回访黄志友:从“极端环保主义者”到迷茫“新农人”
严晓辉: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严晓辉,服务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生态建筑工作室,2004年10月来到学院。 “投笔从农百夏三伏冬数九收获困惑,围炉夜话你两语我三言相信未来”
袁清华:摸索在困惑与失落之间
袁清华,服务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社区发展部,2005年7月成为学院员工。 袁清华是抱着在这片土地上干一辈子、扎扎实实为农村做些什么的想法来的,本来就出身农家,也做好了像农民一样耕田种地的准备,但当理想和期待真正落到土地上,特别是落到牛粪里的时候,还是有一些不适应。
刘健芝:读书应当有用处
刘健芝,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全球和平妇女”联会理事、国际委员会东亚区统筹人。 “念书应当有点意义,而这点意义又应当放得远一些,香港连着中国,中国又连着世界……”刘健芝经常这么说,这是她讲给学生的一句话,也是她用自己的人生实践着的一句话。
谢英俊:安得广厦千万间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乡村建筑工作室负责人,2004年来到学院 如果一个建筑师声称中国八亿农民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通过合作建房住上欧式外形的生态建筑,人们恐怕就会张大了嘴巴:这个建筑师玩得太出格了吧!谢英俊笑了,依旧是那种斯斯文文不紧不慢的语气:“这很现实的,只要我们肯干,完全没有问题。”
将乡建学院比作“一棵成长中的树”,我在这个题目里寄以期待。同感者应该不在少数,大家到乡建学院举办培训,带着孩子来做志愿者,呼朋唤友下地参加劳动,与老乡一起做手工月饼,去那里过年守岁……那个时候,乡建学院对大家来说不仅是一个地方、一种氛围、一件事业,也寄托了太多人殷殷切切的期盼。没有想到,我的书还没出来,就听到学院被逐出翟城的消息。
此前似乎一切形势大好,《合作社法》呼之欲出,三农问题备受关注,学院和温老师接受了越来越多的媒体采访,也开始与政府的合作,06年开春邱建生远赴海南,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代表,任海南儋州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所建“海南石屋农村社区大学”是全国首家建在农村的社区大学。
翟城的乡建学院人丁兴旺,常驻工作人员达到20多人,制订了三年发展规划。新建了礼堂,是谢老师设计的半地下的大棚礼堂,在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小小的生态建筑群,改装了宿舍,可以同时接待100人培训……变故来得猝不及防,除了离开,别无选择。
2007年5月16日是告别的日子,学院地里的麦子已经结穗正在灌浆。后来我几次重返学院,看到他们离开时正在读的书还留在枕边、衣服还搭在椅背上——直到离开的那个时刻,都不愿相信真的是个告别。
2007年冬《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第一版艰难面世,在万木凋零的季节拿到与期待相去甚远的书,学院人事全非。出书之后在北京有过一个小小的主人公聚会,乡建学院的年轻人中,尚在北京的袁小仙、袁清华、黄志友到场。
邱建生严晓辉在学院离开前已经南下(晓辉去汕头一家食品企业做管理),学院离开翟城后潘家恩去香港读书,刘健芝在北京回龙观租了一套民房,后来干脆筹钱买了房子,成了学院同仁在北京落脚的大本营。留下来的人挤在那个狭小的空间里学做城市动物,用“活着就是胜利”彼此鼓励——明知道这里不属于我,但必须适应这里的生活。
学院的年轻人性情各异,但有一点是共通的——热爱土地,印象最深的是黄志友,常常会看到他甩掉鞋子用自己的双脚去亲近土地。自从大学毕业加入乡建学院,黄志友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不论这个机构在哪里。城乡结合部的公交车是最难挤的,进城之初,小黄说到挤车的感受:“上不去也得往里挤,女售票员一开始是拚命喊,后来就会直接用脚蹬,把人硬硬地塞进去。
觉得自己就像个货物。”我真的很担心这些“属于土地的植物”进城之后水土不服。好在植树们有着坚忍的生命力,硬是在北京的水泥地里扎下了根。
学院进城,最早做的是国仁城乡合作社的事情,所谓“城乡良性互动模式的探索”,一开始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为北京市民做农产品配送。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三轮车,车上除了装着货还站着大管家小流,手拿一份北京地图充任罗盘“瞎指挥”,在他前面汗流浃背的苦力则是总经理袁清华。
2008年终于在海淀后沙涧找到一块地,与公司合作建生态农场,要与所在村镇政府和合作企业做大量的协调工作,不仅要经历与商业机构的磨合,也在承受外在压力转为内部矛盾的磨难,是这些热爱土地的年轻人不擅长不喜欢、与自己的能力也不对路的事情,但清华对我说:“做不了也得做,因为我们都不想让学院散掉”,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他像个战士。
邱建生一直在都自我追问,探寻如何照亮内心深处那些黑暗的角落,2008年受洗成为基督徒。尽管这些年来主要在南方,但一直说自己是“学院的人”。他似乎总是在低谷里,总是见他在弓着背爬坡。每次见到都会有很多很麻烦的消息,合作方的变化、师长的误解、资金困局……生活困顿和事业变故此起彼伏,说不清哪个更糟,就像北京的数九天,搞不懂哪天更冷。
我们几次偶遇都是在北京的寒冬里,小邱身上的衣服总是单薄得惊人,他给我的解释是自己马上就要回南方,不想被太多行李拖累,“反正我年轻、身体好”。
每次目送那个衣着单薄的影子融入北京的寒风心里总是百感交集,不知道这个世界还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来考验他。他和小娥的两个女儿在展转飘零的岁月里降生,生活窘迫一如既往,每每听到从他们家过来的朋友感叹只有小娥这样的伴侣能够跟小邱一起面对这样的生活,因为“小娥心大”。
我一直没有见到他们的两个女儿,相信她们会像父亲一样眼神明亮像母亲一样心胸开阔。
在翟城的学院里见到的邱建生让我联想到羊,此后见他,总是会想到“打不死的小强”,不管处境多么艰难,总能听到他的新进展,石屋社大、国仁工友之家、福前培训基地、国仁社区大学、杭州草根之家、天津国仁工友之家……
山回水转,尽管不再有“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这个名头,但一直能与在学院结识的人遇到,在北京“活下来”之后,差不多每年都会有一次与农业有关的研讨会,各种各样与学院有关的人会从四面八方聚拢,让人高兴的是总会见到学院工作团队的年轻人,不管他们是“回归主流”、在外读书、去其它公益机构工作还是留在学院,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学院没有散”。
偶遇学院年轻人最多的是5、12地震后在四川灾区,虽然每次相遇都出乎意料,但在那种地方遇到他们那样的人也是情理之中,很自然。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2009年年末,在深圳建筑年会谢老师的生态建筑展区,遇到多年不见的严晓辉,还当面确认了一个好消息。“下海取经”三年的晓辉在那年最冷的季节里回归学院,接任总经理,与学院同仁一起面临转型的代价。我曾经问过他做此选择的原因,他说得很轻巧:“我一直都是学院的人啊”。
所谓“学院地的人”,就是一直对这片土地、对这件事情有牵绊、有付出,不管他们远行还是回归。袁小仙不断对家人食言将回香港的日期一拖再拖,和学院的年轻人一起度过了来到北京之后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同时在人大读博,2010年回到香港重新适应故乡生活;潘家恩在香港读书的同时,一直在主持学院的研究和培训工作;袁清华结束泰国“米之神”两年学习后回到“小毛驴”,开办田间学校、主持农业技术培训;黄国良则去重庆开办了“打平伙食堂”……
自2005年起与晏阳初乡建学院结缘,不管他们展转到哪里,不管名头是“**公司”“**农场”还是“小毛驴”,提到他们,我习惯的说法还是“学院”,看来我也应该算作“学院的人”。我与学院,不仅仅是一种写作者对采访对象的关注,而是与自己的生命建立了某种联系,邱建生那句“照亮自己内心深处那些黑暗的角落”也成了我的自我追问。
当我向人介绍学院的年轻人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会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这里来,鼓励儿子与严晓辉交朋友,鼓励女儿与黄志友谈恋爱”。与学院结缘的第二年,就带儿子来这里过暑假,让他随晓辉去河南盖房子。
我是一个在计划经济、粮票布票年代长大的人,能够感受到不仅“外在”对人的挤压无孔不入,人的自我束缚也同样可怕。回首自己,不光是处在“自我”与环境压力和父母要求的纠扯之中,也一直都在主动被动地“说服自己放弃自我”,直到不惑之年才想清楚了放手去“做一回自己”,这种作茧自缚的痛楚类似百年前中国女性“裹脚放脚”。
到了年轻一辈的“学院一代”,甚至更年轻的一代,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我深知这般“成长的代价”太过昂贵,不想儿子也受同样的煎熬,我一直提醒自己不给他类似的压力,但不等于这个世界不挤压他。
我带儿子来学院,并不要求他“成为**”,我只是祝愿他的青春心怀梦想眼高于顶,不要年经轻轻就用垂老长者的标准自我审查,敢于在现实土地上放手活出自己,犯年轻的错误付青春的代价。晓辉是小小年纪就能自我解放的人,让儿子与这样的人一起打混,能够真切地看到现实世界里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活法存在。
我与NGO结缘的十几年,也是中国草根NGO发展的时期。算来,“学院一代”年轻人得算是草根NGO里“职业化第一代”(我称他们为“N一代”)。最早的NGO人产生在上世纪90年代那个特殊时期,人数极其有限且较多任职于国际NGO或者海外机构(如李波),这类机构的发起方式、资金来源、注册管理与草根NGO几乎没有可比性,不是我的观察对象放开不表。
一开始真正做事情的草根NGO少而又少,投身其中的人大多来自妇联、科研机构、各级事业单位,不管他们的年龄是60后、50后、还是再年长一些如红枫王行娟自然之友梁从诫等前辈,都可以归为“NGO的前世代”,这一拨不仅人数极少,而且与“社会主流”的生活方式、与体制之间有这样那样的关联,就算不拿体制内的工资也都是“半路出家”,个人生活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也都是在主流中完成的,很难由此观照NGO生态演进发育。
进入新世纪开始有一些70后、80后年轻人进入NGO,除了邱建生和袁小仙,学院一代进入时大多刚刚离开高校,如今“奔三”,正好是立业成家的年纪。
很幸运小邱有小娥那样的伴侣共同面对艰难困苦,这样的付出超出了正常的承受限度,不能指望所有的姻缘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草根机构如何保有人才实现机构发展与提升一直都是个坎,好多人在草根机构干一段离开,去待遇更好的基金会或者国际机构,再就是回归主流,去公司里找工作或者自己创业做生意。
谁都要面对攒钱买房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问题,那些已经做出的明确选择,一生、或者很长一段时间都要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职业化的NGO人,要面对种种现实问题。
我没有女儿,当我说“鼓励女儿与黄志友谈恋爱”的时候常被人笑“这样的丈母娘还没有生出来呢”。职业化的NGO人如何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侣,既能认同他们的理想和人生选择,又能接纳他们的收入水平在现实生活中立足,是一道坎。
中国的NGO要实现职业化、专业化,身在其中的每一个NGO人都要面对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的现实问题,这不仅建立在他们对自我的认同基础之上,也需要更多更广泛的他人的认同、社会的认同,恋爱婚姻当算重要标志。“N一代”们在草根NGO里确立自己当下位置与未来发展的过程,也是一种寻找自我认同、实现社会认同的过程。
第一对因为学院这个媒介相识相恋的情侣是来学院实习的婷婷和黄志友,如今他们的女儿已经两岁多了,在离农场不远的村子里租住民房,清贫温暖的小家庭不仅分享小黄的善良美好诗情画意也共同面对所有的现实问题。学院的年轻人相继结婚生子,聚会时差不多够组一个“儿童团”,“N一代”的孩子们的出生,似乎可以看做这个进程中的一种标志。
这本书写作期间,我曾在自己的泰山小院里迎来了几拨朋友,在无花果树下煮酒夜话,扯各种各样八卦正卦话题。发现NGO里的姻缘越来越多,最早的每一对姻缘都作为一个传奇被人传诵,现在抬眼一看,地域、年龄、种族、国籍都不是阻碍,大家也不复传诵这些姻缘里“传奇”。我们八卦的结论是: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可能性,而且越来越有平常心了,人间烟火,柴米油盐。
不仅仅是学院人作为一个个体把根扎到现实生活里,NGO机构所承载的理念、方式也在不断地寻找认同,要扎根。一番番冬去春来,“小毛驴市民农园”已经成了北京市民中的一个品牌形象,这些年来所获奖项中既有“福特汽车环保奖”这样的民间鼓励,也有来自北京市官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创新奖”一类政府奖项。
每次去学院,都会看到一些变化,新建了市民农园、生态猪舍、鸡栏,有面向市民的共同购买、也有面向农户的生产地加盟,还在做各种各样的市民活动,一开始是在农场做,后来也进入社区做活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起“小毛驴”,说到“小毛驴”带来的启发与改变。乡建学院这棵树在北京活下来了。
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这些树们不仅活了下来,也在改变着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