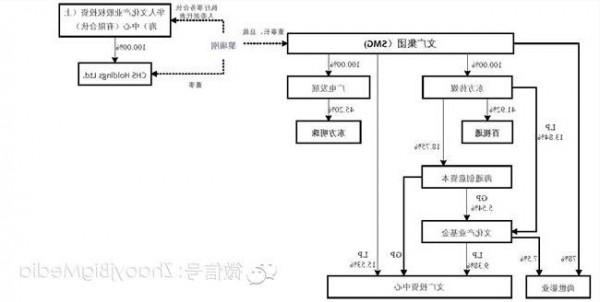《与天下共醒》李怀宇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内容介绍】 作为“文革”后发挥了重要影响的一批知识分子的代表,葛兆光、钟叔河、周振鹤、吴思、邓晓芒、许纪霖、李辉、陈来等当代著名学人,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出发,观照历史与未来,思考个体与家国,瞻望世界与中国,对当代中国之由来与走向提供了各自的解答,赤诚之心见于言表。
在这样多元的答卷中或可发现无限可能,在思想的碰撞与激荡中或能寻得醒世良方。他们的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也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历史脉络。
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特为本书题写书名。
【作者介绍】 李怀宇,广东澄海人,多年从事知识人的访谈和研究。作品有《访问历史:三十位中国知识人的笑声泪影》、《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等。
【原文摘选】 葛兆光:重新思考“世界之中国”
近年来,每年葛兆光有一两个月客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余英时先生时相论学。余先生有言,“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这不妨碍他有中国情怀。葛兆光也说,“我不会和政治近身肉搏,那不是我的特长”,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政治关怀。
在视野所及的学术界,葛兆光看到:“在美国,学术和政治离得很远,所以在学术上专业化、规范化和技术化相对比较厉害。但中国是学术与政治始终分不开。我想,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还是很厉害,道统对政统,总是希望有所制约;当思想不能够自由表达,就要通过学术来表达,那么,学术背后的政治关怀当然就很厉害。
在学术尤其是在历史领域中,思想史是最容易涵纳政治关怀的。” 在《宅兹中国》中,葛兆光强调有一个历史中国,有一个政治中国,还有一个文化中国。
文化中国就像余英时先生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葛兆光专门请人刻了一方“无处非中”的印章送给余先生。
“这句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地球是圆的,没有哪里不是‘中’。艾儒略当年写《职方外纪》,恐怕就是为了破除中国人认为自己总在天下中央,别人都是四夷的观念。在一个球面上,可不是哪里都是‘中’吗?‘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跟‘无处非中’意思好像可以相通,也合乎‘世界公民’的看法,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和身处某个国家的生活现状,完全可以结合起来。
其实,余先生最爱中国,所以才有《情怀中国》这样的书名。
我经常讲,最深切的爱国情怀,有时反而常常在外国。” 坐看学界云起云落,葛兆光不免有一点悲观。他说:“欧美学术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激烈争论到最后,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可我们这儿学术争鸣好像是一个反常现象。自由争鸣的环境是很多人一起辩论,却并不影响到生死存亡。可是,现在的制度使得学术辩论有点儿像生死存亡或者是争一块大饼,因为大家都像是在一个大锅盖下面,大家纷纷试图找到自己存活的地方。
如果说自由的学术争鸣,首先,舆论环境和学术环境应该是自由的,可是,现在有些话总是要曲里拐弯或者含蓄隐晦地说,而且,更可怕的是,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上位的人听的,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还有些小声说的话,倒是说给本土的人听的,所以,声音就不太一样。”不久前,葛兆光写了一篇文章叫《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
李怀宇:在《宅兹中国》里,你写的问题看起来非常宏大,但是用了很多具体的案例来分析这些问题,当初的思想起源是什么? 葛兆光:写《宅兹中国》有一些原因,我写《中国思想史》到最后一章叫作《1895年的中国》。
李怀宇:张灏先生认为1895年很重要,是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关键年份。 葛兆光:我跟张灏先生的意见完全一样。
我们都认为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年头,并不在1840年,而是在1895年。这是因为中国人的观念被真正触动,觉得不变不行,而且非大变不可,是在甲午战争之后。
中国不是被英国、法国这些西方“列强”打败,而是被日本这个过去的“岛夷”打败,中国才会被真正触动。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被拖入一个更大的世界里面,中国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中国。我本来的计划里面,是准备要写第三卷的,第三卷里写1895到1989年。
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20世纪”,20世纪提前在1895年开始,提前在1989年结束,这是一个完整的时段。后来发现没法写,资料太多,我也没这个能力。因为我的专业毕竟是偏向古代的,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
但是,写到第二卷最后的时候,我在欧洲访问,在那里就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当中国1895年不得不进入亚洲、进入世界,已经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自我完整的天下帝国,那么,这个时候,中国怎样反过来重新界定自己?中国的疆域、民族、国家的定位到底应该怎么样?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20世纪的中国,有三个思想潮流是很重要的,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当然还有一个是也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
这几个主义在互相角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中国怎么样重新建构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怎么样融入世界,并跟世界平等相处?由于传统中国有一个朝贡圈的历史,因此还有怎么样重新跟周边妥善相处的问题。
所以,重新界定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觉得中国这个国家是非常特殊的,它跟欧洲不一样。欧洲那些国家是14、15世纪以后逐渐形成语言、民族、文化重叠的现代民族国家。
中国从秦汉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可是这国家变来变去,一会大,一会小,到了清代甚至把满、蒙、回、藏、苗都给整编进来了,就形成一个非常特别的庞大的共同体。这共同体怎么样包容不同民族,怎么样界定自己是有限国家而不是无限帝国,这些问题很复杂。
所以,我写完《中国思想史》以后,觉得没有能力去处理第三卷了,我就开始看一些跟中国有关的周边的文献,像日本、朝鲜的东西,看着看着就产生了一些想法,包括我们现在提倡的“从周边看中国”。
从2001年到现在,我一直在琢磨所谓亚洲或者东亚的一些问题。这就是我写《宅兹中国》的一个背景。特别是,我觉得现代中国仍然是天下帝国和现代国家在观念上纠缠在一起的国家,也就是说,在有限的国家范围,却又有无限帝国的梦想,一会好像是世界中心了,一会好像觉得世界有一个美国老大帝国也蛮不高兴的。
这些问题除了现在政治学的解释以外,有没有一个思想和历史的解释?中国现在困境很多,周边在12、13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在意识上自尊,自我中心化,所以日本、朝鲜和越南等都和我们面和心不和,开始瓦解我们这个想象的“天下”。
到了明代,更远的西洋人来了,中国被抛进一个新的大世界里面,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这也是一个大困难。
到了清代,藏、回、蒙、满、苗、彝都在中国里面,认同问题怎么办,文化怎么样共处,多民族国家怎样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在过去欧洲人的观念里面,多民族是不可能成为国家的,认同建立不起来呀,比如说,比利时北边是讲弗莱芒语就是荷兰语的,南边是讲法语的,东边还有一小块讲德语的,于是,关于认同和国家问题就闹得不可开交。
在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里面,要从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国家,确实是挺麻烦的事情。
所以,国家、疆域、民族、文化认同很重要,我写《宅兹中国》,想从历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有很多人的想法是想当然的,中国就是中国,甚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既然 所辖那么宽,那么,自古以来这些地方都应该是中国领土,各个民族自古以来就归入中华民族。
可是,现在我们面临很多问题,包括南海问题、东海钓鱼岛问题、东北(高句丽)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等等。
现实的这些问题,在我看来也是历史问题。因为我是做历史的,我只有从历史的角度研究,别的我不管。我把历史讲清楚,然后怎么办,再由别人来说。这就是余英时先生讲的“遥远的关怀”,而不是我说的“近身肉搏”。
《宅兹中国》是我十年来陆续写的,里面包括跟日本学者的论战。日本人认为,有一个“亚洲”或者“东亚”,可以建立一个文化共同体,我们国内有些人也跟着瞎起哄,好像亚洲共同体或者东亚共同体,可以跟欧洲共同体、跟西方世界并峙或对抗,好像我们东亚可以把欧洲作为“他者”。
《宅兹中国》这本书尽管现在国外也很注意,但是说老实话,我还是写给国内人看的,包括我对海外一些中国学论著的评价,其实更重要的,都是针对国内学界的。
李怀宇: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提出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中国在晚清经历了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用现代话说是全球化的浪潮,对天朝上国的心理打击也好、影响也好,产生的变局会不会越来越大? 葛兆光:梁启超说的那个三阶段,他是指中国不断地被放在更大的世界里面。
其实,梁启超这个讲法比较有现代性,他是说,中国过去是一个封闭的中国,慢慢地,要跟亚洲的国家打交道,所以是亚洲的中国,最后,一定要开放面向全世界,是世界的中国。我觉得,梁启超这个说法大体上没有错,但也可以反过来说,从观念史的角度,中国人在古代是“世界的中国”,它认为自己就是世界,我就是天下;到了宋元以后,才慢慢意识到周边还有这么多地方,才慢慢地变成“亚洲的中国”;到了现在,应该了解“中国之中国”,就是说它是一个有限的(多)民族国家。
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近三十年来,很抱歉我非常不喜欢用“崛起”这个词,我更愿意说,中国在不断地“膨胀”,刺激得有些人观念也膨胀了,就觉得中国现在也应该成为世界里的大中国,这跟梁启超的意思是不同的。
很多人提出,当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就应该拿出大国的东西来。这个说法表面上看来是有理的,但很容易背后隐藏着一个很强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现在有些人提倡“天下主义”,想重新把过去的“天下体系”端出来。
有些学界朋友说,现在全球化的世界体系是在美国主导下的世界体系,所以要提倡传统中国的“天下体系”,可是,天下体系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中心的,这中心就是我天朝,是以自我为中心。
所以,天下主义表面上看是世界主义,实际上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它有可能把旧资源拿出来,重新包装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也有人认为,中国现在了不得了,所以应该拿出影响世界的价值观,要弄形象工程搞文化输出,这和政府满世界到处建孔子学院很合拍。
其实,当一个文化是好东西的时候,它自然会走出去,问题是要拿得出好的文化。我很不喜欢提“大国”这个词,中国内部问题很多,所以,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建造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多)民族国家,不要急于在世界上膨胀;先把自己现代的、民主的、有限的国民国家搞好,让人民对这个国家有信心。
何况我们内部的满、蒙、回、藏、苗,还有一个台湾到底怎么处理,都需要思考,对不对?现在连自己的事情还没处理好,如果迅速地膨胀,很容易被人家联想像大秦帝国,或者像一个蒙元帝国。
所以,我不赞成去简单地提“天下主义”,中国是应该有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但现阶段,还是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弄好点再说。
现在的中国,无论是政府也好,学界也好,传统帝国时代的天下观念还存在,就是这个帝国或者说文化共同体是没有边界的,还是希望能够蔓延膨胀开来,还是希望能够仍然是老大帝国,总觉得有限的民族国家好像不怎么过瘾,这是一种受压迫受欺负之后的反弹。
当然,在文化上我们都认同中国文化,但我不赞成简单地把文化认同跟政治认同重叠起来。我一再强调政府不是国家,国家不是祖国。政府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常常假借国家的名义,让人们无条件拥护。
按照以前的看法,有人到美国成为美国公民,那么他就不爱国。可是,你看到很多入了美国籍、入了欧洲国籍的人,一旦中国跟外国发生什么纠纷,包括体育比赛,他还是站在中国立场上的。而且,当他们觉得自己在异文化的压力下,常常更凸显自己的文化立场,所以,我看那些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好像比我们在国内的人还要厉害。
国家只是一个现实的合法的疆域空间,不要简单地把它当作文化意义上的祖国,祖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文化概念。所以,以前有句名言说,流亡的人有可能没有国家,但是也可能有两个祖国。我写《宅兹中国》就提醒说,不要简单地把政府当国家,把国家当祖国。
【目录】 葛兆光:重新思考“世界之中国” 周振鹤:求真是学术的生命 钟叔河:期待中国走向世界 朱 正:我是唯恐天下不治 许纪霖: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邓晓芒:哲学就是生活 王学泰:中国历史上有独特的江湖文化 吴 思: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潜规则里 张良皋:向往文艺复兴的时代 章汝奭:字再小也有大气象 董 健:思考当代知识者的命运 黄天骥:文章中冷暖自知 郑 重:在业余兴趣中探寻艺术天地 李 辉:用宽容之心追寻人物与思想 骆玉明:好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提出问题 陆建德: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一点自卑情结 陈 来:国学研究的视野要面对全世界 尤西林: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危机与重建 杨小彦:视觉时代的探索者与实践者 曹锦清:对社会复杂性心存高度的敬畏
【图书信息】 书名:《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出版: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1415-7 作者:葛兆光 吴思 等口述 采写:李怀宇 时间:2016年4月 第1版 定价:49.00元 开本:16开 装帧: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