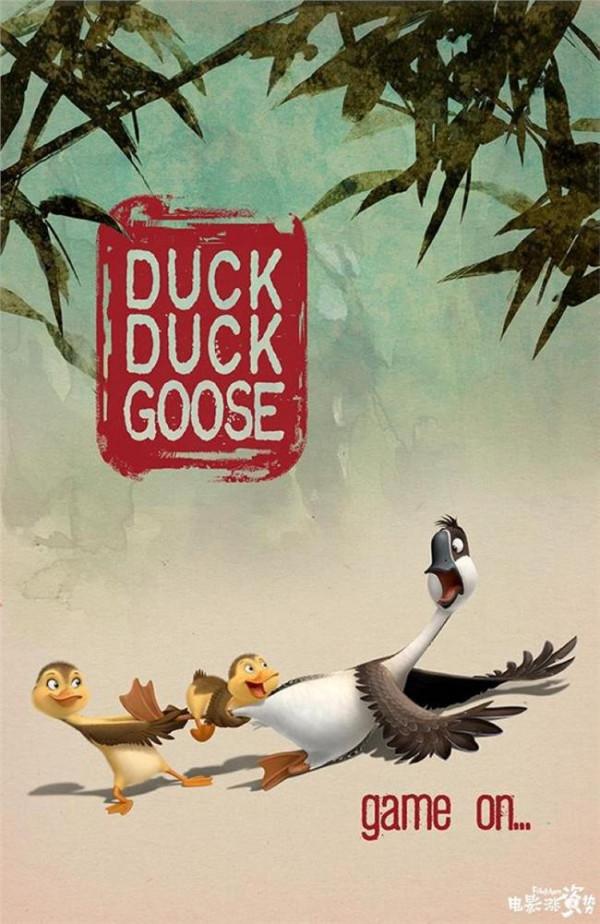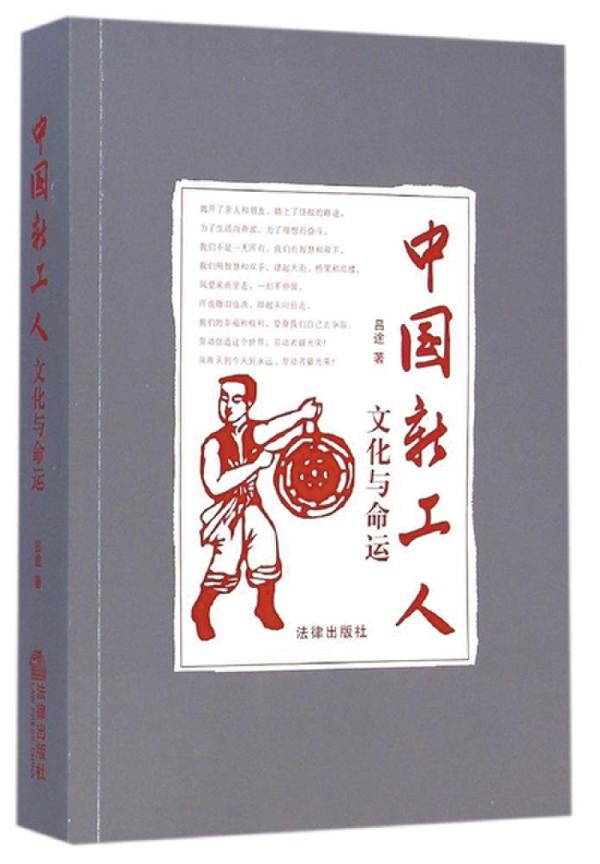郑小琼女工记 郑小琼:诗集《女工记》的后记
郑小琼,女,1980年生,2001年来东莞打工并写诗,有多篇诗歌散文发表于《诗刊》《山花》《诗选刊》《星星》《天涯》《散文选刊》等报刊,作品多次入选年度最佳等选本,曾参加第三届全国散文诗笔会、诗刊第二十一届青春诗会。获得"利群•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多项大奖,与韩寒、邢荣勤、春树等一同入选"中国80后作家实力榜"。
郑小琼:诗集《女工记》的后记
八年前,我写下一首叫田建英的女工的诗歌,她是以捡破烂为生的四川达州人,1991年来广东,1997年到一个叫黄麻岭的地方捡破烂。我认识她是2003年,她来广东十二年,四十六岁。我有很多旧报纸与书籍,差不多全给她了。
她给我说她和她家人的故事,我写了她以及她一家人的故事。那时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写《女工记》,只是觉得她和她家人的命运很悲惨,我当时是流水线工人,一天十一个小时班,上半月是夜班,下半月白班,我的工号是:245,装边制开关,拉线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女工,手工装配螺丝、弹弓……
2004年,我在樟木头打工十多年的亲戚家里有事辞职出厂,回四川老家。半年后再来这边打工,她已三十七岁,在工业区转了一个月,都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年龄偏大,所有工厂都拒绝招一个中年女工,她在这边有十三年的打工经历,做的都是流水线工种,没有技术含量。
像那样的年纪,当时的工厂招普工几乎不考虑,工厂只招18岁到35岁的女工,大部分只招18岁到28岁的女工,她只好选择回家。我送她上车时,看着她过早爬上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看着她走进火车站的背影,我一阵心酸。
在她转身的那一刻,我从她身上看到我未来的影子,我强忍着不让自己流泪。她上车后把脸贴在窗口时落寞而无奈的眼神时时折磨着我,我写下两首诗,一首便是《三十七岁的女工》,在另外一首《黄麻岭》中我写到“风吹走我的一切/我剩下的苍老,回家”。
是的,我注定跟她一样,最后只能带着苍老回家。城市终究属于别人的,我只是过客,只是南飞的候鸟,注定漂泊不定,没有落脚的地方。
我像无脚鸟一样飞着,没有停下的地方。这种过客心理让我对生活充满悲观情绪。我不知道该走向那里?未来在哪里?走在工业区大道,看到一群群年轻女工,她们穿着工衣,看见她们疲倦的面孔。想到她们渐渐老去后,回到北方的情形。我想起我自己,还有拉线上的工友,觉得想写一些故事,开始注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2006年,由于请假太多,我被工作了四年的工厂辞退。走出工厂的瞬间,心里空荡荡的,拎着行李走在黄麻岭的凤凰大道上,面对三大箱书和日常行李,我不知道自己该走向哪里,在生活了五年的城市,我找不到一块可以安放我行李的地方。
天下着雨,我把行李寄放在工厂附近士多店里,给了十块寄存费,一个要好的姐妹陪我去城中村租房子,雨水打湿了身体,我惶惶如丧家之犬,不知所措。尽管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但我仍然不想回南充,我知道回南充以后,呆上一个月或半个月,我还得出来,还得来广东,毕竟这里经济发达些,更容易找到一份工作。
我在工厂呆了五年多,五年来的生活,基本是一个月上二十九天班,一天十多个小时,觉得很累,也想休息一下,这种想法也许出于无奈。日子有些灰暗,还不至于绝望。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诗刊的“青春诗会”,东莞何超群老师与方舟大哥为我争取到东莞文化局一个出书扶助项目,能补上一万多块钱,这笔钱差不多是我一年的工资。
2006年,东莞文学院首次对外公开招聘签约项目作家,一个月能补贴三千块钱,签约大约有一到两年,当时东莞不少人都暗示我能签上,我对此抱有希望。也想安心写东西,我没有急于找工作,选择在城中村呆下来,开始了自己的写作,写作诗集《黄麻岭》还有一些散文。
出工厂一个月,我遇到两件事,我一位多年的工友离婚了,她跟我在五金厂一起工作了几年,我们关系相当好,她老公是四川人,她是湖北人。她是工厂品检员,她老公在另一个工厂做技术员,在我看来,她们是很稳定的家庭,他们的婚姻解体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另外一件事,因为感冒,我去东坑医院,在医院遇到以前工厂的一位工友,她去做人流手术,我们聊到一些女工怀孕后,在小诊所做人流手术的事情。
说到有一个工友在小诊所做的人流手术,清了三次宫,才清除干净,估计以后不能生育了。谈到以前有一个工友把小孩生到工厂厕所。这两件事让我想做一个女工们的婚姻与生育方面的小调查。我通过老乡、工友的介绍,认识许多婚姻解体的女工,也了解到一些女工怀孕后人流的故事,这些人流女工都很年轻,十八、九岁,很多是初次出门打工,在工厂认识了一个异地男孩,同居,怀孕,有的怕家里知道或者家里反对,有的因男孩或者女孩离厂,永远地分开,她们只能选择去做人流手术。
在我的调查中,这些在流水线的女工普遍文化程度较低,对生育知识知道得太少,来自农村的她们比较保守,对性的防护措施也相当少,往往很容易怀孕。调查一个月后,我便想写些女工的故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这些女工,我开始有意识选择跟踪一些女工。
有意识去跟老乡,老乡的朋友,租房旁边的邻居交流,通过她们的介绍,我认识了很多女工。我跟以前的工友联系,她们也帮我介绍一些女工。我当时计划花两年时间做这件事,如果能签上东莞文学院的创作项目,每个月有三千块的补贴,至少我不至于担心我的生活了,这样我有更多精力做女工调查,完成一部女工的作品。
2007年,我申报东莞文学院的项目落选了。
从3月份出厂,到七月底知道没有签上,我已经四个月没有上班,而东莞文化局的补贴一万多块钱也差不多用完了,我必须得找工作。于是,我去了樟木头,在那里的一个塑胶厂打工。有关写作女工们的念头就搁起来,我知道我要写,如果东莞文学院的创作项目没有签上,因为生活,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调查女工,我就不急于写这些女工的故事。我当时想写成散文或者故事之类,后来才想到要写成诗歌可能适合。
半年后,我从樟木头辞职,来到常平镇,在一家五金公司做推销员。在我印象中,推销员有大量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这样,我有更多时间去完成女工的调查,还有一些其它计划中的写作。
我有意识租住在混乱的城中村,每天都会碰到抢劫的、卖**的、嫖娼的、做小贩的、补鞋的、收购废品的、做建筑工的、失业的、偷盗的、贩毒的……各种各样的人出没在我的周围,我也出没于他们其中。2007年5月,因为一次偶然,我获了一个奖,然后引起媒体的关注,很多报纸媒体去采访我,我怕我的邻居们知道我的真实情况,我不敢带他们去我租住的地方,如果让邻居们知道,我与她们之间会有隔膜,她们不会告诉我有关于她们生存的真实境况。
跟南都记者见面,我约他们在桥沥的公园里,南周的人采访,成希陪我去长安,去见我的客户与朋友,后来三联周刊的朋友们过来,也是去的长安。我觉得我寄住的城中村才是我的生活全部,我觉得自己要慢下来,写作要慢下来,我放慢了写作长诗《七国记》。
正是跟这些媒体与外界的交流,我知道自己要写一部怎么样的女工了,当它们把聚焦的光线对准我的时候,如果不是我偶然获奖,也许没有人关注我,我会如同我的邻居们一样,默默地生存着,艰难地生存着。
像她们或上进、或堕落,或成功,或失败……我目睹被拐骗的女工如何变成娼妓,目睹一些男工变为吸毒者,沦落为抢劫犯。在租住的桥沥城中村,我经常见到的一名女工被一个吸毒者谋杀了,我只有默默在纸上记下这一切。
我尽力地逃避着媒体关注,我怕我的同事知道,怕我的老板知道,怕我的邻居知道,我拒绝很多媒体的采访,她们想采访我居住的现场,我都拒绝了,我知道自己将要写什么样的东西,我必须深入到邻居的生活中,成为他们一样的人,只有这样她们才会告诉我她们真实的生存状态。
我有一位邻居是卖**女,我说我是业务员,我们经常碰面,她经常带不同的男人回来,我会跟她点头,也仅仅只是点头,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防备着别人,都不想把自己的真实状态告诉别人。
我这位邻居也一样,她心里充满了自卑,虽然她努力地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装着清高不理我的样子,但是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到她的自卑。大约一个月后,我知道她是四川的,我们以老乡相称,她有时会到我房间借一些打工类杂志,比如《佛山文艺》、《打工族》等,我们之间的交流慢慢多起来,她会讲我一些她们的故事,07年过年,她回四川了,然后过来,她告诉我回去相亲了。
我指着楼下那个与她同居的男人问,“那个不是你的男朋友吗?”她苦笑着说,“是的,但我们不会结婚。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卖**者天天跟着的所谓男朋友并不是她们想结婚的对象。只是因为她们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时面对无赖的嫖客,有时遇到抢劫的,有时会遇到敲诈……做她们这行,碰到这些事情,不好报警,所以只有选择跟一个男人,所谓能够保护她们的男人,这些男人就是外界以为的男朋友们。
她介绍我认识了几个她们店里的姐妹,有的是被拐卖的,有的原来在工厂,碰上一些专门进工厂勾搭年轻女工以谈恋爱为陷阱,逼这些年轻女工出来出卖肉体,有的是主动而自愿,有的被老乡从老家带出来专门从事这个行业,有的因为谈恋爱失败,破罐子破摔从事这个行业。
她们完全把我当作她们的朋友,有几次,我去她们的店里,那些嫖娼者把我也当作她们中的一员,我吓得跑了,她们在后面笑。
从这个年轻的卖**者口中,我知道她们这个行业的很多秘密。比如有一对河南夫妻一起出来,妻子卖**,丈夫跟在妻子后面,妻子一直想通过出卖肉体赚点钱开个小士多店,让自己的生活走上正常轨道,但丈夫却喜欢打牌、吸烟,不存钱,他们两夫妻经常吵架,大约半年后,妻子瞒着丈夫存了两万来块钱,再找她的姐妹借了一点钱,他们盘下一个小士多店,让丈夫看管。
妻子继续做一段时间,还上姐妹的债务然后转正行跟丈夫一起开士多店。但没有一个月,丈夫天天打牌,不会经营,还跟一些人染上毒瘾,结果士多店只能关门,妻子生气跑了,没有经济来源的丈夫也离开了,后来我听说丈夫去了湛江贩毒,妻子去了另外的城市继续出卖肉体,有一个小孩在河南乡下。
还有一个广西女孩,她是一个孤儿,从小父母双亡,是姐姐带大的。她一直想努力赚一笔钱,帮穷困的姐姐修房子,于是选择了走这条路,她没有读过书,什么都不懂,因为年轻,光顾的嫖客多。
有些女孩爱惜自己的身体,一般会选择客人,或者控制每天做几桩生意,但这个广西女孩想努力赚钱,不挑选客人,有客人光顾她就接,她没有像别的女孩,用出卖肉体的钱养一个男朋友。
邻居告诉我,因为那个女孩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夏天出汗太多,皮肤溃烂了,**烂了,也舍不得去医院,两三个月后,附近的小流氓知道她存了一笔钱,便敲诈她,结果被人敲了一笔钱。
邻居说起广西女孩的故事,说,“就是不养男朋友,赚的钱还不是给别人用了。自己不要命地做,还不是帮别人做。“她说这些时,露出一副看不起广西女孩的神色,她们在一个店里出卖肉体,平时关系很好,我在旁边听着,什么话都没有说,我本身也无话可说。我只是默默记下这些。
当我与她们接触时,我知道我需要写下这些女工们的故事,那一年,我接触了很多媒体,也知道了媒体如何做这方面的新闻,比如媒体做一个选题,做工伤方面的选题,他们就会选择一个或者两个有关于工伤方面的个体,用个体呈现农民工在工伤方面的境况,他们选择他们需要的对象,以及适合他们需要的部分,而这个女工其他方面被省略掉了。
更多的时候,她们被媒体、报告、新闻等用一个集体的名字代替,用的是“们”字。我是这个“们”中的一员,对此我深有感受。
当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我的时候,我有一种惶恐,我知道媒体在选择报道我时,它们会把我当作一个选题,一个所需要的选题去报道,或者我成为一个脸谱化的代表,比如女工成才的励志对象,我一直拒绝做一个脸谱化的典型,这种脸谱化的生活让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憎恶,很不幸,我依然成为了这一张脸谱。
我知道自己需要努力深入到女工中,把这个“们”换作她,一个有姓名的个体,只有深入到她们中,才会感受到在“们”背后的个体命运和她们的个人经历。
2007年,也正是与她们接触,我对世界充满尖锐的敏感。我尖锐的敏感,过多的愤怒让我无法在最为世俗的业务员生活如鱼得水。但这些女工与她们的生活带给我很多感动,我努力想靠近一些,更靠近一些。
2006年冬天,从樟木头的工厂辞工后,我去了湖南、湖北。跟以前的同事一起回她们的老家,一路上我听到很多有关女性民工的故事,平时同事跟我讲她们的朋友、同学的经历,比如周红与杨红的故事,美丽与卫红的故事。在洞庭湖平原,从益阳到安乡,沿着湖区行走,见到了大遍的芦苇林,开阔的平原。
我在网上找到一些有关那里的历史与风景的资料与照片,同事陪我去看那里的防洪堤,谈论起被改变的树种,被改变的村庄。同事跟我谈起,以前他们村庄有很多种类的树木,比如榆树、槐树、杨树、柳树、椿树、喜树、杉树、苦楝树……同事和她的父亲说了一大堆在他们屋前和河道边种植过的树木品种,她父亲说,“现在这些树种都很难见到了,河道与屋前屋后只剩下速生杨与杉树,杉树是用来造棺木,如果不是要造棺木,估计只会剩下速生杨。
”何尝只是洞庭湖平原,我的故乡,嘉陵江边的村庄,以前河边的桑树、梓树都被砍伐尽了,我们南充是绸都,嘉陵江边,屋前屋后,有过大片的桑树,如今都被砍伐完了,也只剩下速生杨。
同事的父亲叹息村庄树种的变化,同事跟我聊起村庄人心的改变。她说她很多同学到南京、广东等地方从事**行业。十年前,在她们村庄,很多女人出去,从事这个行当,有姑嫂、姐妹搭伴而行,有同学、表姐妹一起南下闯广东,在她们村庄,最先外出的就是村庄里年轻的女性,从事**行业。
她向我描述她们村庄里的一切,那个平原的村庄让我想起《南方周末》曾报道的被鸡头们改变的村庄。在湖北,我陪一个女同事回湖北老家相亲。
十一国庆相亲,农历正月结婚,一年后,小孩出生,小孩半岁后,同事离婚了,从相亲到结婚到离婚,同事一直跟我有联系,离婚后,她去了长三角,彻底在我的视野中消逝了。这些年,我目睹无数我曾经跟踪的女工从老家过来,然后与我相识,又离开了,最后消逝茫茫人海中。
有时候,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特别是节假日的公共场所,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这种在人群中的孤独让我变得敏感起来。
在人群中,我感觉我正在消失,我变成一群人,在拥挤不堪中被巨大的人群压碎,变成一张面孔,一个影子,一个数字的一部分,甚至被拥挤的人群挤成了一个失踪者,在人群中丧失了自己,隐匿了自己。生活何尝不是,我们被数字统计,被公共语言简化,被归类、整理、淘汰、统计、省略、忽视……我觉得自己要从人群中把这些女工掏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一个女儿、母亲、妻子……她们的柴米油盐、喜乐哀伤、悲欢离合……她们是独立的个体,她们有着一个具体名字,来自哪里,做过些什么,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
2008年,因为经济危机,我彻底失业了,六月份,我去了江西、河南、重庆等地,通过朋友介绍,我去了很多村庄,见到很多女工,听她们讲自己的经历、人生、她们工作的城市、她们未来的打算。她们中有曾经打工然后回家不再出来的,有成功在这边开工厂做老板的,有一个在外打工疯了,她疯的原因至今我不知,她老实巴交的父亲也不知。
听到一些客死异乡的女工的故事,被拐卖的女工,有的沦落为偷窃者、娼妓者。还碰到一个在工厂打工数年,回安徽后,跟随老乡一起做假尼姑骗人。
有跟丈夫一起偷盗的女工。有离婚的女工,有婚姻出现大问题却没有离婚的女工……我努力记着她们的故事。当我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我越来越迷茫,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我该用哪种形式来表达我所遇到的女工以及她们的命运,如何在纸上还原她们,用诗歌还是散文,还是纪实类的东西?2008年,我曾试图写有关女工的组诗,我写了两首女工,是其中第一首与最后一首,我发现这种形式并不是我所需要的,于是我把这个题材搁浅下来,等待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去表达。
下半年,我去了广州,在广州一个杂志社培训,是一个有关农民工写作者的,培训后,我被留在广州的杂志。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准备多年的女工题材,我知道我要写这些东西,也许它是我命里注定,我选择每周五坐广深线回东莞,星期一再返回广州,我一直这样在广深线上往返奔波,在东莞与广州,工业区与大城市,流水线与写字楼……之间不断往返,我把房子租在大朗,在常平横江厦或者天虹附近,我接触的女工越来越多。
比如在横江厦,有很多嫁给香港人曾经在工厂打工多年的女工,被包养起来的女工,我倾听着她们的故事,她们讨论着如何申请到香港长期居住,如何申请到香港的廉租房。
这么多年,我学会了倾听,她们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孤独,她们的故事无人倾听,她们积聚了太多东西需要表达。在工业区的市场里,我跟补鞋的、卖包子的、小菜贩们……交流,我租住在她们之中,她们不做生意时,和她们串门交流。
这些城中村的邻居们会跟我说起有关她们自己的和她们熟悉的人的故事,她们的婚姻,她们老乡与朋友的生活,她们被没收的人力三轮车,被砸掉的摊子,被掀翻的水果架。我跟随他们一起去蔬菜批发市场批发蔬菜。
通过网络,我认识了另外一些女工,比如四个都是被父母遗弃,别人抱养大的女工,她们因为共同的不幸的身世而走到一起,她们是重庆人,河南人,陕西人,云南人。她们四个人一起进工厂,一起出厂。她们对自己的身世都有着深深的自卑,那是她们隐形的伤口,她们不肯多说她们的身世,我曾努力想与她们沟通,但我不忍心**她们的伤口,我终就没有完整记下有关于她们的故事,她们便在我的视野中消失了,我还没有完整地了解到她们的情况,我知道我与她们之间,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建立起信任,后来我的一个QQ被盗了,便彻底地与她们失去了联系。
我与她们只见过一次面,半天时间,我没有写下有关她们的故事,后来我接触了与她们类似背景的女工,我找到了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工,写了她的故事,在写她的故事时,我便想起那四个女工,想起被人抱养大的同事。
我那个同事很胆小,老实,跟老乡们一起来这边打工,她的老乡欺负她,她学会忍气吞声。我见到的四个被捡养的女孩子胆子很大,她们是90后的一群,她们四个人抱团取暖,完全不同于我了解的小敏与亚芳她们。直到现在我都懊恼自己没有好好地与她们交流。
2010年,我觉得我应该开始写我整整准备了六年多素材的诗歌了,我把我了解的女工们列表,把以前写在碎纸上的东西整理了下,有很多已经忘记了,剩下些模模糊糊的印象,有很多有着清晰的记忆。五月份,我写了周细灵等二十六首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些人物写下去,也不知道她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是小人物的志传,还是小人物原生态的呈现,我有些惶惑。
我只是努力地告诉自己,我要将这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呈现,她们的名字,她们的故事,在她们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她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与她之间,有着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命运, 她们曾经那么信任地告诉我她们的故事。
“每个人的名字都意味着她的尊严。”这是我在流水线生活中最深的感受,在流水线的时候,我们被简化成四川妹、贵州妹、装边制的、中制的、工号……我在流水线都努力地叫工友的名字,很少用工位或工种、地域叫人,比如插钢通的刘忠芳,旗仔的戴庆荷、陈群,在流水线时,每当人家叫我“装边制的四川妹”,我心里总有些不舒服,我更希望人家叫我的名字,正是有这种感受,我会叫工友的名字,当她们听到我叫她们的名字,她们脸惊愕了一下,转而很兴奋,然后问道“你知道我的名字啊!
”我觉得我跟她们的关系近了很多。我知道我需要写的是她们名字背后的人,而不是她们工位背后的面孔。到六月份,我写了三十几首后,我把这些诗歌给一些朋友看,比如南都报的余远环、刘炜茗等,他们在他们主持的报纸上大力推出这些人物,比如余远环兄长在他的时评版,把这些女工记里的女工以时评的方式发了一个整版,刘炜茗兄在他责编的南都副刊用一个整版刊发了部分诗歌,他短信告诉我,有很多人关注这些诗歌。
我并非想为这些小人物立传,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世界原本是由这些小人物组成,正是这些小人物支撑起整个世界,她们的故事需要关注。
现实中,无论是新闻、报纸、杂志……太多版面都是关注名人以及他们的成功史,我用这些薄弱的诗歌去写一些小人物的故事,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都是农民工,都是女性,我和她们一样,也是女性农民工,我们有着相同的梦,从农村来到城市,面对无法进入的城市,有着相同的苦恼,比如婚姻、工作……我们有着相同的背景和生活。
我只是努力地记下这些女工,当我04年写下田建英的故事时,直到2010年,我都在迷茫中,我不知道如何着手,我能为这些女工写下什么呢?我自己是女工,我能为自己写下什么呢?这些年,有的工友客死异乡,有的跳楼,有的被车撞死,还有一个被狗咬死了,有的在茫茫人海中消逝了,不知死活,也有在异乡改变了命运,她们开工厂,开商铺,做到高级白领……我曾经因为她们的命运流泪,也为成功改变命运的高兴。
当我穿过阴暗而低矮的城中村,当我打开铁皮房的门时,当我看到她们坐在门口、拉线上时,当节假**们一起去公园、街头,当我在车站看到她们背着行李回家时,在医院门口见到她们去做人流手术时,她们失恋时,她们被抢劫时,她们为了讨薪跪在工厂门口时……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有时候,我胆怯,害怕,耻辱,有一段时间,我租住的城中村有很多从事出卖肉体的女工,路过的那些嫖客把我也当作她们中的一员。我曾想到退却,当我经过城中村低矮的巷道被抢劫,当我租住的房间被盗时……我都想过了放弃。
有一段时间,我因诗歌获得虚名,我感觉我跟她们有了距离感,我不自觉地把我跟她们划开,我内心有一种疼痛,我反复地谴责自己,直到有一次,我在一个成功者的办公室见到她对待她下属工友的态度,她的行为让我彻底愤怒了,正是这种愤怒,使我重新找回了自己,我为自己在内心与她们划开感到耻辱。
是的,我一直在诗中说自己,我是一个怯懦者,我胆小怕事,比如租住在东坑一个城中村时,我的房间被撬开,电脑被盗,我吓得搬家了。当我从湖南到四川到湖北到江西等,只是为了倾听她们的故事,去看看她们生活的乡村,这些乡村与我老家没有两样,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去看,是一种态度,还是真的想去了解,我都迷茫过,我究竟要如何写这些女工们,我知道需要努力地记下来,我是一个笨拙的人。
六年里,外界一直在变化着,比如由找工难到招工难的转化,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了一些改变,《劳动合同法》的制定,最低工资的增加,收容制度的废除,是的,看来一切都在改变。但是她们在底层的状态却没有改变,她们依旧用肉体直搏生活,跟她们交流,我无处不感受到压抑之后在他们心里积聚的暴力情绪,这种暴唳的情绪一直折磨着我,而底层与底层的辗轧是那种暴力、血腥、野蛮、**……他们让我担忧,我在一首叫《底层》的诗歌中有过表达“贫穷的生活正摧毁坚固的道德与伦理/马低头啃食着寒霜 苦与涩更添/人间的寒冷 在底层 悲伤/已沦为暴唳 不幸的人用伤口/测量着大地的深度 黝黑的春天/看见底层人群不断地分裂 他们是/麻木的器具者或者血腥的暴力者/我没有找到与世界和解的方式 深深的/担忧从我的心间投到** 我与马的交谈/就像一副衰老的马皮披上寒冷的树枝”我不希望这些女工沦为麻木的器具者,也不愿意他们成为血腥的暴力者,但是现实却不能找到和解这些的方式,我只能深深担忧着在底层积聚的暴力,或者被压抑的暴力会成为一股怎么样的力量,它会将我们这个国家如何扭曲!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家网——作家自己的网站
点击图片上方蓝色字体“作家网”一点就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