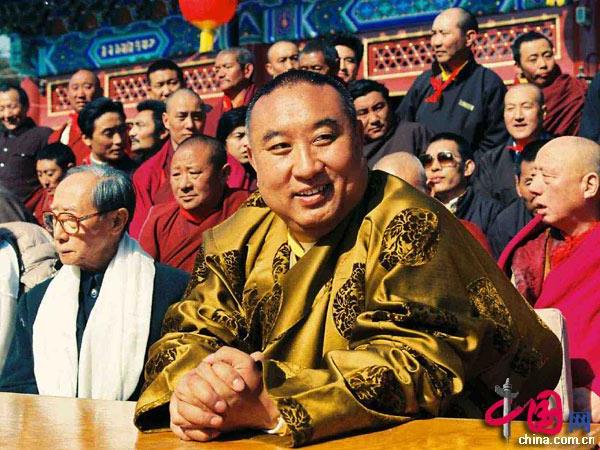余世存家暴 余世存家世非常道读书济世心
《家世》余世存 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11月
我曾经希望自己能像伟大的司马迁那样纪传前贤,他把孔子等人生的失败者、失意者列入“世家”,我们也该平实地写出那些值得“风范”的人家,发“修齐”之光,以使人的身心庶几得到慰安。——余世存
余世存,诗人、学者。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出版有《非常道》、《非常道Ⅱ》、《中国男》、《老子传》、《大民小国》等。
11月,余世存又出《家世》。“梳理百年来的中国家族,挑选我认为值得传述的写成文章。家世本身是教化之源,只要我们听闻,我们就能看见自己的位置和面貌。”
从2005年的《非常道》起,余世存的书就一直是自己定要抓着笔,边做笔记边读的。被其文字激昂滋养多年,对他本人却一直误会想象到底——先惧其“愤青”,后又怕他“沉郁痛楚”。
直到3日下午,在地坛边一间暖气不足的北向大会议室听余世存细说《家世》,才发现他的南方口音、舒展眉宇,还有主动为人算命的好耐心,都温煦如旁边玻璃幕墙反射进来的向晚日光,整个人舒服得像他身上那件灰色毛衣。
在今天中国做个思想者,余世存说“我不痛苦”。“虽然这么多年生活得很曲折,但我个人觉得还是很幸福的。我想既然我从阅读、从历史中能发现安顿我自己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应该也能感动别人,让别人得到安顿。大家在生活匆忙的过程中来不及想、来不及看的那些东西,我可能就像大家所说的‘读书种子’一样,替大家去读了而且去想了,我想,可能我能贡献的也就是这些了。”
如果将来要有孩子,他最希望他成为一个开心的人。“开心本身意味着心灵的开放,而且开心其实是一种创造力。开心并不意味着他不去经历痛苦,而是说他有化解痛苦的能力。”
向晚日光中,余世存娓娓道来——
“我们这些人在送上一代人离开,那我们是不是也该给下一代人留下、传承一些东西”
写《家世》的念头七八年前就有。写完《非常道》之后我跟野夫他们就聊过,当时野夫面临为他的一个长辈安葬的问题。大家都注意到这种家族或者宗亲伦理,在一百年的革命世纪里面被打掉了很多,我们总是把它的负面性看得特别多或者说得太多,是时候关注它一些正面的东西了。
真正开始写是从大理回北京,杂志社约专栏写“君子人格”。正好那年母亲去世,我就在想,我们这些人在送上一代人离开,那我们是不是也该给下一代人留下、传承一些东西。我就跟杂志社商量,君子人格写也可以,但是目前最关键的还是这种家庭教育、这种失教状态太普遍了,能不能写这个?
选择的标准。我原来民国读过很多东西,有些家族本身就在我这儿有印象。这是一类。比如说林同济那个家族,他们的祖先最早认识到在现代文明世界里必须有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很多知识分子,包括我们现在议论朝政时事,都是想当然“拍脑袋”在那儿想,甚至道听途说听点小道消息,他没有分析框架,没有去调查材料。但林家那个时候就有专业精神,我觉得这很了不起。
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我熟悉的人,比如我跟孙家的后人,跟卢作孚的孙子、孙女,跟任家的后人都有一些联系。就像去年我在福州参加弘一法师圆寂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主办方请了弘一法师的两个孙女,看着她们我都特别感慨。弘一法师的两个孙女非常普通,好像是中学老师吧。
丰子恺在上海的后人还是属于文化人,算是我们社会的精英层面,而弘一法师的两个后人算已经跌到贫民阶层,但你还是从她们身上能够看到她们祖父辈的光辉,看到她们身上有那种气质。以前我编《非常道》的时候,看那么多人说卢作孚是个完人,我不相信。结果跟他的孙女一接触,你就发现这个世界上做人和道德上的那种完美,确实是存在的。他真是有一种无私的精神。
再有一个角度就是最后那几篇。选黄家,黄兴这个家族我跟朋友也聊了很多,觉得他这个人在民国史上的位置是被大家低估或者忽略的,他的后人也过得很平淡。但我觉得这个人其实是很了不起、很让人感叹的。
所以也希望把他这种家风家教能够传承给大家,让大家看看有这种活法。
又比如为什么要写蒋家,我是受去年“915游行”的那种刺激,觉得国内很多国民的心灵还是很封闭,缺乏那种世界眼光。其实你看这些传承几代的家族,几乎他们每一代都是极度开放的,一个国民政府的领袖,从他那一代到儿子、孙子,都是中西混血通婚的。反而真正那种穷乏窘迫的人,他们心灵是封闭的。总之我选这些人,还是希望有现实的那种东西能够让人得到一种启迪。
“写《家世》也是希望中国人能够回家、看重家,能够对过去的这种家族有一个了解,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我跟当代一些企业家也打过交道,在他们中间也做过调查。我就问他们“你们跟民国的那些实业家们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有很多人都说:“我们比他们更懂得生活。”这个特别让人纳闷,我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自负。就别说民国那帮纯粹的资产阶级,就那帮企业家,他们的生活是现在这帮人根本不了解、甚至根本不敢过的。就是卢作孚这种有社会情怀的企业家,他们的生活这帮人也完全不懂。我觉得这种隔膜特别可笑。
我认为还是知识不够。这个时代的人他不读书。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戾气这么重,暴力这么严重?中国人到现在为止,没有突破非暴力这个哲学,他去理解曼德拉、甘地是有困难的。他认为在中国的语境只能以暴抗暴。
我们要摆脱自己身上那种戾气、那种暴力,还是要靠知识这个东西。所以你看西方的现代哲学,像波普尔有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要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我们中国人他完全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是希望通过权力获得解放,通过金钱、通过房子来获得解放。事实上他住在那种房子里面,他拥有那么大的权力,他还是一个不自由的状态,他没有得到解放。
《家世》这本书读到后来你就发现,其实真的那种成功或者传承几代的家族,它的共性很多——开放、有敬畏感、读书的习惯,然后懂规矩。这都是一个做人的基本的东西,在现代社会看起来是越来越珍贵。
从五四到现在,我们几代中国人其实都是一种离家出走的状态,都是一个叛逆的状态。基本上都是,每一代人都要反抗他的上一代人。孩子反抗父母,都是一个逆子状态。搞了一百多年,其实我们大家现在心里越来越飘浮不安。而且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当中,也知道西方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一回事。
比如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其实人家那种边界意识,还有它的那种情感的安顿和落实,比我们这边可能做得更好。他们甚至有制度、有信仰层面的保证,我们离家出走之后反而什么都没了。
最近《爸爸去哪儿》、《老有所依》这些大众的文化节目这么火,也都是它提出了这种意识,就觉得要重视这种亲情伦理。所以我说写《家世》也是希望中国人能够回家、看重家,能够对过去的这种家族有一个了解,跟着我能够梳理一下,知道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并不是孤独无依。有那么多人在你周围,你怎么去跟他们相处,然后才能更好地自处。我觉得这是一个出发点吧。
“作为一个知识人、一个思想者,你还是要能先把自己安顿好”
我原来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更多的学者和作家来写一些这种大众作品。不是说把我们的专栏或者散篇的文章集成集子交给读者就够了,而是应该有更多的东西、你更好的思考在里边。
我写专栏从来是跟编辑约好,你即使只要1500字,我给你的时候我也是一万字。我经常是这种格局。我写《大国小民》和《中国男》的时候基本都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我写得很苦,编辑也很苦。后来《环球人物》那个杂志只能给我分上中下。
当年我为什么要跑到大理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觉得《非常道》让我爆得大名,然后很多人就以为我是一个思想家、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对这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发表看法和意见。结果其实你没有那个能力。而且这个社会无论是现实中的问题,还是你自己的那种生命体验的问题都有很多困惑,包括我们面对这个花花世界还有那么多的诱惑,这两大惑对一个中年人来讲是致命的,你必须自己去面对、去解决它。
解决完了你才能有底气或有资格去跟你的读者交流。
我觉得知识分子如果老是做一个苦大仇深或者孤独无人理解的样子,都是有欠缺的,都是存在问题的。你还是应该把这种情绪尽早地管理好、化解掉。孤独和痛苦,这个东西人人都会有。作为一个知识人、一个思想者,你还是要能先把自己安顿好。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当你真的把你的心性打开之后,你就发现世人所说的那种痛苦,包括我自己,比如说我也要为生计苦恼,这种苦恼或者身体的病痛,那个东西它影响不了你的心,进不去的,你的心永远是很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