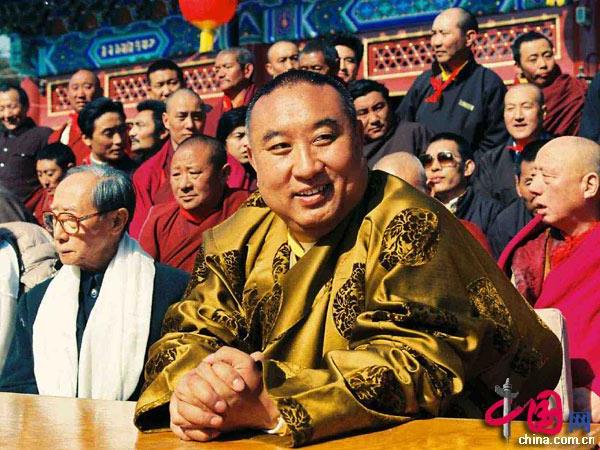余世存非常道 余世存 历史只有走过“非常道” 才能回归常态或常道
余世存:这个序值得向大家推荐一下,把我近年对近代史、中国史、全球化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写出来了。
十年前,我编写《非常道》时根本没有想到开了某种先河,更没想到文明社会的介质很快就转移到移动互联上来。《非常道》问世时遭受过一些人的质疑,幸而它在社会大众那里得到了承认。而网络一旦引入中土,白领、小资、文青、成功人士等社会中间阶层就会日渐获得本阶层的意识,并对通识读物、公共知识产品有日新又新的要求。这也是《非常道》在内的众多历史写作为大众青睐的时代社会原因。
有论者认为《非常道》开创了一个民间价值系统,今天看其价值,远不如网络本身对价值的夯建。十年前《非常道》采花酿蜜,重构了历史;但今天它的一些叙事已经被新出版、新发现的史料校正。历史只有走过非常道路,才能回归其常态或常道。
在这样的时代,人类知识演进正经受挑战,对中国历史的整理总结、对文明世界的解释,仍缺少可观的成果。以《非常道》关涉的历史阶段而言,汉语世界的这一历史叙事仍在意识形态本位、革命本位、故事本位、段子本位等泥潭里挣扎,尚未回归或致意由孔子、司马迁等开创的个人写史传统。
晶报:新版给我另外一个惊喜,是书后增加的“人名索引”。有了它,《非常道》作为文献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索引的想法是怎么来的?
余世存:我当年写专栏时,写到民国某个人物,就在《非常道》的电子版里搜索。当时我就觉得,电子版这个“搜索”功能太方便了,怎么能把它移植到纸质书上?做索引就是一个办法。它不仅仅便利于读者,还便利于写作者、研究者。比如要看蔡元培、鲁迅,通过后面的人名索引就可以把他们的话语或故事找出来,就是一个相当简洁的蔡元培小传、鲁迅小传。再比如你读张学良,通过人名索引可以看到《非常道》收了多少关涉张学良的条目。
晶报:通过这个索引,还能看出你对历史人物的好恶。例如你偏爱的人物,会大量阅读关于他的史料,选取的条目在数量上明显取胜;而你在文化观念上对某些人不认同,就会较少选用他的史料。更进一步,反映出你十年前的思想阶段,在此意义上《非常道》又是个活标本。
余世存:还包括反映了那个时代中文资料中的中国近代史。我马上要出一本《一个人的世界史》,其实就是《非常道2》的修订和补充,增加了近4万字附录还有两张人文地图。给我写序的前意大利驻华使馆文化参赞弗朗西斯科·郗士说,这不仅是看余世存眼中的世界,其实也是看中文文献中的世界。
弗朗西斯科·郗士通读一遍之后,发现《一个人的世界史》里有很多故事,跟他从英语和意大利语种的世界历史里知道的出入很大。他归结为是汉语译本在转述过程中出现的误读。比如拿破仑从来没有说过中国是一头睡着的雄狮,但确实它在一百多年来,已经成为汉语里经典的一个表述。
晶报:“《非常道》里有错”不是一个新鲜的“指控”。这版是否对具体史料有增删?
余世存:当年写这本书本身就是从已有的流传的书里面去摘的,所以很难说每一条都经得上细致的考证。更何况十年时差,肯定还是有史料上的出入和冲突,比如段祺瑞“三一八”惨案之后吃素忏悔,那是后来新发现的史料,但我并没有看到正史去引这段,所以也就没增选进来。
这次我们把原版错误的地方改正过来,新增加了百十条目,跟港版、原版内容各有不同,增加字数约两万(连序言在内)。
我的“新正义论”是常识性的回答
《非常道》用32个关键词,统率了几千条史料。
这32个关键词,不仅仅将散落的史料分门别类,便于归纳;更重要的是,它们还映射了余世存的史观。
尽管不著一字、不注一词,却野心大、用力巧。《非常道》最高明之处,即在于此。
“我编写《非常道》完全是出于对‘话语’的关注。”余世存说,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赶上“启蒙热”和“历史热”,有关党史的资料读了很多,对领袖人物的“个性”话语印象深刻。当时哪里知道今天会盛行微博体,只是摘抄读书笔记时,串连前人言行,他强烈地意识到,这些片断言行本身就有意义,不需要在旁饶舌。
因此,2000年开始编写《非常道》,整理了几千条段子,他最终放弃了自己要站出来表达的冲动,而是选择了由历史细节本身来说话。
为了编写《非常道》做的2000张卡片历经数度搬家散佚,至今还有500多张在身边。遗憾也有,“我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注明出处。比如蔡元培说胡适那句‘旧学邃密,新知深沉’,我就再也找不着了。
晶报:“问世”这一章的隐喻性特别强。这一章的问题,哪一个或哪几个是你现在还没有解答的?
余世存:还是第一个问题。关于华夏文明的猜想,宋恕、夏曾佑讨论时质问:“神州长夜之狱,谁人之过?”现在看来,这还是一个非常重的问题。
晶报:迄今为止,你所做的工作依然在回答这个问题?
余世存:对。我为什么要提“新正义论”的两个原则?只有把“新正义论”拿出来,你才知道这么漫漫“长夜”,每个成年人都应该负有责任。尤其是成年人在这中间的“不义”,才构成了这么一个漫漫“长夜”。所以我的“新正义论”其实是一个回答,一个常识性的回答。
晶报:“人论”这一章中的文化名人,哪一位或哪几位的思想,对你的文化立场影响最大?
余世存:那一代人现在看,很多很不错。无论是梁启超、蒋百里,还是丁文江,他们并没有对自家的文化完全不屑一顾。鲁迅的弱点也在这儿。他过于极端,否定中国字,劝年轻人不要读中国书。这一点跟胡适一样,他们有极端之处。反而我刚才提的这几个人,有贯通中西的见识。
晶报:具体拣选史料的标准有哪些?
余世存:首先是个性,话语的个性。像汪曾祺说:“人总要把自己生命的精华都调动起来,倾力一搏,像干将、莫邪一样,把自己炼进自己的剑里。这,才叫活着。”这条自然要收入“立言”篇。
然后就是“是非善恶那些东西”。上世纪40年代初,闻一多对“天天骂民国、天天要民主、更要官做”的老同学罗隆基正言厉色地指责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有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
足下盖逆取者也。”我们现在很多人还不是一样,比如找一个自由主义的旗帜,聚在它下面“因名成义”或者“因性成义”。史可以“鉴人”,《非常道》里绝大部分历史人物貌似高大上,其实话语、言行方式像个小孩儿。除了民国那些雄杰之外,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候,表现得还是没有担当、没有责任、没有人的尊严。这也是这本书要阐述的。
还有一些入选是出于“要把他们定格”。这种“定格”让读到它们的人体会到,写史确实让人得到了审判。好的我们记住了,这些不怎么样的我们也记住了。虽然名叫《非常道》,但这本书给大家传递的还是有关做人和中国生活一个常态的东西。这里边历史正义的言说,包括对个人生存在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非善恶的追究,这些东西的存在,我认为是《非常道》有价值的地方。
中年余世存对话青年余世存
民国有“南钱(穆)北胡(适)”之称,然而这两位大学者在余世存的《非常道》中出现的频率,可说是云泥之别——涉及钱穆的仅有6条,而胡适则达到60条。
不单如此,在仅有关于钱穆的记述中,有一半都是批评、审视,甚至贬抑。
写史是一种权力。在写作《非常道》的2005年,余世存还是一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他对钱穆、熊十力、马一浮这些为中国传统文化竭力辩护的学人,评价并不高。
就在《非常道》出版两年后,余世存离开繁华都市,隐居大理,在与世隔绝的日子中,他回到原典,回到上古文化,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重新发现了安顿人心的神秘力量,从此他醉心于传统文化的秩序与重建。2010年,《老子传》出版。2014年,《大时间》面世。一步步,余世存从西方走回了东方。
在刚刚出版的“立人三部曲”序言中,余世存又一次写到钱穆。他说,“在钱穆那里,当年西化的鲁迅、胡适骨子里是儒家精神,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传统的儒道互补、内佛外儒,跟人类文化的大小传统统一在个体成员那里是一个道理。”这一次,余世存不仅找到了钱穆,也找到了他自己。
晶报:对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派,你这十年前后的态度迥异。是否可以说,《非常道》映射了你思想深处的一个起点?
余世存:我记得上世纪90年代,钱穆先生的书出版之后,我到舒芜先生家聊天,舒芜先生说起来只摇头,他说,在他那一代受五四和革命党影响的读书人中,无论如何对钱穆的印象都好不起来,钱穆是传统文化中的“村学究”、“冬烘先生”——有点迂腐,有点遗老气,又不被圈子承认。
当年受马克思唯物主义影响的知识界,对钱穆是看不上的。他们很少看得出钱穆有价值,只是尊重他,觉得他很用功,读过很多书,至于学问有多高深,不一定认同。
大前年我见到钱穆的一个弟子,听到一段钱穆晚年对鲁迅的评论,很值得三思:“鲁迅说尽了旧社会的中国,然而他何以如此忧心忡忡?他的目的不是中国的毁灭,而是为求中国的再起。鲁迅全面否定儒教,他不知道他所有的关怀,是一个新儒家的再现,他只是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新儒家。”
对如此反对他的新文化运动的这些人,钱穆能够这么看,我觉得很了不起。更深一层讲,钱穆的见识很厉害。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中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
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儒、释、道、耶、回等等都会成为有效的思想资源,它们如何融合另当别论,但如果融合的外耶内佛表现在一个中国人身上,那绝非“混搭”,而是有意义的立心立命。
我最近在读费孝通的晚年谈话,特别有意思。钱锺书和费孝通晚年的见识,其实非常类似。他们各人的“十六字”,钱锺书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费孝通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意思是一样的。
李慎之曾当面问费孝通:你晚年这个句号怎么画?大家都希望你回到“五四”,回到西南联大时期的费孝通,做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但费孝通的抱负、格局,要远远大于这个。他晚年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不是超越“五四”,而是仍然作为“五四”的精神传人,更好地解决“五四”提的那些问题。
其实费孝通、钱锺书都知道“五四”回不去了,也不应该回去。现在我谈《非常道》,就像是中年的余世存在跟青年的余世存对话。
晶报:从这个角度看你十年的变化,从《非常道》到《大时间》,在文化观念上似乎是南辕北辙。
余世存:也不能这么说。我还是“五四”的传人,我还是在用“五四”精神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只不过在整理过程中,发现了原来“五四”没做出的那些回答。比如胡适曾妖魔化《易经》,而我现在对《易经》非常看重,不能因此说我背叛了“五四”。
在这个意义上,我回到中国传统文化,跟当下流行的“读经热”或提倡儒教救世界,完全不一样。这恰恰也是我做的这份工作既有价值,同时又为大家敬而远之的原因。自由派知识分子觉得我保守了,那些提倡读经或儒教的人,又在我的工作中看出了异端。
晶报:这种两面不讨好的情况,恰恰是把握你的思想很重要的一条红线。你的文化观念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还是强调启蒙的重要性。
余世存:对。“五四”走得太快,没有安顿中国、中国文化,也没有安顿中国人。这个工作是需要后人补上的。
我们太缺房龙、贡布里奇这样的作家
《非常道》十年来的流转,充满了各种“非常道”的故事。
一个中学生在高考前夕读了《非常道》,历史观瞬间坍塌,那种言近旨远的行文方式,让他一学之下拿到奇迹般的作文高分;一位政府文化官员,从《非常道》里读出了《易经》方法论,读出了一个研究“群经之首”的新系统;几乎每一年,余世存都会遇到不止一位热心读者,跟他建议“最近某某人的话可以入《非常道》”。和专家学者的评说比起来,这些故事,才最让余世存心有所慰。
他一直主张,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演进,不是布道,而是提供公共知识产品。所谓的公共知识产品,即是通识性读物。某种意义上,就是畅销书。余世存并不介意被人称作“畅销书作家”,遗憾“像我这样的畅销书作家太少了”。回过头看这十年,余世存不无失望,“知识分子的努力和成绩非常少,能够像《非常道》这样还被大家认可的历史作品,依然太少。”
晶报:十年过去,新发现的史料层出不穷,当日的惊骇或已成为常识,一本“旧书”还有意义吗?
余世存:今天社会的主流读者跟十年前的读者不是一代人了。对我们而言曾经是挑战心智的公共知识产品,对年轻一代人来说不过是常识而已。就像当年沈从文、张爱玲、胡适等人,我们甚至是担着风险去阅读的,而对于今天的读者,他们不过是现代史上的作家而已。
最好的社会是这样的:新一代人的知识或精神起点是在上代人的基础之上。《非常道》如果仍被当做一本新书、大家对它充满惊奇,说明新一代人的某种知识或史观仍是从零起步、重新架构,这当然是一种遗憾。
晶报:那么《非常道》再版的意义是?
余世存:我当年希望这部书能够捍卫历史正义,今天也依然觉得这是它存在并能够传播的意义。《非常道》涉及的史料是近现代史的基础,了解这些有助于看清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我最希望年轻人看这本书,对于他们打破惯有思维、开拓知识结构是有帮助的。与其说,《非常道》可以帮助年轻人形成自己的历史观、世界观,不如说它是在培养一种看世界的眼光和方法。《非常道》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的一本通识性读物。
晶报:通识性读物是汉语写作中一直比较缺乏的,是什么原因?
余世存: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照说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走到一定程度,应该能够支撑社会的知识人去创作更好的作品,能够为这个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知识产品,用美国人的话说,就是提供畅销书作品。
我很多朋友批评中国社会的阅读趣味似乎仍停留在“文青”或“小资”阶段。这种“文青”的阅读跟一个现代公民立身处世的阅读,差异非常大。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社会供养不了这么多通识作家或通识学者的原因。我们太缺房龙、贡布里奇这样的作家。
然而,中国知识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很多是在圈子里面,在一个学术共同体里面,并不在社会,也不面向普通读者。知识人的思考和社会期待之间的距离非常大,相当多的知识人还是用学院的话语说话,即使他们做媒体知识人,生产的仍然是类似读书笔记、学术散论一类的东西,没有整理出一个系统化的思考给大家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他们没有跟大众读者进行有效地交流。
社会的精神演进是我们很少关注的领域,大众的乌合化在某种程度上源于能够参与时代精神演进的产品极度匮乏或受到污染。而要推动时代精神的健康化,需要有效的知识服务,需要优秀的通识作品。
由弟子、学生移位移到“师”
“体制外生存”,是余世存身上一个复杂的标签。
这位北大毕业的高材生,自2000年从《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的位置离职,在体制外已有16年了。他有同龄人中罕见的谋生经历,也因“体制外生存”这一姿态引来知识界的关心或讥讽。
作为思想者,要保持独立性,首先要远离任何“圈子”。余世存清楚知道这一点。这些年,他或在乡野退藏,或在都市大隐,掩不住的,还是一颗入世的心。
是读书支撑了他。“我自觉没有沉沦,没有身心受创,而是从困难泥泞中跋涉出来,身心较为健康地欣见蓝天白云,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读书。”余世存说。他的思想资源可谓杂糅,“鲁迅、我的朋友王康,还有萨特,现象学大师莫里斯·梅洛-庞蒂,再加上庄子、佛陀、《易经》。”
除了读书写书,余世存的生活极为简单——把社交应酬降到最低、微博微信随时断掉,却绝不无趣——他看韩剧,追美剧,甚至向记者推荐最近很火的那部《请回答1988》,余世存从里面看出了中日韩多角互动的东亚大历史,看出了“不需要全盘西化,东方人如何找到自己的现代性”。
晶报:“私人阅读史”是解读一个人的密码,你的思想资源来源于哪些方面?
余世存:从小时候到现在有很多,我们“60后”到“70后”这代人,小时候村里面只有“毛选四卷”可以读,影响体现在我的言路上。我觉得毛泽东是中国文章的一个支流,往前追溯可以追到龚自珍、韩愈、孟子,这是以气势来行文的一路。
鲁迅是我精神上的父亲或兄长。至于他认知上的局限性,主要还在于“五四”这批人没有对中国文化做更深的把握,就要面临接纳西方的问题。无论梁启超,还是胡适、鲁迅,他们对我的影响,更多是人格意义上的。他们的言路、思想本身,对我不再构成一个高标。
艾略特和奥登的诗影响了我的语感。萨特和梅洛-庞蒂是思维的严密性和思辨性。梅洛-庞蒂有一本书《眼与心》,我看了不下10遍。萨特有些重要的论文,有些段落都能背下来。有一阵特别向往他们那种语感,我甚至模仿过萨特的论文写作。
大学时候我的阅读受西化影响很深,包括到现在都拒绝看或很少看中国电影。西方的人本主义对人的尊重比较突出,而在中国的文艺表达中,我们或搞笑或宏大叙事,忽略了个人。直到今天我们社会仍非个人本位,而是官本位、故事本位、物质本位。当然,我的青年时代对中国文化本能排斥,也是受“五四”影响,认为中国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后来一直在调整,到今天为止渐渐走向平和,我既接受东方也接受西方。
晶报:在先秦诸贤里面,你没有提孔孟,而指出受庄子影响深,为什么?
余世存:庄子还是辞章之美,他的文章太漂亮了,当然也感觉他跟佛陀等人很接近。大学毕业看《庄子》内七篇,当时就震惊了,觉得自己这辈子如果能写出一篇,就够了,崇拜得不得了。他的文章里面,语言也有、思辨也有、故事也有,那种天才太突出了。
反而像孔孟就过于“实”,跟青年人的理想气质有些差异。重新认识孟子要到在大理的时候了,读《孟子》才意识到,原来孟子也是很了不起的。老、庄都有一个帮助人在乱世里面立足的作用,先守住自己。
晶报:说到佛陀,我想问问你的信仰。
余世存:我还没有研究《易经》和“时空四象”理论之前,2007年给一个基督徒写过一封信。我当时很明确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每个人都是儒者,但不是儒教徒;每个人都是基督徒,但不一定是基督教徒;每个人都是佛徒,但不一定是佛教徒。
在全球化已经开始的这个时代,如果还是皈依于一个传统的宗教体系,我们的世界就会坍塌很多维度。传统形式宗教的信仰固然可以成为很个人化的一个信仰体系,但是它不足以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国民的信仰。
未来,儒释道有可能全部融合,再一分为二。我们的思想资源如果一分为二,有可能是“儒骨道魂”,也可能是“内释外耶”,外部是以基督教或希腊文明为代表的一个理性的深层体系,内部安顿心灵的可能要靠以佛教为主的那种东西。
晶报: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半隐居?
余世存:这两年对上古史有兴趣,但精力上还没有顾上来,今年年初把专栏停了,只剩下“中国节气”一个。把时间空出来,是因为从今年开始每年都有书要再版,每年都有新出的书,主要是忙着整理这些书稿。
最近我的心态有个大的变化。以前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读书人,一个有着青春心态的人,现在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年人、一个兄长、一个老师。等于由弟子、学生移位移到“师”。我作为一个老师、一个中年人,有什么能给予这个社会,给予年轻人?这是我要交出的答卷。这个转变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