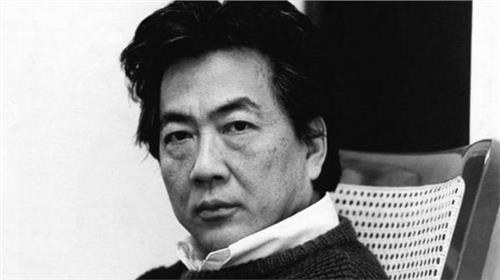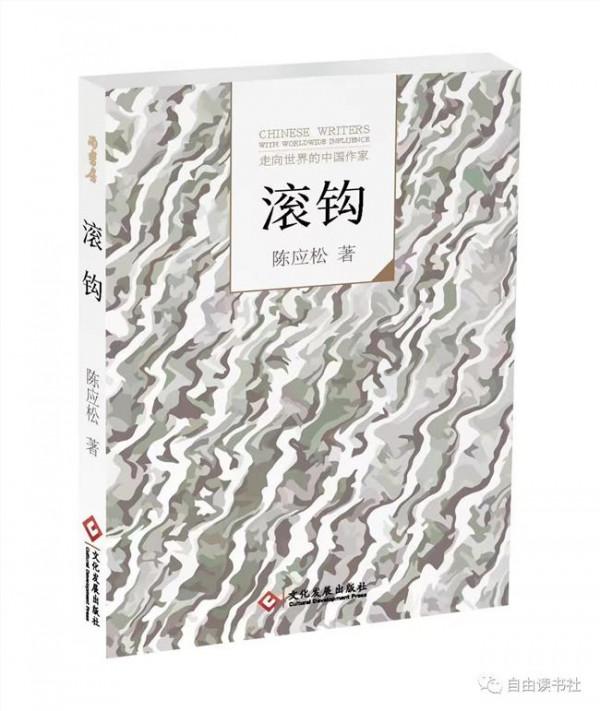陈染原名 知名作家学者对陈染的评价
陌生的陈染 ---王蒙 陈染的作品似乎是我们的文学中的一个变数,它们使我始而惊奇,继而愉悦,再后半信半疑,半是击节,半是陌生,半是赞赏,半是迷惑,乃嗟然叹曰: 陈染,你是谁?我怎么不认识你?我怎么爱读你的作品而又说不出个一二三来?雄辩的,常有理的王某,在你的小说面前,被打发到哪里去了? 单是她的小说的题目就够让人琢磨一阵子的。
《潜性逸事》,《站在无人的风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凡墙都是门》。
这一批题名使你悸然心动:她的笔下显然有另一个世界,然而不是在中国大行其时的“魔幻现实主义”,不是“寻根”,也不是“后现代”或者“新”什么什么。
因为她的作品,那是“潜性”的,是要靠“另一只耳朵”来谛听的“敲击”,是“巫”与“梦”的领地,是“走不出来”的时间段,是亦墙亦门的无墙无门的吊诡。而多年来,我们已经没有那另一只耳朵,没有梦,逃避巫,只知道墙就是墙,门就是门,再说,显性的麻烦已经够我们受的了,又哪儿来的潜性的触觉? 是的,她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和荒谬。
她我行我素,神啦巴卿,干脆利落,飒爽英姿,信口开河,而又不事铺张,她有自己的感觉和制动操纵装置,行于当行,止于所止。
她同时女性得坦诚得让你心跳。她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方式。她的造句与句子后面的意象也是与众不同的: ……看着一条白影像闪电一样立刻朝着与我相悖的方向飘然而去。
……那白影只是一件乳白色的上衣在奔跑……它自己划动着衣袖,掮撑着肩膀,鼓荡着胸背,向前院高台阶那间老女人的房间划动。门缝自动闪开,那乳白色的长衣顺顺当当溜进去。
(《潜性逸事》) 我坚信,梵高的那只独自活着的谛听世界的耳朵正在尾随于我,攥在我的手中。他的另一只耳朵肯定也在追求这只活着的耳朵。我只愿意把我和我手中的这只耳朵葬在这个亲爱的兄弟般的与我骨肉相关、唇齿相依的花园里……我愿意永远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在她的记忆中,她的家回廊长长阔阔,玫瑰色的灯光从一个隐蔽凹陷处幽暗地传递过来,如一束灿然的女人目光。
她滑着雪,走过一片记忆的青草地,前面却是另一片青草地……她不识路……四顾茫然,惊恐无措。(《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想想自己每天的大好时光都泡在看不见摸不着无形无质的哲学思索中,整个人就像一根泡菜,散发着文化的醇香,却失去了原有生命的新鲜,这是多么可笑……(《凡墙都是门》)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琳琅满目。
还有她的小说人物的姓名,黛二,伊堕人,水水,雨若,缪一,墨非……这都是一些什么名字呀?据说有一种理论认为理论的精髓在于给宇宙万物命名。
还有她的稀奇的比喻和暗喻,简直是匪夷所思!这就是独一无二的陈染!她有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语汇,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符号!她没有脱离风俗(这从她的许多冷幽默和俏皮中可以明确地看出,她是我们的同时代人,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生活在我们之中。
)却又特立独行,说起话来针针见血,挺狠,满不论(读吝)。她有一个又清冷,又孤僻,又多情,又高蹈,又细腻,又敏锐,又无奈,又脆弱,又执着,又俏丽,又随意,又自信自足,又并非不准备妥协,堪称是活灵活现的呼风唤雨,洒豆成兵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有着对于爱情(并非限于男女之间)的渴望,有着对于爱情的怀疑;有着对于女性的软弱和被动的嗟叹,又有对于男人的自命不凡与装腔作势的嘲笑;有对于中国对于P城的氛围的点染,有对于澳洲对于英国的异域感受;有母亲与女儿的纠缠——这种纠缠似乎已经被赋予了某种象征的意味;又有精神的落差带来的各种悲喜剧。
她嘲弄却不流于放肆.自怜却不流于自恋,深沉却不流于做作,尖刻却不流于毒火攻心。她的作品里也有一种精神的清高和优越感,但她远远不是那样性急地自我膨胀和用贬低庸众的办法来拔份儿,她决不怕人家看不出她的了不起,她并不为自己的扩张和大获全胜而辛辛苦苦。
她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未必广阔,然而确是很深邃,很有自己的趣味与苦恼的说大就大说小就很小的天地之中罢了。这样她的清高就更具自然和自由本色,更不需要做出什么式样来。
她其实也挺厉害,一点也不在乎病态和异态,甚至用审美的方式渲染之。她一会儿写死一会儿写精神病一会儿写准同性恋之类的。她有一种精神分析的极大癖好,有一种对于独特的与异态事物的兴趣。她的作品里闺房的、病房的、太平间的气味兼而有之,老辣的、青春的与顽童的手段兼而有之。
她的目光穿透人性的深处,她的笔触对于某些可笑可鄙的事情轻轻一击,然后她做一个小小的鬼脸,然后她莞尔一笑,或者一叹气一生病一呻吟一打岔。
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恶作剧吧?然后成就了一种轻松的傲骨,根本不用吆喝。 我当然是孤陋寡闻的,反正我读很多同代青年作家的优秀的作品的时候一会儿想起迦西亚·马尔柯斯,一会儿想起昆德拉,一会儿想起卡夫卡,一会儿想起艾特马托夫,最近还动辄想起张爱玲……而陈染的作品,硬是让我谁也想不起来。
于是内心恐惧而且胆小怕事的我不安地惊呼起来: “陈染,真有你的!” 然后我擦擦眼镜,赶掉梦魔,俨然以长者的规定角色向微笑着走来的陈染说: “祝贺你,你也许会写得更好。
” 戴锦华评论陈染 在她登场之初时,陈染是一个个案。而在“女性写作”多少成了一种时尚、一种可供选择与指认的文化角色的今天,她仍然是一个个案。她始终只是某一个人,经由她个人的心路与身路,经由她绵长而纤柔的作品系列走向我们又远离我们。
以一种并不激烈但执拗的拒绝的姿态,陈染固守着她的“城堡”,一处空荡、迷乱、梦魇萦绕、回声碰撞的城堡,一幢富足且荒芜、密闭且开敞的玻璃屋。
那与其说是一处精神家园,不如说是一处对社会无从认同、无从加入的孤岛。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染并非一位“小说家”—说书人,她并不试图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这当然不是说她缺乏叙事才能,无论是凄清怪诞的《纸片》,哀婉舒曼的《与往事干杯》,诙谐温情的《角色累赘》,还是机智巧妙的《沙漏街卜语》,都证明着她的才能与潜能;她也不是哲学迷或辨析者,然而她又始终在辨析,始终在独白—自我对话与内省间、在意义与语言的迷宫中沉迷,但她所辨析的,只是自己的心之旅,只是她自己的丰富而单薄的际遇、梦想、思索与绝望。
所谓“我从不为心外之事绝望,只有我自己才能把我的精神逼到这种极端孤独与绝望的边缘”。似乎作为某种“断代”的标识,对于六十年代生长的一代人说来,他(她)们在拒绝意义与传统的写作者社会使命的同时,写作成了写作行为目的的动因与支撑物。
而对于陈染,写作不仅缘于某种不能自己的渴求与驱动,而且出自一种无人倾诉的愿望;一种在迷惘困惑中自我确认的方式与途径。
因此,她直觉而清醒的拒斥寓言,在描述一种自我精神状态的同时,规避对某些似无可规避的社会状态的记叙与描摹。她仅仅在讲述自己,仅仅在记叙着自己不轨而迷茫的心路,仅仅是在面世中逃离:凭借写作,逃离都市的喧嚣、杀机,逃离“稠密的人群”这一“软性杀手”。
写作之于她,既是“潜在自杀者的迷失地”,又是活着的重要的(如果不说是惟一的)理由,是写作为她营造着一种“需要围墙的绿屋顶”,一个中心处的边缘。
或许可以说,八十年代中后期,陈染获得机遇是由于一种必然的指认(误识)方式:陈染由于她选题与书写方式的别致,由于其作品的非道德化的取向而获得指认、赞美与质询。于彼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个人、或曰个人化写作意味着一种无言的、对同心圆式社会结构的反抗,意味着一种“现代社会”、“现代化前景”的先声;而非道德化的故事,不仅伸展着个性解放的自由之翼,而且被潜在地指认为对伦理化的主流话语的颠覆,至少是震动。
的确,个人,或曰个人化,是陈染小说序列中一个极为引人瞩目的特征。我们间或可以将陈染的作品,以及围绕着她作品的喧嚣与沉寂,视为某种考察中国社会变迁的标示与度量。然而,这种寓言式解读的先在预期,不仅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陈染小说之为个案的丰富性,同时无疑遮蔽了陈染小说中从一开始便极为浓重的性别写作色彩。
一个个人,但不是一个无性或中性的个人;一个个案,却从一个都市少女的个人体验中伸展出对无语性别群体的及其生存体验的触摸。
王朔的评论 像陈染这样更多写内心是不是算一种新的尝试。当然这也和年龄有关。年纪偏大以后内心越来越丰富,可是外部行为越来越少,不出门了。这时就面临一个怎么书写它的问题……当我在黑暗中摸索的时候,陈染“您老人家”就出来了。
原来我的写作是受海明威影响,认为内心活动通过对话表现就够了,也就是冰山理论那一套。那当然是一种很好的技巧,能迅速跟读者达成默契,可见可感。可是我看了你的小说之后,意识到内心的重要性。
外部东西看似千差万别,其实你仔细检索描写当代生活的那些小说,差不多都是一种模式的。比方新新人类写的就是酒吧,甭管酒吧里发生什么事,感受不一样,但它的生活模式是非常容易相似的,所谓的不同就是指的内心感悟。
关于外部描写现在有纪录片、电视电影表现得更直接。那文字应该达到镜头达不到的地方--就是内心。也就是说文学再往前走,恐怕陈染你那个方向就代表了文字的未来。 中国文学不太关注内心,而是关注人在人群中的位置、冲突。
其实陈染你写的就是个人的战争,小说里最大的感觉就是,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这种可能女性作家发现得更早。因为男性面对和关注的往往是社会性的冲突。 雷达(中国作协创研室评论家): 我非常看重陈染的创作,从90年代陈染就非常引人注目,成为个人化写作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
陈染的创作特点是返回自身,回到个人私有话语的空间,而这个特点恰恰是商品社会、开放的社会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内心的一种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种创作与社会发生了隔离,仅仅是小我的体验,它的社会内涵其实是很深的。
所以陈染在青年人和知识分子中间会引起共鸣,获得自己固定的读者群。我觉得,如果陈染的视野再大一点,再丰富一点,将会有更大的成就。
方方(作家): 陈染才华横溢给人很深的印象,她天生就是作家的料,除了文本的异质性以外,她有一套完全自我化的哲思,她的作品有很女性的感觉,同时又有很深刻的一面,这就使她超越了一般意义上女性作品。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当代女作家中陈染的独特性已经相当确立,构成重要的一面景观。读了这部小说以后非常受触动,因为它不仅讲述了一个女性个人成长的历史,还涉及到一些精典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回忆。
个人成长的记忆,并不是女性个人的体验,还有着相当的公共性,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都非常接近,是社会主义向市场社会转变过程中一个中国的个人的经历。 我非常关注<<私人生活>>结尾处陈染提出的困惑,就是“私人”的植物能否移植到公共的花坛中,能否到公共社群里,是出去经风雨见世面还是在安全的阳台上生长,这是个重要的矛盾,也是个很大的挑战,植物有权长在家里,但也可以、也许更需要长在花坛里,这个问题陈染在未来的写作中可以给我们一个好的回答。
刘震云(作家)话陈染: 我有三点想法:1 陈染是非常优秀的作家,她对文学和生活的思考,她处理个人情感、个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那种方式,国内作家在她以前没有过;2 陈染对汉语写作从文体和观察的角度上显然有开创性意义,其作品在细部把握上有十分独特的价值;3 小说的名字、人物的名字非常奇异,独特而有想象力,我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