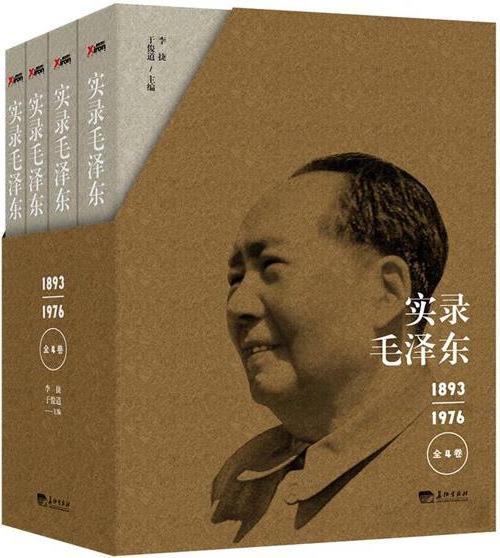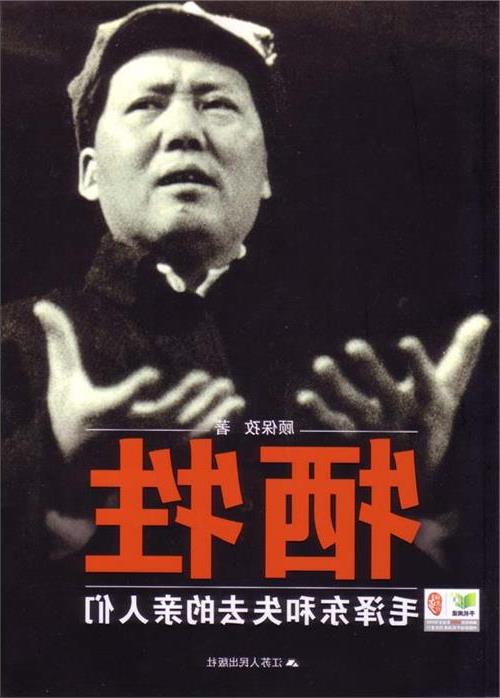金维映儿子 我目睹了贺子珍、金维映在苏联学习时的不幸经历
作为当年一起在苏联学习的党校学员,林利目睹了贺子珍、金维映在苏联的不幸经历,感慨万端。下文摘自由林利撰写的《往事琐记》,该书将于近期出版。
和我们一同学习的还有贺子珍同志。她比我们早一些到达莫斯科,之后不久生下一男孩。在八部 时,孩子放在托儿所,她一边学习,一边课间喂奶。可惜孩子先天不足,出生后只是一般喂养,终至夭折。贺子珍忍受着痛苦,照样坚持学习。
她在长征中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受伤,背上留有不少弹片,在苏联治疗也未能取出,她长期患头疼之症也是医疗无效。但她学习特别认真,我们一起课堂讨论时,她常和学员们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和我辩论,我年幼气盛,不肯退让,她也指着我大声争辩,但是后来待我依然如旧,仍把我当晚辈。
她性情直率、刚强,这几乎是长征过来的女同志的共性。本来也是,如果不刚强,如何经得起那许多日日夜夜的磨难 贺子珍忍辱负重的坚毅性格也是令我佩服的。
关于她婚变的情况我们是在一个十分偶然的情况下知道的。那是1939年的一天晚上,大家坐在俱乐部大厅听翻译读塔斯社记者在延安采访毛主席的报道,其中这样写道:夜深了,我们告辞,毛泽东和她的妻子送出来,在月光照耀的山坡上,我们边走边谈……。
听到这里,我们不禁大为震惊 全场,包括贺子珍在内,都没有料到这种情况,大家久久沉默着,贺也不作声。她非常镇定,直到读完报,大家散去,她也没有眼泪,没有悲诉。过了一段时间,她才向其他红军中的女同志略略说了一些她的家庭生活。从他人的转述中,我只听说她在离延安之前一段日子里,由于误会,她和毛泽东两人之间有过争吵,但没有料到毛会与她根本分手。
在这个问题上,贺子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她默默咽下了苦水。后来恩来同志来时给她带来了一箱书、一封信。又过了若干时日,给她送来了她惟一的女儿娇娇。苏联卫国战争时,她和娇娇 即李敏 都住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
由于语言不通,院方领导完全不了解她,加上她作风泼辣,性格刚直,说话急躁,有时不顾对方反应如何就大声争执,后来竟被院方视为有精神病,被送进精神病院。这些情况发生在战时,原来在七部的同志除我之外,均已离开莫斯科。我和维世对伊凡诺沃的事一点也不知道,直至1946年罗荣桓、王稼祥来莫斯科养病,才了解了一些情况。她大约于1947年回到哈尔滨,以后到了上海定居。
七部的女同志中,结局最惨的是金维映。她是和我们一同从西安到迪化,接着又到莫斯科的。我听说她在中央苏区时就担负过重要的工作,长征中路过少数民族地区时,为了做统战工作,她和一位女酋长喝血酒,拜把子。我又听说,茅盾的《子夜》中写过一位党的女地下工作者阿金,就是以她为原型。
此事我问过她,她认可,但说小说中对党的地下工作描述得不尽真实。她还告诉我她出身很苦,小时裹过脚,很早就被迫嫁人,因为不堪受苦,还出家为尼,最后走上革命道路。她在八部时是党组织的总干事 相当于支部书记 ,身体很不好,但学习很认真。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很想念留在延安的孩子。
搬到七部后,她逐渐地变得郁郁寡欢。有一次在俱乐部听读报时,我恰巧坐在她旁边,只听她自言自语地说:“哼,看不起我。”我很诧异,问她:“谁看不起你 ”她未答复,当时也就过去了。谁知过了一些时候,她竟终夜不眠,而且抱着与她同屋居住的蔡畅大哭,蔡畅不禁陪她落泪。
由于无法休息,蔡只得搬到另一间屋子。后来,金维映的病情一天天恶化,直至精神崩溃。这期间组织上安排她去医院检查诊治,但都无效。后来发展到白天睡觉,夜里从屋子出来在楼上楼下走个不停。
当时院子里有一只巡夜的狼犬,会咬人,为了不致伤害她,同志们特意把狗拴住了,她却走到狗舍边,用滑雪杆去撩逗那只狼犬。学员们都很担忧,夜里也都不能入睡。经过多次检查,组织上终于决定送她入精神病院治疗。
入院后,我们学校的学员轮流去探视她。有一次,蔡干妈和我去探视,只见她身穿一件灰色呢质外套,头发被剃光了,她和我们很和蔼地谈话。以后医院传话过来,说两位名罗莎和莉莉的同志去看过后,她的情绪稳定,要这两位同志多去。
1940年蔡干妈要回国,就叮嘱我多去探视金维映。当时只有我和孙维世住在莫斯科,我们两人就定期去看她。这所医院位于索科尔尼克公园的旁边,在当时算是莫斯科的郊区,现在则是市中心了。后来我们的印象,感到她和我们谈话完全正常,但当时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全走了,我们不知找谁反映。
不久后,苏德战争发生的初期,我和维世再去看她,医院竟已撤走,我们急忙向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苏联同志反映,他们却已无暇顾及。
1941年,我和孙维世也被疏散至乌拉尔山下的乌发城,1942年随共产国际机关返回莫斯科后,我们又去找她,但她的医院没有搬回,我们也投诉无门,没有人管外国人的事。可惜 这位曾为党做过不少工作的女同志就此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