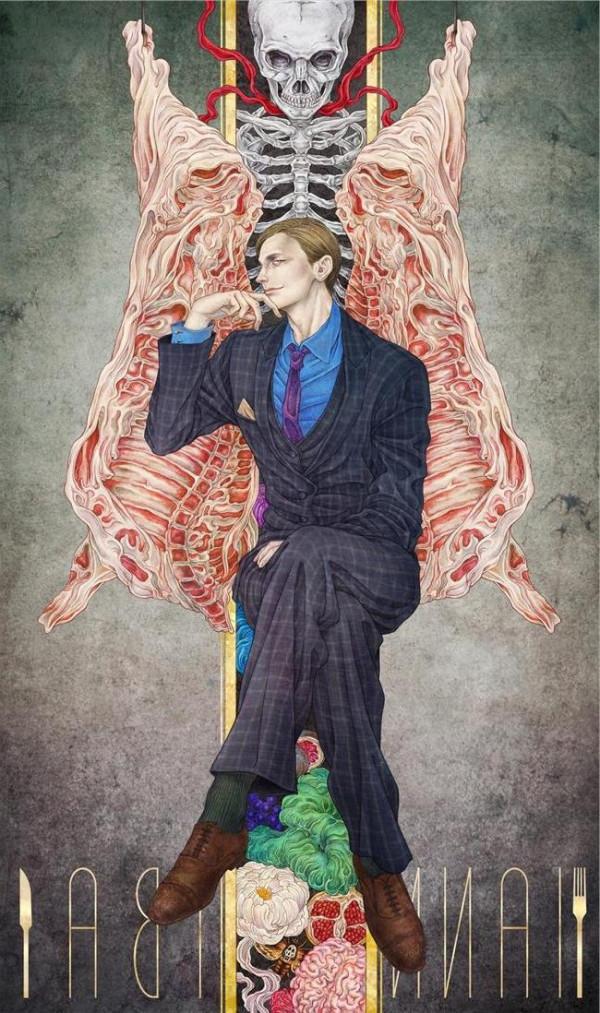史义军:都是极左惹的祸——读《周扬与冯雪峰》有感
近读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扬与冯雪峰》(作者徐庆全)一书,感慨颇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扬和冯雪峰无疑是两位具有重大影响而又十分复杂的著名人物。他们在社会变革中崛起,成为文坛令人瞩目的弄潮儿和光辉的前躯;又在建国后相继被拉上政治祭坛,扮演了可悲而又可惜的角色。这种角色转换,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启人深思,正因为周扬和冯雪峰是这样两位著名而复杂、特殊的人物,我一直对他们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搜集了一些资料,想对他们加以系统的研究。
遗憾的是,别的事总忙不完,这方面的研究至今没有来的急做。但高兴的是,读了徐庆全同志所著的《周扬与冯雪峰》后,又勾起了我对两位文坛先驱和那一段历史的兴趣。
徐庆全是我熟悉的朋友。这本《周扬与冯雪峰》,是他近年潜心研究的成果。与已有的关于周扬和冯雪峰的著作相比,本书以周扬和冯雪峰的矛盾纠葛和身世浮沉为主线,对周扬、冯雪峰、鲁迅、胡风及“左翼”文学运动中的主要人物的重要思想、活动、作了比较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勾勒了他们人生发展的轨迹。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对有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对一些争论较多、分歧较大的问题的分析,不乏新意,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作者也是下了功夫的。
从文字来看,也是简洁而清晰的。尽管书中有些地方还可以推敲,有些分析还有待于深化,有些提法还值得商榷,但从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关于周扬和冯雪峰生平思想研究的可喜的新成果,是一本既有学术性又有一定可读性的好书。作为一名我的同龄人,对于这样一个复杂而困难的课题能作出这样的把握,写出这样的水平,很不容易。
关于周扬和冯雪峰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我觉得还很不够。周扬与冯雪峰,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坛上是两颗灿烂的明星,但现在关于他们的研究,特别是对冯雪峰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说到周扬和冯雪峰不能不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左翼”文学运动,不能不提到五十年代的批胡风、反右,不能不提到那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更不能不提到置身于历次运动中的那些历史人物,这一切书中都较为详细地涉及到了,而且有些资料还是第一次披露,可以说弥足珍贵。
读完此书,我有两点感想,一是尽管作者把当事人放到了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但对左的思想根源解释得还不充分;二是对当时的左翼作家内部的“宗派”情绪反应不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本书中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生离死别的悲剧都是极左惹的祸,不把这一切归到极左思潮上就无法解释那一幕幕的人间惨剧。
当时文坛的极“左”思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片面强调文学艺术与文艺活动的政治功能,忽视了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二是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
“左联”本来是一个文艺组织,但在当时却成了一个政治团体。“左联”行政上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执委会。第一任执行会由鲁迅、郑伯奇、洪灵菲、田汉、冯乃超、夏衍、钱杏邨等7人组成。在党的组织领导方面,“左联”内设有党团,直接受文委领导。文委领导“左联”,主要通过“左联”执委会内的党组织,设一名党团书记。“左联”的第一任党团书记是潘汉年。
周扬在晚年的回忆中说得更为直接:“当年的‘左联’成了第二党。为什么叫第二党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跟党一样的。它本来是个作家团体,可以更广泛一些,更公开一些,更多谈文学,但是后来,却专门谈政治。”(注:《周扬笑谈历史功过》,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2期。
)当时的“左联”领导人,实际上也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在文艺上,而是热衷于组织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鼓动工人罢工等各种激进的政治活动。
相反,谁要是热心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就被说成是“作品主义”,谁要是热心想做作家,就被说成是“作家主义”,就会被视为“右倾”。(注:《胡风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有的作家本人,也特别看重作为作家的政治个性。
殷夫在论述文化工作与实际工作的关系时曾指出:“做文化运动的人,也即是参加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的人”,并这样讥讽过那些不愿直接参加政治活动的作家:“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畏惧实际斗争,怕做艰苦的工作,便自动地投到文化运动的旗帜下去呐喊几声,自以为是既安全又革命的妙计。
”(注:郑择魁等:《左联五烈士评传》,第405页。)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一些作家,表现得更为激进,他们主张,要把文学作为宣传革命的留声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他们声称“我们要战胜一切,我们要征服一切”,要掀起文学领域的新的革命,要是“五四”文学传统来一个彻底的脱胎换骨,要把文学从“为艺术而艺术”的象牙之塔中解放出来,投入到社会革命的时代大合唱中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求文学发挥政治作用,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完全不顾文学自身的特点,甚至将文学与政治等同视之,这又势必会影响文学自身的发展,甚至使一些作家陷入困惑。
正是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有不少作家遭到了不应有的非议乃至批判。蒋光慈因《丽莎的哀怨》中流露了悲愤与消沉情绪,不仅遭到严厉批判,甚至被开除出“左联”。阳翰生在回忆录中谈及:“在这时期,我觉得有两件事做的有偏差,一件是因为郁达夫对徐志摩说‘我是个作家,不是个战士’,便把郁达夫除名,而我当时是主席,至今觉得负疚。
还有一件,茅盾告假半年,专心写《子夜》,大家曾开会攻击他。”(注:《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4期第7页。))鲁迅也多次遭到攻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与敌人“调和”,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是“渗有毒汁”的“花边文学”。
《周扬与冯雪峰》也提到了来自苏联文艺界的“拉普”和日本文艺界的“纳普”等极“左”思潮的影响。正是与其影响有关,左翼文艺界一直存在着过分强调文艺作品的政治功利目的倾向,而无暇顾及艺术本身的探索。
遗憾的是,这种极“左”思潮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警惕。此后,在中国文艺界不时出现的许多争论中,往往都可以看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尤其是在建国之后,这种思潮竟愈演愈烈,批胡风,反右,一直发展到“文革”这般不可收拾的程度。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仅就文艺界而言,一次次的极“左”思潮,不能不说与“左联”时期形成的“左”的心理定势有着某种潜在的关联。
正是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关,在当时“左联”一些政治活动中,冒险主义曾一度极为盛行。这种冒险主义,不仅使一些作家内心衍生了对革命的疑虑,更为严重的是,直接导致了革命力量的无谓牺牲。据夏衍回忆:“一次在南京路飞行集会,闸北区委负责人布置了一二百人‘占领’山东路附近的一个‘慈善’机关,结果二十多人被捕”。
(注: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9——180页)夏衍在回忆录中还谈到:那次南京路飞行集会活动中,他侥幸脱险后,在外滩碰到了李求实,“他就很气愤地对我说‘这样就等于把同志们主动送到巡捕房’,我听了很有同感,但是连‘我同意’这句话也不敢说。
又如,有一次我所在的小组,晚上到三角地小菜场附近去写‘武装保卫苏联’之类的标语,当时下雨路滑,同组的孔德沚(茅盾的夫人)不小心滑倒,弄得满身泥水,我们把她送回家去的时候,她发牢骚说‘连自己也保卫不住,还说什么保卫苏联’,我们还批评了她。
我们这些人不都是知识分子吗?为什么会这样傻?一方面说当时组织纪律很严,而党内又缺乏民主生活,当时我们最怕被说成‘右倾’,像陈独秀这样的大人物,不也因为右倾而被开除出党了么?” (注:夏衍:《懒寻旧梦录》,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9——180页)可见,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即使像夏衍这样坚贞的共产党人,对当时的“盲动主义”、“冒险主义”,也不是没有看法,只是由于担心受到指责,不敢表露而已。
当时,在左翼作家内部,宗派情绪也是十分严重的,突出表现在鲁迅、冯雪峰、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冲突。“左联”成立之初,鲁迅、冯雪峰、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关系原是密切的。胡风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之后,周扬曾亲自登门看望;鲁迅第一次见到胡风,也是周扬陪同前往的;胡风出任“左联”宣传部长,也是周扬提议的。
有一段时间,按照约定,胡风常和周扬一起,到一家饭馆里边吃饭边向鲁迅汇报工作、征求意见,饭费每次都是由鲁迅抢着掏腰包。
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鲁迅与周扬,冯雪峰与周扬,胡风与周扬之间的关系竟越来越僵,甚至发展到恶言相向、相互敌对的程度。“左联”成立不久,鲁迅即流露出对周扬的不信任态度,最后,竟发展到公开以讥讽的口吻称周扬等人为“四条汉子”。
周扬也以不同的方式,多次表示出对鲁迅的不满。胡风与周扬之间的公开冲突,则是围绕“典型问题”的论争开始的。这本来是一次学术论争,但因双方早已存在芥蒂,竟逐渐发展为政治性的互相攻击:周扬指责胡风破坏“左联”团结,在搞宗派活动,跟南京国民党有关系;胡风则反过来控告周扬用党的权力压他,甚至用“转向”分子穆木天的挑拨诬陷来整他。
1936年,“左联”解散前后,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冯雪峰、胡风与周扬等人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
为了平息这场争论,达到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目的,茅盾与冯雪峰商量,请鲁迅先生出面,再写一篇文章,正面表示他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的意见,同时也不排斥“国防文学”的口号。
鲁迅同意了,于是在病中口授、由冯雪峰笔录完成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文章。在文章中,鲁迅从大局出发,按茅盾、冯雪峰的正确意见,以诚恳的态度,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如何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角度,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进行了明确解释。
文章发表后,为了扩大影响,茅盾按冯雪峰的提议,又把文章送到了周扬主持的《文学界》月刊,希望再一次刊发。
但出乎茅盾意料的是,编者竟造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另一篇《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虽然登了,却不仅故意排在后面,且加了一个800字的附记,表示不赞成鲁迅肯定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仍在强调“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正统地位。
由此可见双方分歧的严重,正如茅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深有感触地说过的:“从这里,我直觉地感到了宗派主义的顽固。”(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0页。)
当时左翼文坛上的这种宗派情绪,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与这些作家当时的人格特征与心理状态有关。当时的周扬,尚是一个年轻的书生,1932年重新入党后,担任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兼任文化总同盟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那时还不到25岁,显然还缺乏丰富的社会经验。
加上当时的激进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使他对鲁迅这样的文坛宿将,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尊重。周扬后来说过,“左联”成立后,有些党的文艺工作者并没有从思想上认识鲁迅的伟大。
不知周扬是否意识到,这些“党的文艺工作者”自然包括他本人。从《周扬与冯雪峰》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年轻气盛的周扬对鲁迅有过的误解,也不难看出鲁迅当时的病态情绪,恰恰又处在一种不太冷静的时期。
脾气越来越大,疑心也越来越重,甚至对于身边的许多朋友,也时常流露不满。孙伏园本是他看重的学生兼朋友,《莽原》是他支持的刊物,但1926年11月7日是,他在致许广平的信中说:“即如伏园所办的副刊,我一定就也是被用的器具之一。
”认为莽原社的人,对于他也“大抵是可以使役时便竭力攻击”。(《两地书》)他与林语堂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1934年,在一封信中,他曾建议林语堂不要再提倡幽默、性灵、小品文之类玩艺儿,希望能翻译一些英国文学名著。
林语堂回信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因鲁迅长林14岁,鲁迅便认为林是讽刺他老了,所以才注重翻译。从此,在鲁迅眼里,林语堂就不再是“朋友”了。
有一次,他们同在曹聚仁家作客,闲谈时,林谈起他在香港时的一件旧事:几个广东人在滔滔不绝地谈论时,林插上去同他们讲英语,把他们吓住了。鲁迅闻此,竟勃然动怒,站起来责问林:“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瞠目结舌,不知说什么是好。可见鲁迅当时过于敏感的心态。这样一种心态,当然更难容忍本来就关系紧张的周扬等人对他的责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