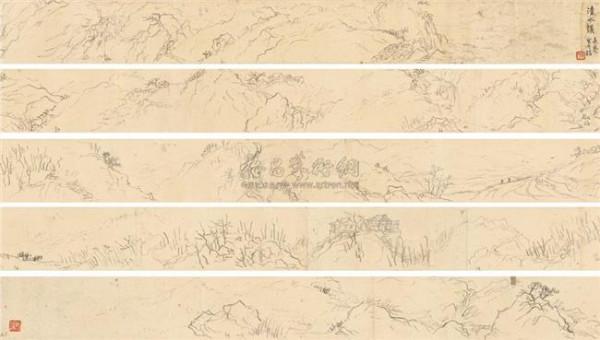我的祖父刘文辉 刘元彦:我的父亲军阀刘文辉
作为川系军阀的代表,刘文辉曾经历了军事的起起落落和政治的波谲云诡,他的人生历程,正是历史的某种见证。
长子刘元彦出生时,正值刘文辉军事生涯的顶峰。如今年近八旬的刘元彦在北京一座普通的居民楼里过着他安静的晚年。刘元彦退休前任人民出版社编辑,说话间眉眼总带着笑,很难想象这是一位出生在军阀之家、当年曾有优裕生活的“大少爷”。
这期间张群多次约谈,试探父亲的态度。起初几次,张群的口气还比较客气,父亲也跟他真真假假应付一番,见父亲一直不明确表态,张群的口气一次比一次强硬。12月5日晚,父亲约请张群和国民党主要将领在家里吃饭、开会。席间唇枪舌剑,最后,父亲说:“我是大军阀、大资本家,共产党哪会要我,如果共产党的部队打到西康,我一定同共产党拼,拼不过,我就到西藏当喇嘛。”
1949年12月6日晚上,张群最后一次来我们家。他说自己马上到云南去,又以好朋友口气嘱咐父亲“好好干”。父亲担心张群一走,胡宗南、王陵基他们当晚就会动手,他让我连夜开车把母亲和妹妹送到认识多年的一位老中医家里,把我爱人和孩子送到岳母家。我和父亲则躲到他一位部下的儿子家住。当时四周都是特务,气氛特别紧张。
12月7日一早,父亲说先回家去一趟,让我在那儿等着他,哪知等了很久不见父亲回来,却突然来了一人,说父亲已经出城,让我到南门外乡下他一个部下的家里等。我只好奉命立即出南门,心里十分懊丧,因为原来说好同父亲一起的。我后来体会父亲这样安排的用意,是防止失利时我和他同时牺牲掉。
原来父亲那一天回家与邓锡侯谈话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通知,要求他下午到军校去,父亲向有关的人打探了一圈,得知只有他和邓锡侯接到这个命令;而且得到消息说,原来负责城防的川军当晚也全部被胡宗南的部队替换,父亲和邓锡侯感觉苗头不对,他们当即决定马上行动。
为了不惊动宪兵和特务,父亲没带任何行李,只有两个随从跟他一道坐车出了门,在离城门洞一段距离后父亲先下车,而将空车开出去,在城门外一隐蔽处等他,万一被哨兵盘查,就说是去机场接客人;父亲自己则从城墙的缺口爬了出去。这时他正患气管炎,当时气喘吁吁,汗流浃背。由两个随从扶着,五步一停,十步一歇的,终于到了城外,邓锡侯已在外面接应。
1949年12月9日,父亲与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彭县宣布起义。得知消息后,蒋介石带着蒋经国,马上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
父亲的24军在成都武侯祠附近有一个营的驻军,消息一公布,胡宗南的部队马上打了进去,大部分官兵牺牲。胡的部队还用炮轰开成都新玉沙街我们的家,密集的枪炮声响了一晚。他们不但将家里洗劫一空,还在撤走前,在住宅里秘密埋下大量炸药和雷管,企图等我们胜利归来后,把全家炸死。
在我们还没回成都之前,有一些想趁机发财的人闯进去,结果引爆了那些雷管,家里的三幢房子被炸了两幢,只剩下我住的那一幢。余下的雷管和炸药还是后来解放军工兵帮助取出来的,一共100多公斤。
父亲的24军在雅安和四川交界处还有一些驻军,起义消息一宣布后,国民党部队马上攻打这部分军队。地下党同志利用电台跟“二野”联系上了,“二野”很快从另外一条路出兵,打垮了国民党的进攻部队,解救了这部分24军战士。刘、邓、潘起义消息宣布后,一些部队相继跟着起义,虽然24军本身兵力不多,但更大的影响还在于政治上的。
最后岁月
解放后,父亲先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59年,父亲调到北京,任林业部部长。这段时间,除了上班和开会外,他还经常去外地视察林业。在家里,他经常读一些林业方面的书籍。
上世纪60年代,刘文彩的“地主庄园”扩大宣传,此事统战部曾经跟父亲先打过招呼。那段时间,“刘文彩”的名声盖过了父亲。但父亲在我们面前只字不提此事,我们也无法窥探到他内心真实的感受是什么[1]。
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就把自己的房产全部上交国家,一直住在公家分配的房子里。到了北京后,国务院分配住在史家胡同,也就是荣毅仁家现在的那座四合院。1966年的一天,门口突然贴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刘文彩的弟弟还住这种房子!
”很快引来了红卫兵抄家,起初第一批红卫兵走后,我们还把散落的东西收起来,谁想到第一批刚走,第二批又来,后来我们干脆也不收拾了,就等着他们来翻。短短几天之内我们被抄了13次,贵重的东西都被抄走,红卫兵还不断向父亲提问题,父亲的心脏病都犯了。
很快周总理派了人来,把父亲送到了301医院,用化名住进去的。当时跟我们家人都没提及他们的真实身份,只是说送进医院,让家里人放心。来的人也是打扮成红卫兵的样子,把家里的柜子都封了,因为柜子里还装了很多文件,这样一来,后来的红卫兵也不会再抄了。
1966年国庆节,父亲和一批民主人士一起,被邀请去天安门。父亲在医院穿上我们从家里送的衣服后直接上的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城楼上,身穿军装的毛泽东见父亲的装束,还说:“你怎么还穿呢子服?要跟我们一样嘛!”父亲后来做了一身布的中山装。父亲是直接从天安门回的家,因为和毛主席一道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样一来身份就不一样了,红卫兵再也不敢上门抄家。
“文革”开始后,父亲的身份是政协常委兼人大常委,林业部部长一职好像也无人提及,但也没有明令撤掉。父亲跟政治打了一辈子交道,平时言语很谨慎,也很少流露他内心的想法。他只是几次叹息着说:“铁打的江山,就这样砸烂了!”
父亲对周恩来总理的感情很深,一直把他视为良师益友。1972年一次见到总理,他对总理说:“郭子仪当了24年宰相,希望总理能超过他。”总理当然明白父亲在说什么,但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哈哈大笑,以后父亲也很少见到总理。
1972年,父亲不小心摔断了腿,他原来就有心脏病、肺气肿,1975年又被发现患了癌症,身体更加衰弱。周总理对父亲的病情非常关心,几次亲自批示:尽一切办法延长生命,只要有危险就随时向他报告。我们后来才知道,周总理下令保护父亲的时候,他自己其实已身患重病了。
1976年1月初,刚出院的父亲得知总理去世的消息,极为伤心,不顾医生不许外出的禁令,他坚持要去向遗体告别,最终还是我们用小车推着他与总理遗体挥泪告别。
不久,父亲再次住进医院,6月去世。“文革”以后,父亲一直较为沉默,总理去世后的几个月,他的心情更是沉重。我们感觉到这一点却无法帮他排解。父亲走后几个月,“四人帮”被粉碎,我暗暗地想:如果父亲能多活些时间,就能放心地辞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