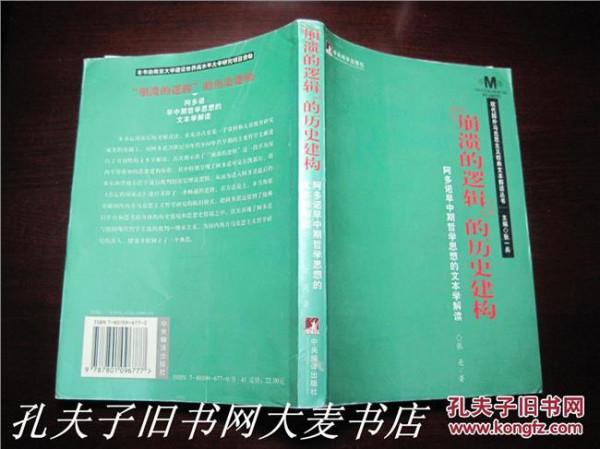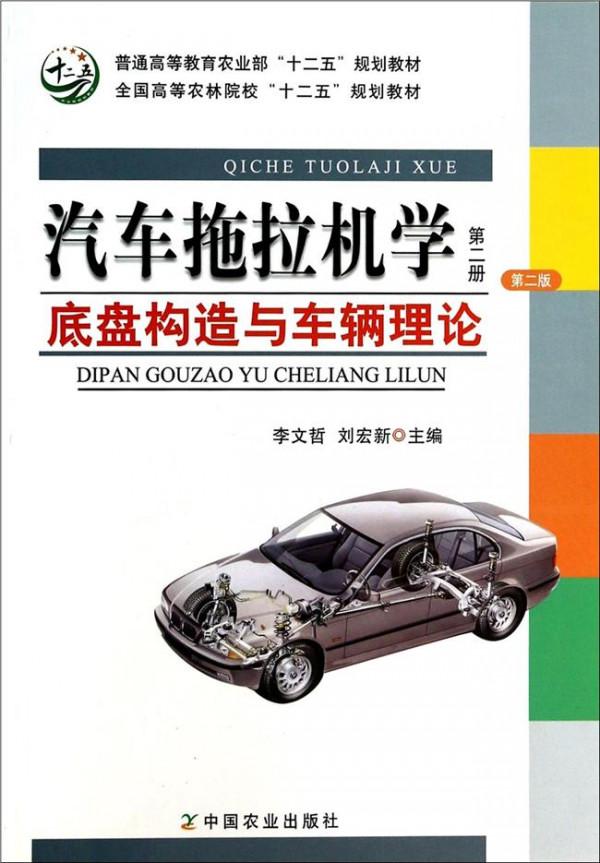哲学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个性——张一兵教授访谈
张一兵教授是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知名学者。自1999年出版《回到马克思》一书,张一兵又先后出版了《回到列宁》(2007)和《回到海德格尔》(2014),最近,他又完成了《回到福柯》的书稿。应该说,人们对张一兵教授这种思考主题不断游移的哲学研究方式以及下一步的打算充满了好奇,最近,张琳博士就此问题专访了张一兵教授。
受访者:张一兵,南京大学特聘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博士生导师。以下简称“张”。
访问者:张琳,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辑,博士,以下简称“问”。
参加者:周嘉昕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问:您在中央音乐学院的一次讲座中曾提到:“哲学实际上是每一个人形成内在精神个性的历练过程”,“哲学实际上跟神性相关,它很多是体悟”,“哲学是思想,它不是知识”。在另一次访谈中您说道:“哲学是开智的,它会使你在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时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创造性思考结构。”我觉得这些段落里面多少表达了您的哲学观。可以请您具体谈谈您的哲学观吗?
张:如果说我有一种哲学观,它跟那种概念化的体系哲学还是存在一个间距的。我记得在一本书后记里曾讲过,当时我们专业里面,像孙伯鍨老师、胡福明老师、李华钰老师,我们遭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它至少在南京大学已经有很多变化。
我们的老师已经不再是按照前苏东体系给我们简单讲概念,孙老师、李老师和胡老师比较多的都是基于原着的文本解读。我们78、79级研究生就学的那个时期,应该说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我们在面对马克思、面对黑格尔的过程当中,虽然很细地去读书,但阅读的时候还是能够充分发挥创造性和想象力,没有什么禁区,我们不会简单相信马克思一定是对的,或是黑格尔的传统解释不能碰。
所以,慢慢地就会对哲学有些自己独立的想法。我们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知识要点,而是如何去思考,如何形成自己独立面对世界的这样一种方法,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这也是后来我在做哲学研究,或者教书的过程中强调较多的东西。
对我们这批人来说,哲学更多地还是一种运思的方式,一种思考的存在方式,它不会外在于我们的生命过程。我们这些人学哲学,有很大的偶然性,同学中要么是“文革”以前的老大学生,要么是有一定实际社会经历的老高中学生,我算是同学中年纪偏小的。
通常,一个人能够学好或研究好一个东西可能是非常热爱才能做到,但哲学并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在当时那个时代里非常偶然地进入和遭遇的。当然,虽说进入哲学是个偶然的事情,但是至少自己还是有一部分天生的东西跟这个学科比较接近。
进来了,就真地喜欢上了哲学。所以,如果说我有一种哲学观,也应该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观,就是你向这个世界发出声音的一种方式,你的存在方式变成了一种哲学的思想方式。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会比较拒斥把哲学当作传递给别人的一种概念,传递一种结论,传递一种知识的过程。我从一开始会非常抵触现成性的知识,这种观念慢慢又会扩展到我对大学教育的理解。在本科生通识教育的第一堂课,我都会讲这样的问题,大学主要不是学知识,主要是体验生命的意义、存在的意义。
所以,哲学、人文科学,然后艺术,这些方面都是离生命特别近的部分。哲学,它会非常拒斥那种死掉的知识概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问:您建议大家通过哲学史、思想史来进入哲学,“因为哲学表现为一个历史连贯的解决问题的过程,了解每个时代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问题,这样你会有一个全景性的思想建构。”能具体讲一下您所说的“全景性的思想建构”吗?
张:我一开讲座就会被问如何学哲学,可是真的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有趣的是,通常提这种问题的学生还往往不是哲学系的同学。依我自己的想法,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做哲学,如果将来要成为有成就的思想家,还是要有天赋,哲学之思与宗教、艺术里面强调的那个悟性相关。
它确实是如此,很多创造力的爆发点,都不在于那个理性的积累、线性的一点一点往前走,原创性的思想通常是突现的灵性存在。不是所有人都能学哲学,这是一点。第二点,如果是想了解哲学这个学科,我个人的建议一般都是读一点思想史,这不限于哲学史。
我以为,了解一个学科最重要的方面是了解它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就有可能对这个学科有一个历史性的理解线索。而所谓全景式的掌握,这应该是专业学习的要求,这个要求会相对高一点。
在哲学研究中,有些人总想做一点原创性的东西,但所谓的原创是建立对前人驻足地方的深刻了解,按阿尔都塞的话说,就是读出空白,读出学术先辈以为完成而实际上没有完成的问题之处。所以,这个全景又有一个纵向发展线索的维度,就是你必须知道你自己的起步和你了解一个思想史断裂中呈现的可创新的问题原有的解决程度如何。
就像齐泽克、列维纳斯一批人都讲过,今天海德格尔是当代哲学的最重要的一个前进路标和参考坐标,任何哲学研究者都会把海德格尔拿出来作为一个标尺,你和海德格尔的距离就是你跟当代哲学前沿的距离,海德格尔已经解决的问题是你将要新进思考的一个比较近的标注点。
就像我们计算机系统崩溃的时候会有一个还原点一样,所有的偏差和错误都会在还原点中得以清除。
真正的学术还原点的历史链环会构成在东方的、西方的思想史的基本发展线索。这里的全景式的构境意义就是如此,它不是那个研究视域的宽阔程度,而讲的是从哲学的源起开始,然后一直到今天的问题驻守的那个地方,这是我们试图去寻求到真问题向前走的最核心的部分。
显然,我的全景式把握讲的是去思考连贯性解决问题的过程,但这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认识断裂。当代思想家,特别是从法国科学认识论的传统生长起来的欧洲学者,比较多的都不是强调那个连续性,而是拒斥总体思想史,反对起源和目的论,主张关注思想史中出现的“认识论断裂”。
这个认识论的断裂是由巴什拉、康吉莱姆提出来的,后来在福柯、阿尔都塞的哲学方法论中得以延展。相比之前面所说的连续思想史线索中的驻足点,这个断裂似乎更难理解一些。
比如,福柯读马奈的那幅著名的画——《弗里·贝尔杰酒巴》,他在其中读出了某种断裂。一开始读福柯的这篇文章,我觉得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对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绘画的线索和所有美术专业的学术还原点并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福柯讲的美术传统中的断裂,我们不太容易进入,比如为什么说马奈的画是一个断裂。依福柯的分析,从用光上来讲,马奈用光是一个平面光,和过去传统透视法中有景深的光是不一样的,平面光让对象直逼观众的目光。
但如果你不了解西方绘画的历史线索,你就可能不了解马奈的革命意义。就像进入任何一个学科,你只有知道它的发生和发展进程的历史线索,你才会知道它每处变动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明白你自己可以做什么。
这个我所谓的“全景式”跟前面讲的方法论自觉不同,这是一个思想史定位的问题。我们可看到,国内的一些学者在写文章或者跟人讨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思想史的什么位置,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21世纪某个时段中我们民族学术思想发展的什么断代上,这个断代在世界理性思维和发展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中,由此,他的言说会成为某种空洞的自言自语。
全景性把握是一个历史定位问题,它不是方法论自觉,对此,我会用话语的历史反思性这个表述。
问:西方现代思潮中跟马克思沾边儿的思想家,很多都出现在了您的论着中,而且有的思想家正是经由您和您的团队的引介而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并进而有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您是如何定位自己的学术工作的?同时您是如何理解并处理前沿与经典之关系的?
张:好吧,我现在可以预告一下,马上就会有很多跟马克思不沾边的思想家也要出现了。在我原来做过的人头方面,阿多诺、阿尔都塞当然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将,拉康跟马克思基本不沾边,鲍德里亚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海德格尔与马克思有内在关联,而福柯到后期是与马克思有点沾边的。
我即将做的广松涉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接下去,在编译出版方面,我们会出版巴迪欧、阿甘本、朗西埃、齐泽克和维利里奥等人的一批书,这些人,大部分是齐泽克2007年访问南京大学时向我推荐的他的朋友。
我们还会出版佐恩·雷特尔的一本重要著作《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①,他是跟法兰克福学派很近的一位思想家。我认为,他是第一个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透视,真正解决了康德难题的人。
此外,我还会关注马拉布、斯蒂格勒,这对曾经的夫妻都是德里达的学生,但后来的学术道路却是不同的。还有德国今天最重要的哲学家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他算不上左派,但却是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真正的激进知识分子。
也因为后面提及的这些思想家并没有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所以,我现在已经把相关的译丛书名换成了“欧洲激进思潮译丛”,这样面会宽一些,包括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激进话语。
其实应该申明,我的立足点还不在于重归经典或者前沿开拓,相对于我自己的哲学思考,这些都是辅助性的工作。从我自己来讲,特别希望能够有中国学者自己的一种独有的哲学思想。至少我做这些文本解读和译介,实际上只是做一些准备和铺垫工作,和这些大师对话,是对自己学术思想成长和验证最重要的方面。
我做当代这一块,并没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要求学生。我在研究生刚毕业的时候,笔记里面全是复杂性科学、波尔的量子力学和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一类的东西,心理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是我特别关注的方面,然后我才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这是我当时理解的当代前沿,我并没有要求我的学生这样做,但我觉得自己还是尝到甜头的。比如,同样是做经典文献,这可以有两种做法:一个是用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方式,即用原理来反注文本的解读模式来读原着;另一个则是在新的各个学科的方法论视域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弯路(孙老师的话叫“深刻的错误”)中来重构经典。
实际上,在我“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的读经典的过程当中,在遭遇文本时已经不知不觉地突现出很多新的支援背景,这使经典文献本身的呈现会是断裂性的构境图景。
所以,经典和前沿的关系不像我们想的那么隔膜和遥远,在我的“回到”里面,更多的是构境论意义上的“回到”,很多都是一种重新解读。我觉得,如果说经典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安身立命的学问的基本训练,那前沿就是保证我们有最新的方法论和最活跃的兴奋点的一个支撑。它们是一个互补关系。
问:我注意到您的著作、您的关注点、兴奋点一直在变,感觉有很大的跳跃性和跨界性。这会让读者感到难以把握您的问题域。而事实上,您在教学和研究中强调“作为问题的历史”与“作为逻辑的思想史”之间的对应关系,这里想请您谈谈,您的思想史研究最终指向的是怎样一些基本问题?在您一以贯之的方法论自觉之外,能否为读者简单勾勒一下您的问题域?
张: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没办法简单回答的。我始终关心和一直在做、在思考的过程,经常会是异质于我公开发表的“主题游离”的解读性文本的。就像我刚才提到从实践结构开始慢慢步入构境论的过程,这个讨论域实际上是一直存在,可是,一直到现在,这个独自的思考过程的内容,除去上世纪80年代的一次系列论文,后来我并没有把它很集中地公开发表过。
并且,对于我全部的文本解读进程中遭遇的思想家及其文本专题研究,我无法把这些大师、把所有“回到”的部分归个类,做个固定的研究域,真的归不起来。因为,这些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形成我自己的想法,每一位大师和他们的文本都是作为我很重要的对话者和反思对象。
如果说,我有一个不断思考的非目的论地“走向”构境论的问题域,即从辩证法的逻辑到实践的结构再到塑形-构式=构序-构境的整个过程,我还没有开始把这一部分的全部思路重新整理完,我虽然也在文本发表的外部做了几个标志性的公开发表的还原点,包括明确提出构境论,以及从赋形一直到塑模的前设理论过程,但实际上这个过程都还在进行当中。
你所问的问题域是要说,你的这个主要对象是什么?学术关注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从马克思也好、海德格尔也好、福柯也好、齐泽克也好,仿佛就是在他们这个很大的部分里面形成不了一个从外部一下能够直接抓住的那个东西。
因为,那些传统哲学里面讨论的所有问题,在我这里都会是不够的,我不会拿那样的问题域来约束我自己,让我形成一个和传统哲学主题相关的部分,而且也没有。
问:那您的问题域与传统问题域的差别何在?
张:哈哈,事情又回到它的原点。我觉得,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么一条指向新的讨论域的思考线索。显然,对习惯于传统哲学讨论的人并不能很快地进入其中。没关系,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比如在马克思那里,我关心的东西是从关系性社会存在然后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经济关系结构的颠倒。
到拉康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是一种关系总和,被颠倒为一种负的、空无的关系本体论;阿尔都塞那里也是如此,经过海德格尔到福柯,基本上都是在这条线索上。
但你很难把它定位为什么主题,本体论还是认识论,或者人的主体论。如果要给它命名的话,我关注的线索,按照我自己的说法就是从实践结构向构境论的这样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所有对话的那些大师和文本,与这个线索相关的部分被不断地提炼出来,正是这样的一个为我所用的思考过程。
我从来没有用认识论、本体论或历史观那种传统的学术讨论域来捆住自己。你会发现,需要深刻地理解的一个问题是,列宁通过马克思理解了黑格尔,在哲学中被界划为不同领域的所有东西是同一个东西,用列宁的话说,就是被称之为本体论的辩证法和逻辑学、认识论是一个东西,过去这种领域的区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时代思想发展的特定产物。
我们在海德格尔那里也会看到他对传统本体论的存在论重构,用关涉性的内居论对认识论的彻底否定,这里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思想贯通性。
认识论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对象性认知的二元分裂,当你说属于认识论领域的时候,无形中已经掉到传统形而上学中去了。
你会发现,传统哲学中这些边界在我这里会经常游离得很厉害。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做得比较多的是认识论,稍后一点,自然科学方法论关注多一点,回到马克思那部分以后对社会、对人的关注多一些,但都不是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东西,我自己关心的不是这些问题。
比如,我早期对实践结构的思考,为什么会生成一个实践格局的概念,因为当时思考比较多的一个方面就是库恩的范式说。范式说是有现实的实践基础的,库恩讨论的是科学理论范式对实验和研究的规范制度,但每个时代科学的范式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库恩是没有回答的。
而我是想到马克思的社会生产方式、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结构,它才是形成一个特定时代认知结构的最重要的基础,这是马克思在颠倒黑格尔的时候想清楚的一个问题。
但是,到80年代后期我开始重新解读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时候,这部分更深的思考内容我从来就不发表了,一直到2007年。这个被暂时悬置起来的思考构境是始终存在的,它一直存在于我的努力当中。
比如说我在写《回到马克思》的过程中,我会把马克思的相关内容重新提炼出来,但我不会写成文章。所以,在表面上的文本发表进程中,似乎从实践构序到构境论之间存在着很长一段我的思考链的中断和空白。如果仅仅从已经发表的东西来看,人们发现不了真实发生的东西。你看,不太容易说清楚吧?
问:因为我一般觉得,思考的动力来自困惑,所以我想知道您的这个思考链条,它的缘起性困惑是什么?
张:我这个思考过程好像真还不是从什么具体的困惑开始的。通常说,很多学者会从一个困惑开始,比如从某个不理解的问题开始自己的学术研究,我这里似乎从来没有过。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我进入一位大师的思想构境时,有些地方我会遭遇到微观性的难题,自己思考行进过程中会遇到一个理解上的障碍,但这些具体的问题都会在不断的文本精读中或自己的进一步思考中得到解决。
比如多年以前建构实践格局概念的过程中,当时做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因为受到德里达解构理论的影响,我就在想,过去马克思提生产方式的时候是在肯定性地建构一个生产内部的结构性的东西,那么,所有的社会生活本身,在通过活动建构生产结构或者社会关系结构的时候,应该瞬间同时又都是解构的,消解的。
我当时努力在想的事情是,德里达已经提出来这个结构的消解本身是不是合法的?他和马克思的链接在什么地方是可以进入的?既能够坚持马克思原来在整个历史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里边功能性这样一个过程,又能吸收解构理论非常合理的部分。
这就有了实践格局这个概念,格局通常是在动态力量作用形势中建构的变动的功能结构。这样的问题是我在思考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难点,当我把新东西和我原来依托的东西结合在一块的时候,我会比较快地找到消化的地方。
因此,过去被假设为肯定性结构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在我这儿迅速地变成一种同时建构-解构的双面性的东西。比如刚才讲建构论的时候,你只是问:你是不是建构论?但我所有的“建构论”其实同时都是解构论的,但是我没有完整地说出来。
然后,为什么选“构境”,我刚才讲构境问题是一个中国传统的思考,但我在选用构境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具体问题是因为这个情境存在本身的消解性,人的所有情境都是瞬间出现、瞬间消失的,就像马斯洛讲的高峰体验一样,它不是一个凝固化的状态,一个不可消失的东西停留在那儿,它没有。
海德格尔和德里达都同时遇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海德格尔是在“存在”(Sein)上打叉,而德里达则是将存在擦掉,而构境本身是自身消解的。这个同时建构和消解、在场与不在场的构境,就是人的生存的真正本质。这就是我所遇到的难点,它还在进一步的解决过程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