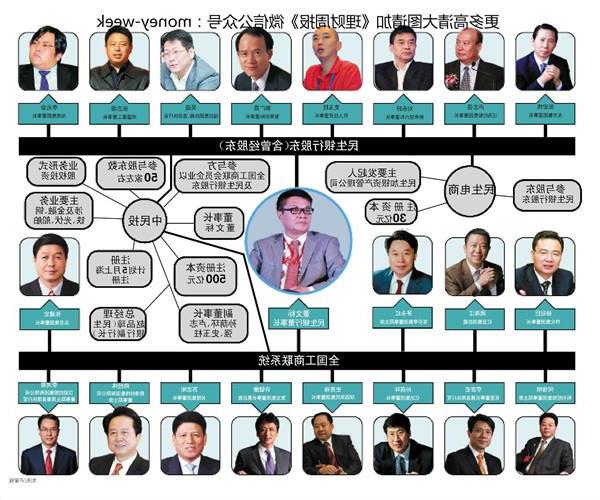董豫赣周榕 董豫赣对话周榕 北京的清水会馆
董豫赣对话周榕 北京的清水会馆 作者: 韩宪澄 可能很多人看过了 董豫赣对话周榕 北京的清水会馆 2006.10 DOMUS 宏大叙事与个人微叙事 周榕:我看了清水会馆的平面图,感觉它还是对基本的形式咬得比较紧,整个建筑环环相扣,逻辑、对位的手法等等都相当紧密。
设计本身的质量肯定没问题,而且国内现在能做到这种质量的房子很少,但我想问的是,如果你现在再设计这栋房子,会不会还是按这种方式做,因为你已经研究了几年的中国园林,可能会有很多改变。
你以前做的那个“水边宅”,和这个清水会馆有异曲同工之效,都有很紧凑的平面,以一种非常紧凑、自足性的空间为特征,具有仪式感,比如厕所啊、餐厅啊。每一个单独空间的这种完整性会使得它的物体感比较强,尤其是你又采用了一种特别突出材料的做法,就是清水砖的做法,这就把建筑的“物质”属性突出了很多,而把中国园林的那种灵动感(减弱了),虽然你这里用了很多花窗的做法,但我还是觉得它的西方性比较强。
这和我所了解的你的中国园林情趣颇为不同。这里很多小空间和中国园林非常相似,但就是因为用了这种纯粹的清水砖材料,每个部分都感到物体在膨胀,而不是内敛退隐的,每一个空间的规定性都太强,而自由性就削弱了。
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西方的建筑语言系统,和你所醉心的中国园林的这一套搭接的不是很自然。 董豫赣:可以借用我的业主对这个房子的评价——它既不是园林,也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变形的四合院”,就是说,还是有某种仪式感,但又叠加了一些园林的东西在里面。
说到空间的自足性,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等同于西方建筑学的“自明性”,但有一个前提我承认,就是做这个房子的时候,东西方的东西在我头脑中交织得非常厉害,就像我在写博士论文时感到的,我觉得我对东方的了解不如对西方的了解,这非常让我受刺激。
所以后来我理解的自足性就渐渐有了另一个角度,不再是科林•罗或者埃森曼在讨论柯布西耶的建筑时的那种自明性角度,因为那里的自明性强调物体是可以自我发生的,而我觉得这里如果用独立性就比较好解释一些。
而“独立”恰恰是我对中国园林的一个理解,这是我读中国诗、山水画等等感受到的,它有一个很强的特点,就是片段的独立。当然独立以后怎么发生关联,这是区别的开始。
中国有个词叫“对仗”,这是西方没有的,而对仗的前提就在于,如果这个东西不独立,那下一步就不可能做,所以必须第一句话就把话说完,并成为下一句的起点,这里强调的是片断的独立。
我思考的就是将不同的片断搁在一块,我相信自由就发生在这些原本各自独立的、且差异性非常大的片断的对仗并置之间。至于把哪些片断放在一起以及依据什么来进行对仗,我到现在做中国园林研究已经第五个年头了,但还是觉得根本不够。
从这个角度说,你可能会觉得它里边有一些硬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阶段已经非常好了,因为你已经开始自觉地意识到有些个人的东西要做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认为建筑学是一个集体的目标、是人类的目标。
周榕:我觉得你说到的一个论点挺好,就是建筑学不需要为宏大叙事负责,建筑学本身承载不了人类命运,承载不了一个集体性的叙事,而当代建筑师的一个趋向就是向个人微叙事回归。我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谈谈中国建筑师如何一直沉溺于宏大叙事中,老一代的都是新古典主义的宏大叙事,包括张永和也是用西方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来摧毁中国传统折衷主义的宏大叙事,总之,都是在用一个比较空洞的大词来对待建筑学,比如什么逻辑、法则等这些抽象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能够觉悟到建筑学向个人的微叙事转变,这是挺好的一件事,但我要指出的是,你这个房子恰恰和你刚才的表述不一致,因为我在每个房子中都看到原型的力量,你其实在替很多背后的人发言。
比如那个卫生间,这其实不是你个人的微叙事,而是你比较偏好的宏大叙事。 董豫赣:我不知道你这里说的个人的微叙事和个人的偏好有什么差异。 周榕:我觉得是你一直受到这种宏大叙事的教育,这些东西已经进入你的潜意识,你虽然说不要宏大叙事,但一动手画图,这种潜意识又使你把人类历史上、特别是西方历史上的很多建筑原型做一个勾连。
比如这两个环,我们就很容易想到康,想到卡洛•斯卡帕,甚至从一些细部上想到马里奥•博塔,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南美的建筑师、许多地区性建筑师,以及一些善于用砖的古典建筑师。
在你的潜意识深处,其实还是在跟他们进行勾连、进行对话。你不自觉地一出手就做到这一点。 董豫赣:我必须打断你,是因为我上次和童明也聊起这事,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意识,你回避不了过去所学的以及现在正在学的一切,那假如人人都有自己的潜意识,人人都回避不了,那这就不是个人的问题,如果这不是个人的问题,那…… 周榕:当然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我的意思是你的这种紧张感是从哪儿来的。
就是因为在你的潜意识深处有一种恐惧,对失去法则的恐惧。因为你现在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中规中矩的,都符合所谓的建筑学逻辑和建筑学法则。 董豫赣:这点我知道,上次史建也来说,你做房子就应该去一下罗马。
但我心里觉得,人不一定要做好所有的准备才开始做事,等你所有的准备都做完了,估计你也就不想做事了。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看到我那两个圆洞都觉得像斯卡帕,但其实那个想法非常简单,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因为把两个或者三个圆搁在一起的形式,在你能想到的人类史中可以列出一大堆名字,但每个地方用的都不一样,如果不能看出这其中的微观区别的话,那我觉得这恰恰是在用宏大叙事的眼光看问题或点评一切建筑,因为只要看到圆的,就会想起康,就觉得和康有关,可是如果你又看到古罗马的呢?那又不可能想起康来,那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些意义都不大,意义更大的地方在于,你为什么用这个圆。
比如斯卡帕用圆,可能是和他对数、对鱼的迷恋有关;而我做这个,是因为我去了苏州的半园,我觉得半园的那个廊子做得太有意思了,它特别狭窄,并且为了小中做大,又折了一下,然后又留了一个八边形——我原来一直以为是一个圆形——的缝隙里种了一点东西,所以我刚才带你穿过那三个圆洞的时候,和你说我打算在那里种东西的。
所以从一个形上来看,我们可以找出一堆我们知道的东西,但你知道的不一定是我知道的,所以如果用你知道的东西来定义我的东西,这就又变成了…… 周榕:我是说,一个建筑师做的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文本,是允许别人进行解读的,而这种解读就是建立在一个建筑学的背景上,如果他没有接受过建筑学的训练,那这种解读是不一样的,比如,如果他受到过建筑学的训练,那他一眼就会看出你对于比例、尺度这些方面的把握和对一些细节的处理。
我对这个房子其实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就是,它是中规中矩的,就是没有任何败笔,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现在中国建筑师做的房子,有时候你进去一看处处都是败笔。
而清水会馆没有什么败笔,但是,我也没有感到特别大的惊喜。其实我对清水会馆是寄予了很大期望的,因为四年前你就和我说你在做这个房子了,我也等了四年了,而在我头脑中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想象空间,可到现场看了以后,我就觉得做得稍显拘谨了,因为你太守规矩了,每一处都无可挑剔,比例、开窗等等,反正在这个房子里端详半天,好像也只能这么做。
但是这里面,立格和破格,我在这儿看到更多的是立格,而破格的地方比较少。
包括你刚才谈到的近体诗、韵文与园林的关系,其实立格和破格相间是一种最好的状况;而特别符合诗词的平仄、对仗、音韵这些规则的其实并不是什么好诗,比如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它对仗完美,平仄讲究,但并不是好诗。
相反,比如李白、李贺、苏轼等人,常常会打破这些音律,那么这个在立格中掺进破格的东西,我觉得可能会更好。在这里,我原来期望看到一些中国园林常见的看似蛮不讲理的破格的东西,但我看到的是很多条轴线、很多对位与呼应,一种建筑学的兢兢业业的态度。
这些毫无疑问是非常好的,但离我的期望还有距离。 董豫赣:关于立格和破格的问题,首先我觉得如果还没有立好就破,这也成为一个问题。
周榕:我不是假设不立就破,我只是说,这个房子和水边宅,都有非常严格的对位、转折等,显得紧张有余、放松不足。我知道你在这个现场做了两年,现场本身会有很多即兴的成分。其实现代建筑师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建筑师和工地分离,去推敲一个图纸上的完美的东西。
而我觉得现实里面,如果能即兴的出来一些华彩乐段、一些特别有趣的东西……但我看到的还是非常精确的执行一个抽象空间的完美模式,而不是即兴地让砖舞蹈起来。
比如这些大片的花墙,它其实表达的是一个概念化的墙面,就是要把每一个花纹的纹式做好,它没有把花墙本身的那种可能性、对墙本身的挑战(挖掘出来),而还是规规矩矩的一排,这里所有的花墙我都仔细看了一下,做得都是这样,包括那边700平米的房子。
这是一种集群式的方法,而不是个人话语的表达。因为你在替背后很多人发言,这点你自己都很难意识到,但确实是说了很多,比如你还要替半园发言。 我在想怎么能够把建筑师或者古典(工匠的工作借鉴过来),他(古典工匠)自己要砌砖头,要凿梁、锯木头,要做很多这样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灵感和新的创意会出现,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破除预设的东西出来。
实际上我总说建筑是戏剧,而不是电影。
一部电影可能是完美之作,中间不会出现瑕疵,不会出现有什么对不上的事,演员也不会摔跟头,不会突然失误,但是它确实没有生活里面那种特别真实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神秘性,一种现场的氛围,一种灵光所在,它应该根据现场做出来。
而我觉得你的现场工作更多是投入在如何坚决执行在另外一个空间里面构想出来的纯粹的东西。 董豫赣:我觉得你这是在帮我说话。你说我的背后有个半园或者有一些什么,而我觉得关于“个人”,在罗兰•巴特以后,假定个人是万能的已经是荒谬的事了,因为你是一个建筑师,你只能做你自己能做的事情,你不再是神,你不是能满足所有的要求。
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你自己能接得上的,你就会变成什么都不是,所以你肯定要跟一些东西接上。
你刚才谈到的紧张和放松,我跟你观点不大一样。比如你以前跟我说,斯卡帕、康、还有西扎中,你觉得西扎最放松,但对我来说放不放松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房子。
我的性格不是放松的,我可能更容易紧张,我做的东西就表现紧张。所以紧张或者放松都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东西,关键是不是适合你的性格。我做的窗格子都中规中矩,但每个地方的差异都有它的理由,因为我不能做一个我不肯定的东西,比如你说让砖舞蹈起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让它跳这种舞?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建筑物体》,讨论柯布的建筑怎么发生的。
所以它跳不跳舞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它是在这儿而不是那儿。 周榕:我觉得建筑学的原则,其实是在代表大多数人发言,这恰恰是一种宏大叙事,是一个集体的说法,只不过经过多年建筑学的实践和考验,发现这些地方被大多数人接受,所以我仍然觉得你建筑学功底很深(笑)。
董豫赣:可是你回头想想,这个园子里用同一个材料,造价基本差不多,如果说大家都觉得这是能接受的,那为什么这个房子之前没有人这么盖过? 周榕:我觉得你这个房子不一样,它有两千多平米,如果是七百多平米的尺度,那其实会差得很多,本质上因为你使用砖的材料。
这个房子你用了这么多砖,之所以没觉得很压,是因为它空间足够大,院子足够大,如果院子小的话根本达不到现在的效果。这个房子有一些无比巨大的空间,具有仪式感的空间,而且很多空间形成一个嵌套,形成一个砖的迷宫的做法,对于没有这种空间体验的人来说,当然会觉得很有趣。
但我觉得在材料方面,大,一方面挽救了它,另一方面大对它又并不是一个好事,因为如此匀质的材料,以一种不厌其烦的方式在重复的时候,这个体验多了以后,一眼看过去全是这种红砖的东西,恰恰会有一些问题出来,就因为它太匀质了。
比如在这么大一个地方的生活体验,永远都在墙和窗户这样一种方式之间,其实是同一句话不断地变化说法,或者同一种语言不断地说着相类似的话。
这时大本身就成了一个双刃剑,一方面会形成力量,另一方面就会觉得枯燥。 董豫赣:其实材料没那么重要,中国园林里,比如现存的苏州园林里能剩下得几乎全是白,它变成另外一个匀质,可是没有人认为它是匀质的。
周榕:你看苏州园林难道只有一种材料吗?只是墙是白的。要说苏州园林,我觉得恰恰有一点,就是根本不强调每一个房间的仪式性,跟你这个建筑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类型学的方法,计成说:“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亭和榭没有关系,只要知道亭是一个类型、榭是另一个类型就行了,不需要知道具体一个什么样的亭,什么样的榭。
像你设计的餐厅中间一个大圆,上面还有几圈光,墙上有突出,还有缝,所有这样精心做一个物体,就使得物体感强得多,而且砖这种材料本身就具有实体感,也就是物体感。
它跟中国园林的精神还真是不一样。 董豫赣:这里有一个特别大的矛盾,宜亭斯亭也好,宜榭斯榭也好,那时候中国文人是不做这个的,亭不用自己做,榭也不用自己做。
而我们现在的专业就是做这个。我觉得重要的是,你会做一些东西后,慢慢你会改变它的做法。 周榕:关键是,这里很多空间令人非常惊奇,或者就是仪式性或规定性的空间,这些空间对于你整体的房子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益处,可能增加一些噱头,增加一些“景点”,但是这些“景点”把整个空间的流畅或者有趣的东西阻隔了。
我觉得在你的院子里远远没有在你的房间里精彩,这就是原因所在。 董豫赣:我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买中国园林的石头什么的也不大现实,而且根本也不可能;还有一点,我在南宁做的两个房子,态度就和这个房子有非常大的差别。
比如,我最近在南宁明秀园做的“一卷山房”,因为那个园子里天然长的一块石头特别像董其昌画的一座山头,那个房子的起点就是那堆石头。
而这个房子,我一开始面对的就是…… 周榕:你这话说到了一个点子上。你刚才说的一卷山房,可能更偏向于我说的这种个人微叙事的方式,因为你是有东西可说,一张白纸最难画。
比如一张纸上已经滴了一个墨点子在上面,你就着它做,反而会有很多别出心裁的东西出来。而像你做这个房子的时候,恰恰没有最核心的一点来围绕它做,反而变成以很强的逻辑秩序来做。
董豫赣:这一点有——但可能不像现在表现出来的那么强——就是这个游泳池。原来任务书里写明必须有一个游泳池,并且当时甲方和我说过一句话,就是他觉得北京特别干燥,所以他希望他的厅堂里便能够湿润一些。
那怎么让这里湿润,用加湿器当然是一种方法,但那不是建筑学的方法,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游泳池做在东南方位,这样夏天的东南风就会把水汽吹向整个房子。由此为起点,其他的房间布局、南向光的解决啊等等,做了很多建筑学的剖面图之类。
除此之外,我还希望游泳池的水用完后不要直接排到市政排水管,而是能环绕整个房子,你能听到、看到它跌落、流动。我希望的就是把它的流动过程展现出来。这些东西就构成了这个房子的基本格局。接下来,我就把这几年没房子盖憋着的很多想法搁在这里,有些搁在这块不合适就搁那块,搁完了以后在想想它能干什么,这点我毫不隐讳。
包括前面那个假山和水,我开始不知道那里能挖水池,因为也不知道那里有没有地下水。刚开始只是做一个类似大地艺术的园子,后来他们回填土方需要土,挖到两米多时看到地下水了,这太让我兴奋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开始做那些东西。但是有一点我做过努力,我想建筑学这个东西,可能十年的西方式教育还是压倒五年的中国文化的自觉,所以我刚刚说到片断,我拼起来的时候,它是不是按照一个标准建筑学的古典比例之类,我从来没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我不信感觉,我不大会跳舞,因为本身它跟我的性格不大能够融洽,比如像我看《时代建筑》上罗旭做的那个房子,我真喜欢,因为我知道,只要你画图你就盖不出那个房子。
他的性格跟我不一样,比如他对家庭的态度,对女人的态度,我根本不可能做到他那么放松,那我做建筑怎么可能像他那么放松?可是我真喜欢他的东西,我老早就从吕彪那看了他的图片,他能把砖用得跟布一样。
周榕:他是完全建立在没有任何规范的基础上,他完全不懂啊,只要那些砖掉不下来就行,掉下来也无所谓了,反正砸着的是自己。 董豫赣:我第一次看见吕彪那些照片上已经裂了,就拿胶条粘上。
所以那个做法本身你真喜欢,可是让你做的话,你立刻就知道你做不了。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就做你能做的事,跟自己的气质比较匹配。 周榕:你要说到这个地方那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这牵涉到判断什么建筑是好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最后的定论,每个人喜爱的都不一样。
只能说,我本身经过这么多年建筑学学习——今年正好20年,在这么长时间的学习以后,我挺厌烦建筑学的这种陈词滥调的,比如说这面墙上这俩洞,确实看着不错,但我就不太喜欢。
其实从建筑学来说它是很规矩的,但是我看着挺别扭。 董豫赣:我从来没觉得它规矩或不规矩,那就是两个灯的位置,我和工人说,你给我安高一点,安两个灯,就这样。
周榕:但我看这个东西挺别扭。 董豫赣:因为它不是一个形式,它就是你要用它。 周榕:要用也可以不这么用。 董豫赣:当然可以。 周榕:为什么这两个间距是一样的,给游泳池这处空间加了这根轴线。
不就是为了这根轴线嘛。 董豫赣: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当时我准备用砖砌一个躺椅,从灯照的均匀程度它也该在那。 周榕:为什么要均匀? 董豫赣:那边是台阶,这边是这棵树,你说我两个躺椅往哪放? 周榕:那这跟灯有什么关系? 董豫赣:我躺在这看书什么的,当然和灯有关了。
周榕:这就变成了是那种现代主义最讲究的,比如功能逻辑主义。 董豫赣:我确实特强调功能。 周榕:关键是功能逻辑主义在一个很小的建筑里面非常重要,因为把你逼到极限,你没有办法,你不能浪费更多空间资源,但是对于一个两千多平米的房子来说,你有大把的空间可以呆,躺椅也有大把的地方可以躺,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停留在这样一个功能逻辑主义基础上?还要再……它本身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节约空间,比如多大一个笼子可以关一个老虎,而老虎需要多大的空间,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你说那个东西,比如这个院子只有它的十分之一,我需要灯光,可能中间一个灯,希望两边照度均匀——以前北京公共厕所就是这样,在这之间为了省空间,一个灯两边厕所照,我觉得这是在资源极度稀缺的情况下(的做法)。
而你现在的情况不是资源极度稀缺,你的态度是矛盾的,因为这儿有很多廊子就是浪费空间,没有意义,就是希望在一个有顶的地方走嘛;而很多这样的地方,你又把自己逼到功能特别极端的方式,甚至不能多一点、不能少一点,就是要匀质分配的方式。
那这两种矛盾的态度,在你建筑里面是充斥着的。 董豫赣:我觉得在任何地方,比如那个廊子,我为什么要做几个凳子在那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功能可取的话我将无从着手…… 周榕:恰恰你这个房子不是一个功能逻辑主义。
那边外头上面从屋顶下去的台阶,为什么隔几步你要把砖垛子砌进来呢? 董豫赣:那是拉筋啊,那才能搁得住。
周榕:不光是这样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这是形式主义啊。 董豫赣:你说的地方我都能解释我为什么那么做。 周榕:你说你花窗为什么做得不一样?这些花窗其实在功能上没有道理做得不一样嘛,可是你做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再比如这边台阶下去做了这么多,这是形式主义嘛,这跟功能有什么关系啊? 董豫赣:你如果说一个功能只有一个办法的话,那就不用说了。 周榕:所以说一个功能不只一个办法,现在你要说回去,又回到一个功能只有唯一性的办法。
董豫赣:我不觉得是唯一性。我以我对功能的理解解释它,我就这么简单。因为我的精力也是…… 周榕:你的态度不统一啊。 董豫赣:我不需要统一。
周榕:你要说这个就好办。那咱们就达到了共识。 董豫赣:比如我做那个书房的格子,当然它首先是个灯,没有那个灯我不会做它,但我有意把它做得像门。这个东西你说它有多少功能,多少不是功能?是不是需要三扇还是五扇?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说不清楚,可是它如果不作为灯,只作为一个格子,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做这样一个格子…… 周榕:实际上你没必要为每件事都找一个理由,我觉得你太紧张,就是在于你每件事都要找理由。
你刚才说了这么东西,每个都有理由。
董豫赣:我没理由做那些我解释不了的东西。它们一定统一在功能上。 周榕:我不同意,你这东西显然不是功能,那一堆台阶下去那是功能吗? 董豫赣:它首先是台阶。 周榕:花费很多钱做这个台阶,如果按你这个逻辑就是最直接的功能,你肯定不做这种台阶,这台阶明显就是形式,你说不清楚,你自己逻辑都是混乱的。
董豫赣:首先,它首先有一个功能才有不同的形式。 周榕:你就说这两个地方,这两个洞口和你那个台阶是一种逻辑吗? 董豫赣:这个我没想过。
周榕:绝对不是一个逻辑。那是最不直接的方式。 董豫赣:我觉得做房子的时候,如果要一天到晚想逻辑,你会烦的。 周榕:这恰恰是我希望跟你说的,就是我觉得你的逻辑太强了。
董豫赣:逻辑强是因为你老是问我。 周榕:建筑的乐趣是不是在于每做一件事情都给自己很强的理由,最后假设这些特别直接的逻辑的协调拼接结果就是效率最高,比如任何人不可能比我这房子做得效率更高了,你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成为智力挑战,你也觉得是一个乐趣。
可恰恰不是这样,你有些地方效率高,有些地方效率不高,当然你可以用混杂理论来解释,但恰恰你又不混杂,你试图用一种砖的逻辑来把这些事情全都说清楚,这实际上是一个矛盾,这个房子的矛盾都归结于这里,整个内部逻辑不统一。
而张永和在这一点上,他就比较直接,他不会出现同一个建筑里头很多自相矛盾的事,至少早期是这样,这套建筑逻辑非常强,虽然我并不一定同意他的逻辑基础,但是我觉得他至少自圆其说了。
董豫赣:那你觉得,你不喜欢他的房子而喜欢这一套说法的话,那说法与房子是分离的吗? 周榕:没有啊,我只是觉得这是建筑学的陈词滥调,我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说了。
其实秘密就在这一点,你在这里干脆不要说逻辑,一说逻辑你就自相矛盾了。但是你恰恰每做一个东西都有一个理由,因为你受的教育、包括你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一种线性因果的对接;这样一个方式,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因为现代人想得太多,这么做可能纯粹性更好一点,但是如果每件事都找理由,我觉得建筑还是蛮累。
…… 周榕:这面墙正中间放一个窗户干吗? 董豫赣:拔风啊。 周榕:拔风为什么一定要放在正中?这两个空间又不对称、又没有轴线。
董豫赣:偏也无所谓。 周榕:我不是说偏,不是无所谓,恰恰你是放在中间了,这就是你受的教育。一看就是建筑学的做法。 董豫赣:对,这个我同意,这是个问题。有可能再往上想会做得更细,比如风从哪过来,如果考虑了这些,也许放在左上角而不是正中效果会更好。
有些东西我觉得,毕竟学建筑学这么多年,这是我盖的第二个房子,等了这么久,机会终于来了,你要说不紧张恐怕也是很难的。 周榕:其实这个房子,我个人认为几乎是国内最好的房子了,我说了它没有败笔,中规中矩,放在这儿没错,但是没有错误是不是等于好?因为我觉得没有错误或者正确地处理,往往等同于没有趣味的处理,或者说没有乐趣的处理。
董豫赣:我对“绝对正确”一点兴趣都没有。
周榕:可是建筑学一旦成为教条,它就要试图教给人家什么是正确的。 董豫赣:可是荒谬的地方在于,一旦你知道它正确,你还做它干什么? 周榕:所以我说建立在功能逻辑主义基础上的这种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挺害人的,它就让建筑学越走越窄了。
董豫赣:不过我觉得人得有一个准线,让你知道宽还是窄。 周榕:关键我是觉得进去还要出来,这点是重要的。我绝没有要否定你的房子。 董豫赣:前天童明给我了一些拉土雷特修道院的照片,看那做工真的很差,这特别让我吃惊,可是那个房子我真喜欢。
我当时在想,我要求工人把砖砌得这么直,是不是因为我另外一方面特别差。我有时真的会怀疑这些。当然你说的这个拔风的窗口我特别同意,但我不认为它不是一个功能主义的问题,而是不经思考就放那了,就是建筑学的习惯。
我觉得要真是功能主义,我倒有可能把它搁在一个角上,我能够得着。而恰恰是这里我不大知道在一次盖房子里头,是所有的地方我都来想清楚呢,还是保留一定的习惯不去思考,只做自己感兴趣的点。
这个度很难把握的。 周榕:我跟你这么说,这样的处理就是一个僵尸,就是一个标本,任何人做都是这样做,我相信你的学生做也是这样做。恰恰你研究对流,风从哪儿过来,从哪儿出去,窗子放在那儿,它就有生命了,因为它不是从属一个概念、一个纯粹空间形式的东西。
你能感觉到风吹出来。这个功能就跟我们所说的抽象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具体的可感的功能反映,所有生活情趣会在那个地方出现。
董豫赣:这点我特别同意,因为抽象的功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会假设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一旦建立,我觉得建筑学几乎可以不教。 周榕: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因为所谓的宏大叙事、代表集体发言,说的就是这种抽象的功能。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你要节约资源、节约空间资源。为什么要节约空间资源?因为你有社会责任感,因为地球上人太多了,有60多亿人,每个人占的地儿太少,然后社会大同的思路全来了,归根到底还是有一个宏大叙事在其中。
但实际上你放到这儿,你偏了两米,难道60亿人就因此受损了吗?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现代主义就是把自己看成救世主,包括柯布、密斯、格罗庇乌斯这些人,就是这样啊,把自己看成一个救世主的角色,他要为社会代言,他做的所有工作都是这样,因为这些人都是社会主义者,说白了就是这样。
为什么皇军要给你做主?你为什么要给别人做主?你能把自己的主做好就不错了,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董豫赣 1967年生,毕业于西北建筑工程学院(本科)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硕士),曾执教于北京工业大学,2000年起执教于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 周榕 1968年生,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博士;山西朔州市市长助理。目前在清华大学主讲研究生建筑评论课,并从事建筑与城市设计理论研究及工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