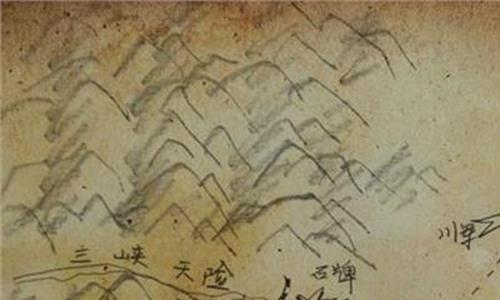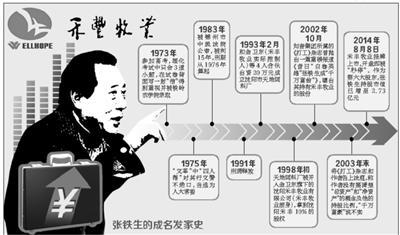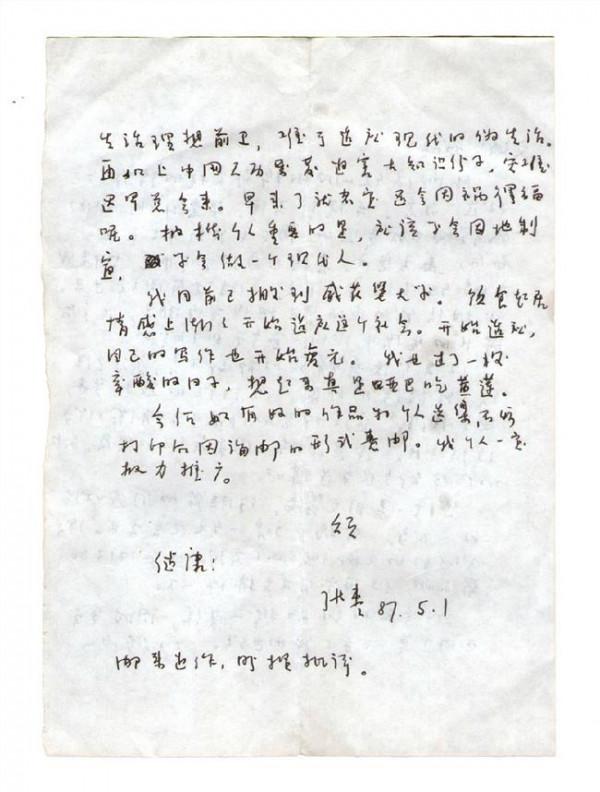张枣的诗春秋来信 张枣:诗集《春秋来信》未收录的诗(15首)
张枣:1962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考入四川外语学院念硕士。1986年出国,常年旅居德国,任教于图宾根大学。著有诗集《春秋来信》,代表作包括《镜中》、《边缘》等。2010年3月8日因肺癌逝世。
大地之歌
1.逆着鹤的方向飞,当十几架美军隐形轰炸机偷偷潜回赤道上的母舰,有人心如暮鼓。而你呢,你枯坐在这片林子里想了一整天,你要试试心的浩渺到底有无极限。
你边想边把手伸进内裤,当一声细软的口音说:“如果没有耐心,侬就会失去上海”。你在这一万多公里外想着它电信局的中心机房,和落在瓷砖地上的几颗话梅核儿。
那些通宵达旦的东西,剎不住的东西;一滴饮水 和它不肯屈服于化合物的上亿个细菌。你越想就越焦虑,因为你不能禁止你爱人的咏叹调这天果真脱颖而出,谢幕后很干渴,那些有助于破除窒息的东西;那些空洞如蓝图又使邻居围拢一瓶酒的东西;那些曲曲折折但最终是好的东西;使秤翘向斤斤计较又忠实于盈满的东西;使地铁准时发自真实并让忧郁症免费乘坐三周的东西;那会是什么呢?诱人如一盘韭黄炒鳝丝:那是否就是大地之歌?
2.
人是戏剧,人不是单个。
有什么总在穿插,联结,总想戳破空虚,并且仿佛在人之外,渺不可见,像鹤……
3.你不是马勒,但马勒有一次也捂着胃疼,守在角落。你不是马勒,却生活在他虚拟的未来之中,迷离地忍着,马勒说:这儿用五声音阶是合理的,关键得加弱音器,关键是得让它听上去就像来自某个未知界的微弱的序曲。错,不要紧,因为完美也会含带另一个问题,一位女伯爵翘起小姆指说他太长,马勒说:不,不长。
4.此刻早已是未来。
但有些人总是迟了七个小时,
他们对大提琴与晾满弄堂衣裳的呼应
竟一无所知。
那些生活在凌乱皮肤里的人;
摩天楼里
那些猫着腰修一台传真机,以为只是哪个小部件
出了毛病的人,(他们看不见那故障之鹤,正
屏息敛气,口衔一页图解,蹑立在周围);
那些偷税漏税还向他们的小女儿炫耀的人;
那些因搞不到假公章而煽自己耳光的人;
那些从不看足球赛又蔑视接吻的人;
那些把诗写得跟报纸一模一样的人,并咬定
那才是真实,咬定讽刺就是讽刺别人
而不是抓自己开心,因而抱紧一种倾斜,
几张嘴凑到一起就说同行坏话的人;
那些决不相信三只茶壶没装水也盛着空之饱满的人,
也看不出室内的空间不管如何摆设也
去不掉一个隐藏着的蠕动的疑问号;
那些从不赞美的人,从不宽宏的人,从不发难的人;
那些对云朵模特儿的扭伤漠不关心的人;
那些一辈子没说过也没喊过“特赦”这个词的人;
那些否认对话是为孩子和环境种植绿树的人;
他们同样都不相信:这只笛子,这只给全城血库
供电的笛子,它就是未来的关键。
一切都得仰仗它。
5.
鹤之眼:里面储有了多少张有待冲洗的底片啊!
6.
如何重建我们的大上海,这是一个大难题:
首先,我们得仰仗一个幻觉,使我们能盯着
某个深奥细看而不致晕眩,并看见一片叶
(铃鼓伴奏了一会儿),它的脉络
呈现出最优化的公路网,四通八达;
我们得相信一瓶牛奶送上门就是一瓶牛奶而不是
别的;
我们得有一个电话号码,能遏止哭泣;
我们得有一个派出所,去领会我们被反绑的自己;
我们得学会笑,当一大一小两只西红柿上街玩,
大的对小的说:Catch-up!
”;
我们得发誓不偷书,不穿鳄鱼皮鞋,不买可乐;
我们得发明宽敞,双面的清洁和多向度的
透明,一如鹤的内心;
是呀,我们得仰仗每一台吊车,它恐龙般的
骨节爱我们而不会让我们的害怕像
失手的号音那样滑溜在头皮之上;
如果一班人开会学文件,戒备森严,门窗紧闭,
我们得知道他们究竟说了我们什么;
我们得有一个“不”的按钮,装在伞把上;
我们得有一部好法典,像
田纳西的山顶上有一只瓮;
而这一切,
这一切,正如马勒说的,还远远不够,
还不足以保证南京路不迸出轨道,不足以阻止
我们看着看着电扇旋闪一下子忘了
自己的姓名,坐着呆想了好几秒,比
文明还长的好几秒,直到中午和街景,隔壁
保姆的安徽口音,放大的米粒,洁水器,
小学生的广播操,剎车,蝴蝶,突然
归还原位:一切都似乎既在这儿。
又在飞啊。
鹤,
不只是这与那,而是
一切跟一切都相关;
三度音程摆动的音型。
双簧管执拗地导入新动机。
马勒又说,是的,黄浦公园也是一种真实,
但没有幻觉的对位法我们就不能把握它。
我们得坚持在它正对着
浦东电视塔的景点上,为你爱人塑一座雕像:
她失去的左乳,用一只闹钟来接替,她
骄傲而高耸,洋溢着补天的意态。
指针永远下岗在12:21,
这沸腾的一秒,她低回咏叹:我
满怀渴望,因为人映照着人,没有陌生人;
人人都用手拨动着地球;
这一秒,
至少这一秒,我每天都有一次坚守了正确
并且警示:
仍有一种至高无上……
1999.(赠东东)
醉时歌
昨夜,当晚会向左袅袅漂移,酒
突然甜得鞠躬起来。音符的活虾儿
从大提琴蹦遛出来,又“唰”地
立正在酒妙处,仿佛欢迎谁去革命,
有个胖子边哭边从西装内兜掏出一挂鞭炮,
但没有谁理他。
唉,不要近得这么远,
七八个你不要把头发甩来甩去,
茶壶里的解放区不要倾泻,绽碎,
不要对我鞠躬,鹿在桌下呦鸣,
有个干部模样的人掂足,举杯,用
零钱的口吻对外宾说:“吃鸡吧”,
酒提前笑了。
我继续向左漂移,我
就是那个胖子?怎么也点不亮那挂鞭炮
我的心在万里外一间空电话亭吟唱,
是否有个刺客会如约而来?地球
露出了蓝尾巴,只有一条湿腻的毛巾
递了过来,一叶空舟自寒波间折回。
东倒西歪啊,让我们从它身上
提炼出另一个东三省,一条高速路,
通向袅娜多姿,通向七八个你,
你叫小翠,这会儿不见了,或许
正偎着石狮朝万里外那电话亭拨手机,
(她的小爱人约好来那儿等电话,
但他没来,她想象那着那边的空幻)。
她回到这儿,四周正在崩溃,仿佛
对面满是风信子。
一个老混混晃过来,
与谁干杯。性格从各人的手指尖
滴漏着,胖子的鞭炮还没点燃,
有人把打火机夺了过去,“我心里,”
胖子呕吐道:“清楚得很,不,朕,”
胖子拍拍自己,“朕,心里有数。
”
刺客软了下来。厅外,冰封锁着消息。
“向左,向左,”胖子把刺客扶进厕所。
刺客亲了缺席一口,像亲了亲秦王。
秦王啊缺席如刺客。而我,像那
胖子,朝遍地的天意再三鞠躬﹔我或是
那醉汉,万里外,碰巧在电话亭旁,
听着铃声,蹀躞过来,却落后于沉寂,
那醉汉等在那空电话亭边,唱啊唱﹕
“远方啊远方,你有着本地的抽象!
”
告别孤独堡
1
上午,仿佛有一种樱桃之远;有
一杯凉水在口中微微发甜,
使人竟置身到他自身之外
电话铃响了三下,又杳然中断,
会是谁呢?
我忽然记起两天前回这儿的夜路上,
我设想去电话亭给我的空房间拨电话:
假如真的我听到我在那边
对我说: “Hello?”
我的惊恐,是否会一窝蜂地钻进听筒?
2
你没有来电话,而我
两小时之后又将分身异地。
秋天正把它的帽子收进山那边的箱子里。
燕子,给言路铺着电缆,仿佛
有一种羁绊最终能被俯瞰……
3
有一种怎样的渺不可见
泄露在窗台上,袖子边﹕
有一种抵抗之力,用打火机
对空旷派出一只狐狸,那
颉颃的瞬翼
使森林边一台割草机猛省地跪向静寂,
使睡衣在衣架上鼓起胸肌,它
登上预感
如登上去市中心的班车。
4
是呀,我们约好去沙漠,它是
绿的妆镜,那儿﹐你会给它
带来唯一的口红,纸和卫生品﹔
但去那儿,我们得先等候在机场的咖啡亭。
是呀,樱桃多远。而咖啡,仿佛
知道你不会来而使过客颤抖。
咖啡推开一个纹身的幻象,空间弯曲,而
有一种对称,
命令左中指冲刺般翘起﹕
“决不给纳粹半点机会!
”
在森林中
1.
几件你拖欠的事情,
乌云般把你叫到小山顶。
落叶的滑翔机,
远处几个跳伞的小问号蠕袅地落进
风景的瓶颈里。天气中似乎有谁在演算
一道数学题。
你焦灼。
钟声,钟声把一件无头的金铠甲
抛到森林的深处。
那儿,雾
在秋风的边角运转着,启动
一个搁置的图像,
一个状如闹钟内部的温暖机房。
那儿,你走动。
2.
你走动,似乎森林不在森林中。
松鼠如一个急迫的越洋电话劈开林径。
听着:出事了。
天空浮满故障,
一个广场倒扣了过来。
你挂下话筒,身上尽是枫叶。
蘑菇,把古铜色的螺钉拧得更紧——
使一家磁器店嵌入葱翠的自由大街,
使那些替死亡当侦探的影子
尾随进来。
他们瞥了瞥发票上的零,
身子分成好几瓣踅出玻璃旋门。
他们向右拐,指了指
对岸的森林。
迷离的蝴蝶效应。
正午,流水吹着笛子。
磁器皎洁的表情,多姿的芭蕾舞。
它们说:砸吧。我们什么也不说。
3.
你狂暴地走动。
那发票就攥在你手中,
你想去取回你那被典押的影子。
森林转暗,雨滴敲击着密叶的键盘,
你迷失。而
希望,总在左边。向左,
那儿,路标上一个哑默的抽象人
朝你点了点头;
绿,守候在树身里如母亲,
轻脆地拧着精确的齿条。
几只啄木鸟,边说边做,
一圈圈声波在时光中荡漾。
几只啄木鸟,充盈了整座森林,和
星期一。
4.
一圈空地。
长跑者停在那儿修理他呼吸的器械。
他的干渴开放出满树的红苹果,
飘香升入金钟塔,归还或断送现实。
他因干渴而深感孤独。他低头琢磨
他暖和的掌心:它仿佛是个火车站,
人声鼎沸。
一群去郊游的孩子泼下几绺
缤纷的水柱。
光,派出一个酷似扳道工的影子站在岔道口。
他觉得他第一次从宇宙获得了双手,和
暴力。
父亲
1962年,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
还年轻,很理想,也蛮左的,却戴着
右派的帽子。他在新疆饿得虚胖,
逃回到长沙老家。他祖母给他炖了一锅
猪肚萝卜汤,里边还漂着几粒红枣儿。
室内烧了香,香里有个向上的迷惘。
这一天,他真的是一筹莫展。
他想出门遛个弯儿,又不大想。
他盯着看不见的东西,哈哈大笑起来。
他祖母递给他一支烟,他抽了,第一次。
他说,烟圈弥散着“咄咄怪事”这几个字。
中午,他想去湘江边的橘子洲头坐一坐,
去练练笛子。
他走着走着又不想去了,
他沿着来路往回走,他突然觉得
总有两个自己,
一个顺着走,
一个反着走,
一个坐到一匹锦绣上吹歌,
而这一个,走在五一路,走在不可泯灭的
真实里。
他想,现在好了,怎么都行啊。
他停下。他转身。他又朝橘子洲头的方向走去。
他这一转身,惊动了天边的一只闹钟。
他这一转身,搞乱了人间所有的节奏。
他这一转身,一路奇妙,也
变成了我的父亲。
吉祥物
如果你真愿意佩带
它便是吉祥物
它扑朔迷离,但不会
从那机器创出的小小木葫芦
以檀香油的方式
越狱似地打出一拳
“不”这个词,挂在树上
如果你愿意
“不”也会流泪,鳄鱼一样
吉祥物的某日啊
月亮正分娩月亮
凌驾于一切表达之上
树在落发
抽屉打开如舌头
如果你愿意,吉祥物便是那
疼得钻进你脑袋中的
灯泡,它阿谀世上的黑暗
灯的普照下,一切恍若来世
事物宽恕了自己还不是自己
宽恕了所窃踞位置的空洞
“不”这个词,驮走了你的肉体
“不”这个吉祥物,左右开弓
你躬身去解鞋带的死结
你掩耳盗铃。
旷野——
不!不!不!
到江南去
我们相隔万里正谈着虎骨,肥皂剧,樟树
和琴,忽然电话“嘎”地一串响,像是
卫星掉落了:漆黑。
你丢失在你正在的地方。
话筒裡仿佛憋着监听者带酒气的屏息,
和哗啦啦的翻纸声,若有若无的浑沌,或
大水,它正乌云滚滚地倒映在碎玻璃之上;
窗:有个胖姨在朝天喊谁下来搬煤气罐。
你会在哪儿呢,这一瞬,是否荒蛮果真
重临?
你,奥尔甫斯主义者,你还会
返回吗?线路,这冷却的走廊,仍通着,
我不禁迎了上去:对,到江南去!
我看见
那尽头外亮出十里荷花,南风折叠,它
像一个道理,在阡陌上蹦着,向前扑着,
又变成一件鼓满的、没有脑袋的白背心,
时而被绊在野渡边的一个发廊外,时而
急走,时而狂暴地抱住那奔进城的火车头,
寻找幸福,用虚无的四肢。
对,到江南去!
解开人身上多年来的死结:比如,对一碗
藕粉之甜不恰切的态度,对某个细节的争议,
对一个篮球场的曲解:它就在报社的对面,
那儿,夕照铺了成吨厚的红地毯,它多想
善待你啊;那儿,你忘了你的白背心和
眼镜: ,大地的篮球场,比天堂更陌生!
(1999,赠钟鸣,liebem Freund der vielen Fernen)
世界
这个世界里还呈现另一个世界,
一个跟这个世界一模一样的
世界--不不,不是另一个而是
同一个。是一个同时也是两个
世界。
因而我信赖那看不见的一切。
夜已深,我坐在封闭的机场,
往你没有的杯中
倾倒烈酒。
没有的燕子的脸。
正因为你戴着别人的
戒指,
我们才得以如此亲近。
第二个回合
这个星期有八天,
体育馆里
空无一人;但为何掌声四起?
我手里只有一只红苹果。
孤独;
但红苹果里还有
一个锻炼者:雄辩的血,
对人的体面不断的修改,
对模仿的蔑视。
长跑,心跳,
为了新的替身,
为了最终的差异。
枯坐
枯坐的时候,我想,那好吧,就让我
像一对夫妇那样搬到海南岛
去住吧,去住到一个新奇的节奏里——
那男的是体育老师,那女的很聪明,会炒股;
就让我住到他们一起去买锅碗瓢盆时
胯骨叮当响的那个节奏里。
在路边摊,
那女的第一次举起一个椰子,喝一种
说不出口的沁甜;那男的望着海,指了指
带来阵雨的乌云里的一个熟人模样,说:你看,
那像谁?那女的抬头望,又惊疑地看了看
他。
突然,他们俩捧腹大笑起来。
那女的后来总结说:
我们每天都随便去个地方,去偷一个
惊叹号,
就这样,我们熬过了危机。
(赠Y.L.)
边缘
像只西红柿躲在秤的边上,他总是
躺着。有什么闪过,警告或者燕子,但他
一动不动,守在小东西的旁边。
秒针移到
十点整,闹钟便邈然离去了,一支烟
也走了,携着几副变了形的蓝色手铐。
他的眼睛,云,德国锁。总之,没有的
都走了。
空,变大。
他隔得很远,但总
在某个边缘:齿轮的边上,水的边上,他自个儿的
边上。他时不时望着天,食指向上,
练着细瘦而谵狂的书法:“回来”!
果真,那些走了样的都有返回了原样:
新区的窗满是晚风,月亮酿着一大桶金啤酒。
秤,猛地倾斜,那儿,无限,
像一头息怒的狮子
卧到这只西红柿的身边。
厨师
未来是一阵冷颤从体内收刮
而过,翻倒的醋瓶渗透筋骨。
厨师推门,看见黄昏像一个小女孩,
正用舌尖四处摸找着灯的开关。
室内有着一个孔雀一样的具体,
天花板上几个气球,还活着一种活:
厨师忍住突然。他把豆腐一分为二,
又切成小寸片,放进鼓掌的油锅,
煎成金黄的双面;
再换另一个锅,
煎香些许姜末肉泥和红艳的豆瓣,
汇入豆腐;再添点黄酒味精清水,
令其被吸入内部而成为软的奥妙;
现在,撒些青白葱丁即可盛盘啦。
厨师因某个梦而发明了这个现实,
户外大雪纷飞,在找着一个名字。
从他痛牙的深处,天空正慢慢地
把那小花裙抽走。
从近视镜片,往事如精液向外溢出。
厨师极端地把
头颅伸到窗外,菜谱冻成了一座桥,
通向死不相认的田野。
他听呀听呀:
果真,有人在做这道菜,并把
这香喷喷的诱饵摆进暗夜的后院。
有两声“不“字奔走在时代的虚构中,
像两个舌头的小野兽,冒着热气
在冰封的河面,扭打成一团……
狷狂的一杯水
薄荷先生闭着眼,盘腿坐在角落。
雪飘下,一首诗已落成,
桌上的一杯水欲言又止。
他怕见这杯水过于四平八稳,
正如他怕见猥亵。
他爱满满的一杯---那正要
内溢四下,却又,外面般
欲言又止,忍在杯口的水,忍着,
如一个异想,大而无外,
忍住它高明而无形的翅膀。
因此,薄荷先生决不会自外于自己,那
漫天大雪的自己,或自外于
被这蓝色角落轻轻牵扯的
来世,它伺者般端着我们
如杯子,那里面,水,总倾向于
多,总惶惑于少,而
这个少,这个少,这才是
我们唯一的溢满尘世的美满。
娟娟
仿佛过去重叠又重叠只剩下
一个昨天,月亮永远是那么圆
旧时的装束从没有地方的城市
清理出来,穿到你温馨的身上
接着变天了,湿漉漉的梅雨早晨
我们的地方没有伞,没有号码和电话
也没有我们居住,一颗遗忘的樟脑
袅袅地,抑不住自己,嗅着
自己,嗅着自己早布设好的空气
我们自己似乎也分成了好多个
任凭空气给我们侧影和善恶
给我们灾难以及随之而来的动作
但有一天樟脑激动地憋白了脸
像沸腾的水预感到莫名的消息
满室的茶花兀然起立,娟娟
你的手紧握在我的手里
我们的掌纹正急遽地改变
蝴蝶
如果我们现在变成一对款款的
蝴蝶,我们还会喁喁地谈这一夜
继续这场无休止的争论
诉说蝴蝶对上帝的体会
那么上帝定是另一番景象吧,好比
灯的普照下一切都像来世
呵,蓝眼睛的少女,想想你就是
那只蝴蝶,痛苦地醉到在我胸前
我想不清你那最后的容颜
该描得如何细致,也不知道自己
该如何吃,喂养轻柔的五脏和翼翅
但我记得我们历经的水深火热
我们曾咬紧牙根用血液游戏
或者真的只是一场游戏吧
当着上帝沉默的允许,行尸走肉的金
当着图画般的雪雨阴晴
五彩的虹,从不疼的标本
现在一切都在灯的普照下
载蠕载袅,呵,我们迷醉的悚透四肢的花粉
我们共同的幸福的来世的语言
在你平缓的呼吸下一望无垠
所有镜子碰见我们都齐声尖叫
我们也碰着了刀,但不再刺身
碰翻的身体自己回头站好像世纪末
拐角和树,你们是亲切的衣襟
我们还活着吗?被损颓然的嘴和食指?
还活在鸡零狗碎的酒的星斗旁边?
哦,上帝呵,这里已经是来世
我们不堪解剖的蝴蝶的头颅
记下夜,人,月亮和房子,以及从未见过的
一对喁喁窃语的情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