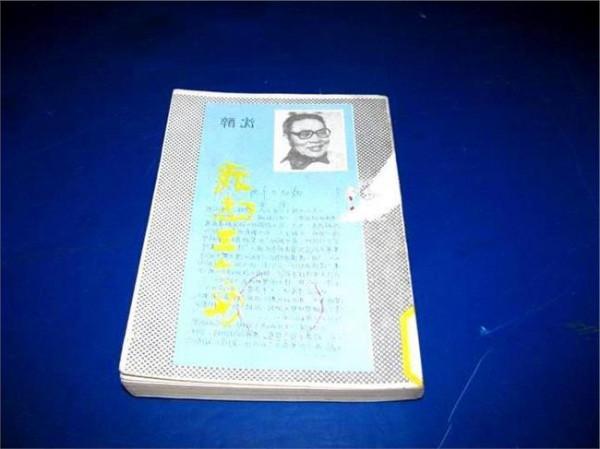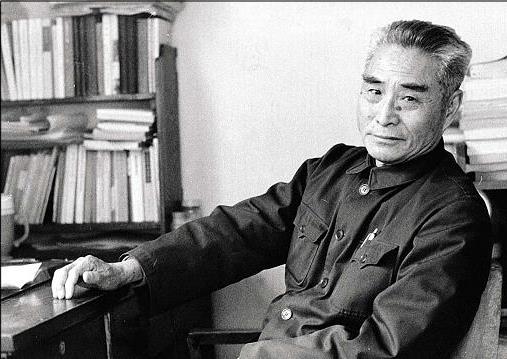沈醉得孙劝女离婚 黄维冷漠老妻自杀
文史专员当中,沈醉的年龄几乎是最小的,但转眼之间,已经年过半百了。这个岁数的人有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能抱上孙子或者外孙。就在沈醉第二次获得自由没几天,沈美娟带着一个刚满周岁的男孩从宁夏回来了。沈醉看着可爱的外孙,禁不住老泪纵横,喜出望外,一把抱过外孙,使劲亲了几口,然后问,他的爸爸呢,怎么不一起回来?沈美娟稍有迟疑,“在陶瓷厂上班哩,请一天假,要扣两天的工资!”
这位在陶瓷厂当工人的西北汉子叫张万银,比沈美娟大十几岁,而且结过婚,老婆因病而亡,没有留下孩子。当他托人向一河之隔的农场职工、北京知青沈美娟提亲时,沈美娟与他只见过一面,便满口答应了,用她以后写进《沈醉和他的妻儿们》一书里的话说,“父亲已经几年没有消息了,生还的可能是那么渺茫,自己在国内已经举目无亲,能在不嫌弃自己出身的人家屋檐下躲风避雨,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婚后的生活并不美满,张万银心情不好的时候,还会对沈美娟拳脚交加。但是,沈美娟原谅了他,因为她知道,这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自卑感在作祟,为了留住她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罢了。
听完女儿关于婚事的陈述,特别是看了女儿留在胳膊上的伤疤,沈醉没有说话,他没有责怪女儿,也没有责怪自己,只是沉默良久之后,突然提出一个建议,“你们离婚吧,如果你同意,我就给上面写个报告,申请把你和孩子调回北京。
”“我不同意!”沈美娟的回答也很突然,“你要调就把我和张万银都调回来,要不谁也别调。爸爸的好意我领情了,我的心结也请爸爸能够包涵,我家的处境比过去好了,我更不忍心把他一个人扔在戈壁滩上。像芨芨草那样孤苦零仃,因为这样的日子我过够了,不想让他再受折磨。反正一句话,这辈子我跟定了那个王八蛋,这是我的命呀!”
放下女儿的事情,沈醉又回到案头,忙他一篇材料的写作去了。这篇材料很特别,也很重要,他在《红旗》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发表的攻击鲁迅“帽子上绣着斧头和镰刀,衣袋里搞着布尔什维克钞票”的文章,就是“***”之一的***,用“狄克”这个笔名写的。
沈醉知道,“狄克”是当年上海崔万秋的座上客。而崔万秋是军统上海特区的直属通讯员,由沈醉单线与他联系,而他又联系了化名为“狄克”的***,为他的《大晚报》副刊撰稿,就是说,***与崔万秋早有勾结,而且受崔万秋指使,直接为***特务机关效劳。
花了一个星期,沈醉把这份长达两万字的材料交到全国***,立即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机关部门通过核实,通过删减,最后以三千字的篇幅,出现在有关揭露“***”罪行的中共中央文件的附页。也许是对沈醉辛勤劳动的报答,当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安部大礼堂设立特别法庭审判“***”集团的时候,他得了一张弥足珍贵的旁听证。
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沈醉觉得这句话是对他而言的。因为落实政策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年前,自己被迫参加了云南起义的全部档案,经过他从昆明以要犯身份被押重庆,又转至北京这么多年,仍被保留下来,而且在十年浩劫中幸免毁于一旦,于是云南方面根据拨乱反正的精神,把这些档案全部清理出来,送到了中央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一经审定,立即宣布:沈醉的个人身份由获赦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子女的家庭成份由军统特务改为革命干部。
宋希濂的五个子女以及他们的后代,均侨居美国。30多年来,除了大儿子在中美建交后回国探望过他以外,其余的子女都没有见过面。宋希濂思亲心切,他在同一天分别向***机关和文史专员办公室递交了假条,然后偕同妻子去公安局办理了因私护照,而在美国驻北京领事馆答应下达的第二天,他们就取道香港,启程赴美了。
动身去旧金山之前,宋希濂与妻子在香港住了两天,住在他三哥家里。第一天他去看了黄埔一期同学关麟征。第二天他去看了新闻界的老朋友、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费彝民对宋希濂的造访甚为惊讶,连呼“天上掉下个宋将军!
”宋希濂解释说,“本应早些时候来拜望你的,但害怕记者,不愿意有人对我的行踪作什么报道。如果费先生一定要发表我去美国探亲的消息,请俟我那天离开香港后再见报。”“我答应你。”费彝民快人快语,“不过我告诉你,见报是肯定的,因为你是全国***委员,又是第一个赴美的前***高级将领,对媒体而言,是条特大新闻哩!”
费彝民恪守诺言,宋希濂到达旧金山以后,才看到刚刚出版的香港《大公报》,上面有他赴美探亲的消息,也有他与费彝民的合影。翌日,美国所有的华文报纸都报道了宋希濂的和行踪,绝大多数是一字不漏地转载了香港《大公报》的消息。
不过,也有少数添油加醋甚至无中生有的,台湾方面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日报》以头版头条位置推出一篇文章,说宋希濂的美国之行是奉中共之命,“以探亲为名,行统战之实”,还说宋希濂在香港“手面阔绰,挥金如土”等等。
宋希濂写信要求对方予以更正。过了几天,《世界日报》不仅没有对前文提出更改,反而以一种用心险恶的笔调说,“宋希濂先生辗转来信说明,自称不是来做统战工作的,而且没有拿***的巨额经费。”宋希濂拍案而起,委托律师向法院正式起诉。《世界日报》自知理亏,赔偿宋希濂一万五千美元。
黄维获赦后,留在了全国***,增补为全国***委员,每月有二百元工资,妻子蔡若曙从上海图书馆调到北京,分配了相应的工作。他们还分到了一套宽敞的住房,地点在永定门内东街,推开窗户,但见流水潺潺,垂柳青青。
一日,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董主任主动找黄维谈心。万事不求人的黄维也开口了,他讲了大儿子黄新的事情,在山东农学院任教时,如何被打成右派分子,在“***”中,又如何成了现行反革命。殊不料黄维没有讲完,董主任便咧嘴笑了,“你尽可以放心,黄新的错案肯定会平反,剩下的只是时间早迟而已。”
果不其然,黄新很快来信了,他告诉父亲,自己是当地第一批提到平反的人,同时,他感谢父亲,之所以第一批提到平反,是因为全国***给当地致函,专门过问了他的事情。看完大儿子的信,黄维的手在发抖,心里发颤,他对妻子说,“趁我的双腿还没有发软,我要回趟老家,看看那边有没有需要我的事情。”
黄维去了贵溪,在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上,即使是块石头,他也会多看几眼。不过在他看来,城市变化太大,农村变化太小,春耕时节,依然是水牛耕田,木盆插秧。看在眼里,想在心头又是他描绘过的蓝图:油料昂贵,运输困难,今后插秧机上安装永动机,农民插秧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回到北京,他就把家中最大的房间开辟成实验室,把工资的绝大部分,用于设备的购置,而他的时间与精力,更是百分之百地投入其间,不惜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妻子蔡若曙苦苦等了将近三十年的生活,就这样被黄维毁灭了。她依然是永动机的反对者,昔日探监时,为了规劝丈夫丢掉幻想,她把喉咙说破,把眼泪说干,却只能换得黄维一个“滚”字,现在她试图另辟蹊径,说点别的什么话题。
适逢那天下班,蔡若曙收到大儿子黄新来信,信中告知父母,他不仅恢复了原职原薪,而且新近又连提两级,由助教晋升为副教授,另外,学院还破例分给他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一俟装修完毕,他就准备结婚。
蔡若曙欣喜若狂,箭步冲进实验室。把大儿子的好消息告诉给了黄维,让她失望的是,黄维毫无表情,似乎什么都没听见。
蔡若曙犹豫片刻,鼓起勇气,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次黄维听见了,可是就像他每次听不耐烦的时候那样,依旧是一个“滚”字!“滚就滚吧!”蔡若曙绝望了,趁着天黑,她跑出家门,跑下楼梯,跑到仅有几十米之遥的永定河边,然后一头跳进水里。待黄维稍有觉察,顿感大事不妙,匆匆赶来河边的时候,为时已经晚矣!
邱行湘对黄维的家庭不幸悲伤不已,让他痛心疾首的却是这种不幸没有发生在黄维人生的低谷,而出现在黄维命运发生逆转的时候。破镜重圆的幸福刚刚开始,家破人亡的痛苦接踵而至,邱行湘不能不哀叹人生无常,虽然他知道无论命运怎么捉弄人,生活不得不继续。
这天,邱行湘正在写一篇题为《石牌要塞保卫战》的文史资料,突然听见有人叩门。开门看时,门外竟站着蓬头垢面的外甥黄济人。他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跑到邱行湘这里,是想采访舅舅,写一本“关于你在***监狱生活的书。
”“你这本书当然大有写头!”疑虑尽消,邱行湘不觉高兴起来,“不过,光写我一个人不行,我在监狱当过学习组长,当过劳动标兵,但是还有比我表现得更好的人。”“这本书不会是表扬稿,单纯记录好人好事,我想通过你坎坷的经历,去写你复杂的内心,在你人生角色发生变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力量征服你的。
”“嗯嗯,看来你学中文的,写法和我们写文史资料还有所不同。”邱行湘安排黄济人在家里住下,他要把自己的过去从头说起。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黄济人七天的采访,天天都有这样的感受。当他合上厚厚的笔记本,揣着深深的感激心,就要打道回府的时候,邱行湘叮嘱他说:“***改造***战犯,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我能提供给你的,不过鸡毛蒜皮而已。
你要真正想写好这本书的话,就一定要到北京去。”黄济人点点头,“你给我讲了那么多,够得我消化一阵子了,所以我决定放寒假再去。”“那好,事先我会给北京的文史专员们每人写封信,他们和我过去是牢友,现在是朋友,都会像长辈那样关照你的。
”邱行湘想了想说:“不过,因为在***同属陈诚集团的缘故,我与黄维、方靖、杨伯涛等人的关系尤为亲近,在这几位长辈的家里,你想吃就吃,想住就住。至于你想了解我们监狱生活的全部过程,那就一定得找最后一批获赦的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