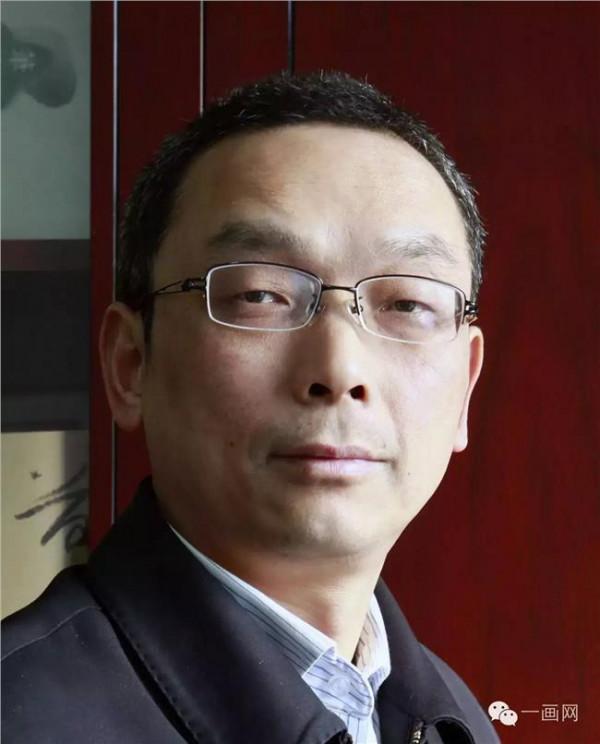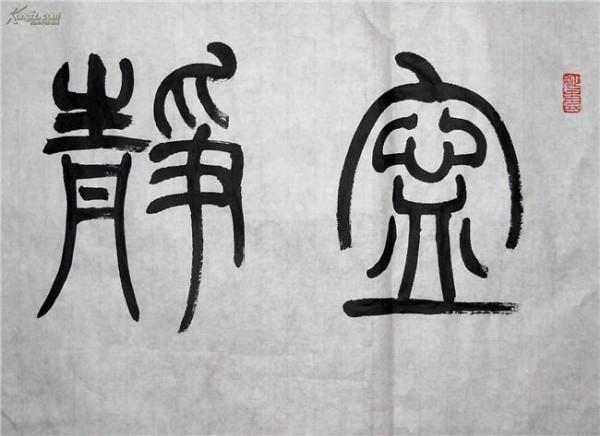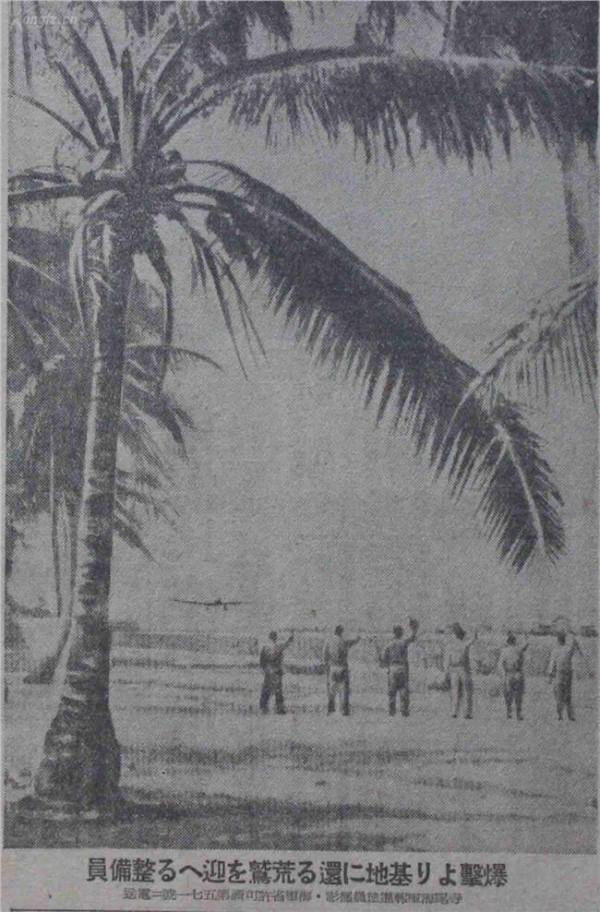上海书法家高式熊 九旬书法大家高式熊:日本所有好相机我都摸过了
高老从年轻时候开始就是照相机、音乐发烧友
2003年程多多为高老画的画像(局部)
特约撰稿 潘真
今年92岁的高式熊以篆刻、书法名世,是中国书坛的寿星之一。他是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上海市书协顾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有别于许多同行的是,除了谈写字、刻图章,谈摄影、谈音乐他也头头是道。原来,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开始玩照相机了,而他的耳朵早就被好音响、好音乐宠坏了。面对其传记的作者潘真,高式熊先生谈了他上世纪60年代那些好玩的事。
日本所有好相机我都摸过了
少年时代,母亲给高式熊买了第一个照相机——十几块钱的蔡司伊康。不久,这件宝贝被朋友借走,从此没有下落。他念念不忘,直到另一朋友买了个二手柯达照相机送他。当时,因为胶卷太贵(120胶卷每卷3.45元),有了照相机也不太玩得起。
后来,进了上海维纳氏电工器材厂,他意外发现老板也喜欢玩照相机,和自己很有共同语言。老板在静安寺开过一家雪鸿照相馆,正是他之前买照相机的店。公私合营后到了上海电影机械厂,在社会主义学校学习期间,他担任班里的文体副主任,全权负责校庆的舞台设计、请演员、拍照。
为了拍照,回厂里向组长借照相机,组长不肯,“这只机器,要500多块,不好借的!”演出照片没拍成,他发誓无论如何自己要买一个好照相机,哪怕卖掉皮袍子也要买!
1961、1962年时的月工资,只有100多元,可他花80元买了一个上海牌581型照相机。没多久,又买了个582型。后来看到南京电影机械厂出的“紫金山”照相机更好,又买了一个。这样,在照相机是绝对奢侈品的年代,他一下子拥有了三个照相机。
从此,买照相机成了一个习惯。在上海或出门,但凡看见好的名牌照相机,他就会买。收藏照相机的名声传开去,各路朋友手里有好东西,也会送上门来。最近,摄影家协会一位副主席刚刚送了一个照相机给他。“我的包里,至少要放一个照相机。莱卡我有三四个,佳能5Dmark2,日本所有的好照相机我都摸过……好照相机,可遇不可求的。”至今,他收藏的名牌照相机,数量多得连自己也说不清了。
与大藏家钱镜塘“因照”为友
1962年,西泠印社6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成立。他带了三个照相机去,120的、135的上海牌各一,还有一个双镜头的禄来牌,专门聚焦于老一代篆刻家,拍了五六十张不同角度的单人创作照。同时在场的新华社、《浙江日报》摄影记者都忙着拍主席台、拍横幅,拍大场面、拍领导,后来发稿时需要篆刻家创作照片了,只好求助于印社。高式熊就把自己拍的照片连底片都给了人家。
一次在西泠印社开会,遇见大收藏家钱镜塘,听说钱先生的藏品需要拍照。此前,是把藏品分批拿到河南中路附近的昭通路15号容新照相馆去拍的,价钱自然贵得不得了,而且珍贵文物拿进拿出很不方便,也不安全。那时候,高式熊已迷上摄影,就自告奋勇“让我来拍”。二人虽然年龄差了14岁,但非常谈得来,于是开始了合作。
因为常常有精品字画真迹可以一饱眼福,高式熊兴趣很高,有空就骑了自行车从四明村到茂名路159号钱府,有时一星期去好几趟。拍藏品要求极高,用的是俗称“大片子”的反转片,3元多一卷,只能拍八张。钱镜塘的收藏,分成各种专题系列,如八大、荷花等等,他就一个一个分门别类拍过去。
这样拍摄了整整一年。有一天,他问:“拍得差不多了吗?”钱先生笑道:“才拍了一箱。我有一房间藏品呢!”尽管1960年代圈子里都在传说 “钱先生收的东西不得了,专门雇了人管的”,但听到这一箱与一房间的说法,高式熊还是大大地吃了一惊。
于是接着拍。断断续续拍到文革来了,还没拍完,钱氏藏品到底没逃脱浩劫。
家里音响功放必须自己组装
高式熊长了一张富于雕刻感的外国人面孔,因此多次应邀客串电影、电视剧里的老外。在电影《万水千山总是情》中演一位国外摄影师,道具正是自家收藏的上世纪初产的柯达格林福照相机。
私营的维纳氏厂并入国营的电影机械厂后,小时候装过无线电的高式熊如愿成了录音机组的电讯工。当时的录音机,用的是与电影胶片一样尺寸的35毫米宽磁片,与之配套的录音,不管是原始录音还是录音棚录音,要求都相当高。试音,最常用的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与外界听到的声音根本是两个味道。录音师空着手进门,好多个喇叭同时试音,他讲得出任何一个声源出了什么问题。
每天上班,听的都是最高级的声音,耳朵听刁了,以至于后来自己家里的录音机需要5万元一套,OTL、OCL功放必须是自己组装的才能听。
电影机械厂的职业生涯,练就了高式熊对音响音质的敏感度。所以,在电视剧《一号机密》中扮演1930年代的上海爵士乐队吹奏手,对他来说小菜一碟。还有一次,在美琪大戏院听邓丽君歌曲演唱会,他乍一听就说 “有问题,音响没调好”,音响师马上跑去补救,不一会儿,一旁懂行的朋友赞叹“声音完全两样了”。
上世纪60年代练就电吉他
很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一种特别好听的乐器声音。交响乐团的朋友告诉他,那叫夏威夷吉他。隔了几天,朋友送了一把吉他上门,声明“无限期出租”,当然是有条件的——要他写一个《铜雀台赋》扇面。
他骄傲,“我的吉他老师是柳中尧先生!”柳中尧可是当年音乐界的名流,与在上海国立音专任教的音乐家黄自齐名。柳氏家族在上海建有国泰电影院。柳中尧曾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改编过国乐代表曲目《春江花月夜》。他这个连简谱都不认识的学生,买来夏威夷吉他曲子的书,与四五个同好一起学得煞是投入,课后勤于练习,进步还蛮快的。
后来,专业人士介绍他进了和平口琴会,他成了一名负责电口琴、电风琴、电吉他部分的队员,也开始接触贝司、西班牙吉他等乐器。那是1961、1962年,上海正风靡轻音乐,口琴会平时白天排练,晚上骑自行车到处演出,很多大学回荡着他们的琴声。
一次应邀在国际电影院演出,报纸预告了,票子卖完了,为满足没买到票的听众而加演了一场。还有一次是科学会堂的暑期音乐会,黑市票价翻了几倍,他这个业余选手竟与葛朝祉、周小燕等专业名家同台演出。
2006年出访洛杉矶时,高式熊说起平·克劳斯贝的某支名曲是吉他伴奏的,美国人很诧异,“你怎么会知道平·克劳斯贝?”他告诉对方,自己家里有平·克劳斯贝的唱片。他回家找出那张伴奏碟,还有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伴奏碟,“好的伴奏,有劲!听上去骨头也酥脱了!”
电影机械厂的《梁祝》伴奏带,使他悟得音乐的气势,“那是无形的气势,而公孙大娘舞剑是有形的气势。”这些,是否都潜移默化到了他的作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