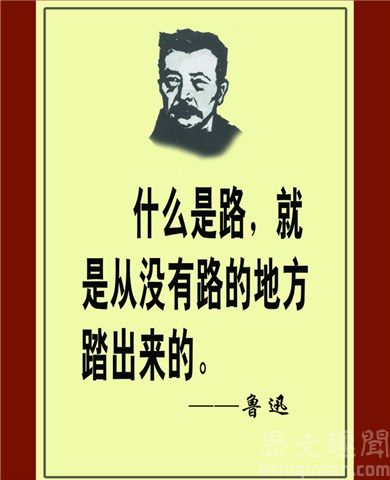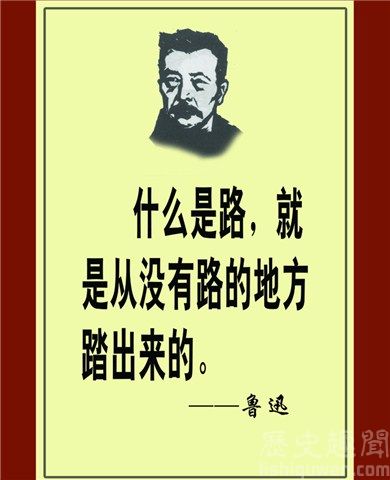福柯思想 我们过着福柯要颠覆的生活 从没让福柯变成我们思想的一部分 | 现场
尤伦斯报告厅“今日福柯”现场对谈,从左至右依次:杜小真、吴琼、汪民安
“福柯反对福柯”:反现实、反自身的思想家
一看到这个题目“今日福柯”,就想到了德里达谈保罗·德曼的《多义的记忆》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人虽远去,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注视我们”。福柯的书,他本人经历,我们一遍一遍地读,一遍一遍地回想,就会感到他正在用他的目光正在注视着我们,而且越感到有很多很多想要说的事情。
我今天有一个小题目,就是异和权力。
对“确信”的绝对否定
第一,今天回忆起福柯,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总在“变异的福柯”——他同时是一个社会活动的激进的斗士,又是一个学术殿堂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他从来没有只投身到某个单一的观念世界,也从来不只关注一个学科,只深入一种领域。
从1940年从外省来到巴黎高师,直到1984年他去世,这几十年间,福柯本人及其著作的形象从来没有固定不变。有一位哲学出身的电影人Francois Caillat,在2014年拍摄了一部哲学电影,名叫《福柯反对自已》(《Foucalt against himself》)。
我想 Caillat用这样的题目来拍福柯电影,就是要说明福柯的形象是流动的、是多变的,甚至是对立的。
因为他自己的生命活动和他的学术著作都是变动不居的,像绵延起伏的波浪,后浪推前浪,永远的向前,又像一曲交响乐,音符互相交替,奏出非常动人的乐曲,福柯在这种貌似水流的过程中不断变换自己的位置,在乐曲中调整音符。
对于我,这是福柯最让人心醉神迷的地方——他永远趋向“异”。他对于不断更新的嗜好,来源于他对“确信”的绝对否定。福柯说他是乐观主义者,而他的乐观主义在于——我可以改变的东西这么多,这些东西如此脆弱,事物更多的维系于偶然而非必然,更多地接近人的意愿,而不是理性确立的东西,更多的取决于复杂而又暂时的历史偶然,而非不可避免的人类学的恒量。
所以对于要求理解福柯及其思想的人来说,读他的书,就应该作为作者来构建书的作者。你在阅读他的书的时候,你就在构建作者,你是构建作者的作者,构建出对书的感知,所以福柯说,“我的书只不过是阅读的结果”。
因为福柯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Caillat特别指出福柯思想变动不居的过程可以用四种运动的轨迹或者说是变异的运动来说明。
这样四条运动轨迹,显示了思想家福柯的变异和改造。福柯“反自己”实际上就是他所要求的,也是他自己所思考的中心问题。
权力的派生
不断发现权力的新形式
第二,我想谈谈关于权力的派生或者权力的多样化的过程。权力问题是福柯思想中最深刻、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也是最有分量的部分。并不仅仅因为福柯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把权力当作一个研究对象,而是因为福柯是以各种各样的陈述方式提出这个问题。
所以权力的派生几乎贯穿着福柯所有的著作,而且贯穿着他从哲学到历史,从心理学到刑法等涉及的一个又一个领域。从古典时期的《疯狂史》(也译作《疯癫与文明》)到《性史》的第一卷《求知之志》,很好地说明福柯思想的异变特征。
因为《疯狂史》乍一看会把它当作一部医学著作,而如果从权力的角度看,它是一部讲如何对待疯人的实践的著作。但是归根结底,这本书是20世纪思想界对于当代社会权力运作的一种反思。
在《疯狂史》中,福柯描述的是古典时期的驱逐和排斥。它把疯子、同性恋,都置于边缘地位,古典时期的大监禁展现了否定和阴暗的力量。在常人看来,在医生看来不正常的一群人实际也是一群具有生命力的人,而他们这些人突然在厚厚的围墙之后,接受监禁甚至被遗忘。
福柯在这本书中,要把人道主义作为权力的一种新技术,把自身从承受的监禁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这种思考实际上也更新了精神病学的思考。所以他对这些监禁的思考和批判,实际上就是想指出“精神病学”这一概念需要更新。精神病学就是要用非医疗手段来记录疯人是如何形成的——也就是说,他希望从外部建立一种科学,从外部来接受对象。
福柯不断在实践或者是在思考之中,更新自己的一些反思。如果说前面《疯狂史》是“驱逐”和排斥的逻辑,那么后面在《求知之志》这本书里实际上贯穿的是“接纳”和“包容”的逻辑。福柯分析了西方的有关“性”这一概念的地位,他描写了一种发展,实际上是一种要促进权力发挥出积极一面的活动。
所以在这本书里,他也有了一些更深入的思考,他认为权力不仅仅是禁止,权力也有建构的性质。如果对1961年的《疯狂史》和1976年的《求知之志》进行比较,就很能说明福柯在权力问题上的一个思想变异的过程,也可以说是这个领域中不断改造自己的观点——不断发现权力检查机制的新形态的一种过程。所以权力在不断更新的争论中,派生出来了。
新的认识论
“断裂”、“障碍”和“不一致”
在对福柯的研究中,很多人已经谈到了这一点:福柯的思想,福柯的变异,应该放到法国新认识论的传统中去谈。从认识论的角度讲,法国20世纪的一位思想家巴什拉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注意。巴什拉在福柯的思想活动和学木都给予过很大的影响和支持,他是自然科学出身大器晚成的思想家。
法国的认识论和英美的认识论或者黑格尔传统下德国的认识论不同。在巴什拉的著作中,特别明显的是“断裂”的思想,“认识论障碍”的思想。首先,在认识过程中得出的结论,处处都有断裂的,而且都是要有更新的。
其次你不可能直接认识一个对象,一定要有一个中介,因为你一定要排除了偏见和固有的压力,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权力。第三,所谓的中介,是在科学发展到20世纪,就是很多认识对象你不能够用肉眼来认识,而是要通过间接的科学技术。
福柯继承的是这样一个东西。在认识论的过程中,福柯不是要抵达一个对象去认识,而是要给大家一个方法——也就是说我应该如何去认识,要用什么方法去认识。
在福柯之前,重要的哲学思想的形象都是建构体系或者学科,所以经常是提出概念,完善概念,要完成这样的任务,甚至到了阿尔都塞,到了布尔迪厄,到了萨特,还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这样的哲学思想形象依靠的是对理论路线和世界感知都进行“肯定”的思想。
而福柯思想给出的是另外一个形象,他的面孔是多种多样的,他的著作显示的是不一致的,但却完全不能说明形式体系结构的失败。相反,这是对归为己有、思想在其中能对自身有价值的观念进行另类的思考。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的任务不仅仅是要驱逐人们看不见的权力中掩盖着的肯定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保护一个人反抗对其成为“不一致”的压制,保护一个人“不一致”的权利,也就是把“否定”引入了自身的权利。福柯有时候说他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思想家,这是在说福柯是一个极度关怀现实的人。但他的关注现实,是不断地否定现实。
在政治领域也同样,这也是他和政治哲学理论相对立的一种思考。所以这就引出了关于知识分子任务的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是成为现在的代言人,而是要不断的构建新的政治对象,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不断地反现实、反自身的思想家。
处于法国动荡不安的政治现实以及在知识分子的活动与斗争过程中,基于自己切身的经历,福柯对知识分子任务问题的思考非常深刻。而且他还谈到,知识分子就是要陪伴这些“异”一直走下去,而且要保护这种“异”。
解放与自由
真正的自由是反抗任何压抑个体的权力
福柯独特的权力与反抗的论述,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条在认知领域的一种求知之路,这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你追求知识在认知领域是需要克服障碍的,或者说,是需要经过反抗权力这样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真知。
所以求知之路,意味着要在产生知识、冲破认识论障碍的过程中解放自己的。所以福柯曾经说过,“权力无处不在,也就是压迫无处不在,反抗就会是永恒的。”这颠覆了传统的对权力的看法。福柯特别有意义地指出,权力往往难以被意识到,它在每个个体身上都是特殊的,所以真正有效的反抗,实际上反抗的是这样的权力。或者像福柯自己所说的,反对自己的反抗。只有这样的反抗成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这让我想起法国另外一位伟大思想家,就是保罗·利科,他有一本特别著名的书《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可以说利科在这方面受到福柯的影响i。一个人要把自我当做一个他者来看待,才会产生我要认识自我的动机,而且到福柯这里,你还要呵护作为他者的自我,把它当做一个艺术品来欣尝、珍爱。
倘若你不认识自我,说认识世界,都是不可能的。所以真正的解放是个体的解放,要从你已经习以为常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当你说解放全人类的时候,要知道解放自己才是最艰难和最根本的一个解放。
归根结底,使解放成为可能的条件,就是要尊重“异”,也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过去和现在也不一样。只要是受压迫者,就是持续不断的“不一样”、“不一致”。所以尊重个体、解放个体,实际上就是尊重每个相异的个体。真正的自由是反抗任何压抑个体相异的权力,追求从这些权力压迫下解放出来。
我想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主人公伊万的话作结束:“无论事业的多么伟大,但只要是引起孩子的一滴眼泪,我就不会去做!(大意)”。这是一种人道主义,你说的天花乱坠,你的理想多么伟大,但是损害到个体,我就不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想是否可以套用这句话,对于福柯,无论你的计划多么美好,无论你的理想多么高尚,但是只要个体的“异”受到了一点权力的压迫,我也要反抗到底,而不是争取所谓的胜利。
“今天福柯拥有众多的爱慕者
但他的思想在中国依然是被流放的思想”
当我们回去看20世纪的时候,会发现20世纪的哲学和19世纪有一种不同的面貌。19世纪的哲学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不谈它讨论的问题),它是带有民族主义特色的——英国哲学、法国哲学、德国哲学,虽然有所谓的互动对话,但是各自谈论的都是在自己的问题。
但是到20世纪就会发现,实际上由德国人来提出一些“计划”,然后由法国人进行改造的施,哲学在20世纪成为一种参与到世界之中的积极力量,是法国人的革命性的一个改造,是对德意志思的革命性改造。在00年代,德国人在00年代提供的现象学,提供了精神分析,提供了萨特,这一切到40年代以后,法国人才让它们真正的开花结果。
萨特是媚俗主义的哲学家,
福柯是先知主义的哲学家
如果我们看20世纪的人文哲学的结构,会看到有三种大的类型:
第一种我把它称作“英雄主义”。比如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他们的哲学都带有很浓重的英雄主义的气质,他们要用哲学来解决哲学的理论的、思维的等一些十分关键的问题,或者说他总是想用哲学思想的世界,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或者一种全新的方向。它是一种殿堂级的,带有英雄主义气质的、很担当的一种东西。
第二种我把它称之为“先知主义”。尼采、福柯毫无疑问是20世纪先知主义的两个人物。说到这两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海德格尔不再重要。先知的哲学,它不会关注那些存在的问题,先知哲学的根本是要把我们整个的生命、生活、世界连根拔起抛向天空,而你会落在哪,那不是它关心的事情。
我觉得只有尼采、福柯,具有的这样“连根拔起”的一种力量,他们的哲学具有这样的一种效果。在福柯的凝视之下,我们都会产生一种失重感,你不知道会落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福柯的思想一定是会给我们带来那样一种震撼。在20世纪似乎我所想到的,也只有这两个人的哲学,具有这样的一种特质,当然20世纪更受公众欢迎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我把它称之为“市场主义”的。比如说20世纪下半叶,美国人制造了学术泡沫——后现代主义,彻底媚俗的一种哲学。我甚至认为萨特的哲学都带有这种特质。当巴黎刚刚解放后不久,1940年代,当萨特在一个挤满了人的会议堂,他被人举得很高抬到了讲台,然后向世人宣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人绝对是自由的,有绝对选择的自由。
所以当国家危机的时候,你是选择上前线还是选择做孝子,没有人可以干预你,没有一个道德的规则可以要求你。
”全巴黎人为之潸然泪下,为什么?所有的巴黎人在战后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道德的审判:战争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干什么?这就是媚俗。他在戳着每个人心窝子说话,然后给出一个很安慰性的话语:你是自由的,你可以在家里做孝子,你也可以去上前线。
这就是为什么当海德格尔听到法国人向他通报这样一番话时,他只是笑了一笑。所以这种哲学,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媚俗,他的话语形态,他讨论问题的姿势带有很浓的,力图去迎合公众或者是社会之趣味的特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拉康也是十分之典型的媚俗哲学。拉康的哲学是在讨好谁呢?他不是讨好公众,他是用讨好自己的方式讨好公众。就像60年代的巴黎高师人,就喜欢你说一些让我听不懂很受虐的话语,你越是那样,我越是开心。
你说60年代,福柯的《词与物》出来,有几个巴黎人看明白了吗?不会超过2个人,但是其中有一个是拉康。但是大家就是那么受虐,那就是60年代的心理特质。所以拉康就是故意制造那样一个东西,所以在这一点东西,他也是在迎合公众的,他用讨论好自己的方式来讨好他人。
这样一个定位方式是一种非理论的、非学术的一种东西。这样来定位福柯,把他放在先知主义的体系里,完全是基于一种非理论性、非哲学的,所以在学院派是不认可的。问题在当我们把福柯理论化的时候,我们能得到什么?福柯进入中国的时间其实不算短。我买第一本福柯的书时不知道福柯为何物,但是就买了,为什么?因为那本书的书名很吸引我——《性史》,80年代。他的第一本书翻译成中文,是作为一个地摊读物出现的。
福柯提供给我们一道进入现代性的目光
福柯真正进入我们视野要晚很多。但是今天,福柯在中国生根发芽了吗?他拥有众多的爱慕者,但是福柯的思想在中国依然是一个被流放的思想。这种被流放性就变得有一点点诡异——我们今天就处在福柯所揭示的那样一种社会中,我们每天还在过着福柯所要颠覆的那样一种生活,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让福柯的思想变成我们思想的一部分。
刚才杜小真老师讲了一个“福柯反对福柯”,其实那是那种思想的一种特质。在学术意义上讲,福柯在今天的中国,我认为我们对他的思想的认知、领会,还十分之浅显。我们不能把福柯只是作为一个阅读的对象,我们是要想一想福柯给我们提供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就已经可以谈论福柯的一个遗产,那么这份遗产对于我们来讲紧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所昭示出来的紧急状态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一种面对生活的立场,一道看待我们这个世界的目光。
在福柯那个地方,这一道目光贯彻始终——虽然他的眼界经常从一个地界移到另外一个地界,不断在游离,但是你会看到,福柯的写作或者思维的触角支点,都一定是落实在一个东西之上,比如说现在性的早期,16、17世纪。
因为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了今天我们说的人或者是叫主体这样一个近代的创造品,就是近代思想、近代哲学、近代知识所创造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怪胎就是“主体性”,这个主体性的东西仍然在今天主导着我们的脑袋。我们觉得能够追求达到一种主体性的自足,主体性的自由等等,就已经觉得很了不得了,就是完成了一种福柯意义上的“侏儒哲学”——侏儒才会把自己变成主体。
所以他提供给我们的目光,就是进入到现代性的一道目光,空间也好,主体之生产也好,身体也好,现代性作为一种建制,医院,监狱等等,它们同时也是一种建制的体系,所以我们会看到福柯带着对现代性的批判所走出来的路线是深刻又具有透视性的。
他还提供给我们一种技术——如何去进入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内部。德勒兹曾有一本书叫《褶皱》,那么在福柯的意义上来讲,这个世界的构成,不管是文本、语言系统、规则、建制,其实他们都是一道褶皱,所谓褶皱,不是指它们的存在形态,而是指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技术来打开我们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的各个层面呈现出来,来建立一个界面和另外一个界面之间的一种力学的体系;或者说是我们的身体在各个界面,到底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形态来展开和呈现等等。
我认为如果福柯有一种所谓的理论的话,那么这个理论一定不是概念。
什么叫权力?这样的概念并不重要,而是在权力作为我们去进入我们的这个世界的一种技术学的时候,它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启示。所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谈论一个福柯在学术上的一种价值,其实也是他提供给我们这样一种技术。
我们当然在西方的学术史上能够看到福柯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到90年代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那就是在众多的领域或学科当中,所开启的一个范式变革,方法论的一种变革,在很多很多的领域里面,他都是有一种根本性的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再重新面对福柯的时候,该思考如何让福柯嵌入到我们思维的内部。“福柯反对反对福柯”实际上是一种内在性的自我质询。所以他一定不是用一个福柯反对另外一个福柯,不是说一个早期或者说一个晚期,福柯只有一个。
他是要让我们学会有自我本身裂变的东西。福柯对于现代性的批判,也始终采取这样一种姿态。比如说他对监狱的讨论,他所指涉的现代性的社会——敞视主义社会,似乎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处在权力的监视之下。
对福柯来讲,不是政治权力,不是五环上的那个摄象头,根本的东西,是在现代性的这样一个体系,这样一个视觉建制的系统,建构了让我们每一个人学会了自己监视自己,这才是现代性的恐怖主义。
道德就是自己给自己施加的一种恐怖主义。那么社会治理、生命治理的本质就在这儿,他让我们把一种外在性,一种外在的规则内化为一个自我监视的制定,道学家把那个称之为是道德的东西。那么在福柯的意义上就是一个“非我化”的过程——把一个外在性植入到自身之内,然后把它转化为自觉的、自主的主体。
所以我觉得这是福柯的力量,有人可能会对福柯的力量感到不适,说这样一种思想,当他把我们连根拔起抛到空中的时候,不管这个种子会落在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只能处在一个失重的状态,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社会怎么办?我觉得福柯所给予我个人而言,就是这样一个晕眩感,让我在这种晕眩之中去辨别一些方向。
我热爱福柯的三个理由
刚才吴琼老师对福柯有一个定位,说福柯是一个先知。我也给福柯一个哲学定位,福柯在哲学史上,到底是什么位置呢?
谱系学的独创性:
我们如何成为此时此刻的我们
欧洲现代哲学或者说近代哲学,大体上来说有几个关键人物。第一个关键人物是17世纪的笛卡尔。笛卡尔的兴趣是什么呢?笛卡尔讨论“人是什么”,讨论普遍意义上的“人”是什么。但到了18世纪,康德是一个关键人物。他讨论这个时代是什么,这个时代的“人是什么。
他讨论的是“具体的人”是什么,讨论的是“我是谁”——就是说此时此刻的我是谁,康德把笛卡尔普遍意义上的人变成一个具体的、特殊的人,就是此时此刻生活在这个世上的这个人,他是什么?这是康德和笛卡尔的差别。
那么福柯讨论的是什么呢?福柯讨论的问题是“我是怎么形成的”。福柯不是说人的本质是什么,而是说历史是怎么一步一步把我们塑造成此时此刻的人——这就是福柯的谱系学。从古希腊开始,欧洲文化是怎样把古代人变成基督教时期的人,把基督教时期的人又变成了近代时期的人,近代时期的人又如何变成今天的人?今天的人在欧洲是怎样一步一步被塑造而成的?我觉得这是福柯的问题,是福柯的特殊之处。
第一种是排斥的方式。就是说,我要成为我这样的人/获得我的主体性,我就要把跟我相对立的或者不一样的人排斥出去,把他们隔离出去,把他们囚禁起来,我通过隔绝和排斥他人的方式来获得自己的主体性。比如理性人把疯子关起来,还有守法的人,把犯人给关起来,异性恋把同性恋排斥出去,等等。
第二种形成主体的方式,是通过知识和学科来勾勒出人的形象。这是《词与物》的主题。就是说“人的概念”,“人的知识”或者我们“现代人的形象”——我们所谓的的人道主义,我们所赋予人的各种各样的想象,各种各样的知识——是通过各种学科构造出来的。
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的诞生。古希腊没有这样的人的概念,中世纪没有这种概念,甚至17世纪、18世纪也没有这样的概念,只是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期的时候,才出现我们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概念。
经济学、生物学、语言学,这些学科的不断发展,才创造出了一种有关人的概念,这就是福柯所说的主体的知识形象。但是,从尼采开始,这样的一个人的知识构想就开始坍塌了——福柯接着尼采说出了“人之死”。
第三种塑造主体的方式,是自己来塑造自己。福柯在这里面主要是讲古希腊人的自我技术,希腊人是反复的塑造自己,他们反复地把自己当作一个对象来塑造,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自我修炼,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主体。
福柯主要是讲西方历史,就是说欧洲文明史上,存在着这几种塑造主体的方式。而且他以谱系学的方式追根索源: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这些方式是如何变化的?排斥的历史,自我修炼的历史,人文学科的历史,这几种塑造主体的历史是如何变化的?这就是福柯的主题,也是福柯的独特之处:人是怎样变成自己的?
写作风格的独创性:
每一部著作都是一部不可复制的艺术品
福柯第二个有魅力的地方,是他的写作方式。如果读过福柯的书,你会发现福柯的写作是前无古人的。福柯在某种意义上,既是一个哲学家,又是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作家。但没有一个哲学家、历史学家或作家是这么写作的。
福柯是创造性的写作——没有人像他那样写疯子的历史,性的历史和监狱的历史。他的这些书的形式,也跟传统的著作完全不一样。他是以否定哲学的方式而出现的哲学家形象。他也是以否定历史的方式而出现的史学家的形象。
福柯的著作非常具有感染力,非常形象化,非常具有叙事性和戏剧感,最重要的是,他的著作充满诗意。他不可思议地将语言的美妙和严谨结合得如此之完备,这也是福柯能够有众多读者的原因。福柯自己也说,他受影响的一些思想家,喜欢的一些哲学家,都是作家兼哲学家。他喜欢尼采,喜欢巴塔耶,布朗肖和克罗索夫斯基,他们都是作家兼哲学家。我们在西方哲学史上看不到福柯这样的形象。他的主题独特,表述独特,思路独特。
福柯另一个特点,就是他写每一本书,使用的都是不一样的语言。每本书都不重复,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作品。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艺术品。如果抹掉作者名,《词与物》和《疯癫与文明》,你完全不会相信是同一个作者写的。它们讨论的对象差别如此之大,完全没有任何的连续性。
就语言本身而言,福柯早期非常华丽,非常辛辣、富有激情,令人眩晕。但是我们看他晚期的著作非常平实、非常优雅,毫无早期的抒情性,看上去像是一个古典作家写的优雅散文。
而《规训与惩罚》则将早期的华丽和晚期的优雅结合起来,那本书既充满激情,又异常地冷静。你能在书中看到他的怒火,但是又能看到这种怒火被克制,看到他的隐忍。他甚至每一本书的构思方式也不一样。像《知识考古学》,完全是思辨性的,这本最接近西方哲学传统的哲学书,就像一个迷宫一样,几乎没有什么材料,没有什么注释,看不到什么思想来源,像是自己在构造自己。
而《规训与惩罚》则全部是档案,是完全没有人看过的监狱档案,所有的论点全部建立在档案和材料的基础上——他可以通过细致具体的材料来思考,也可以抛弃任何具体材料来思考。
我们要说,福柯的写作方式非常迷人。没有一个人像他那么写作。所以他的著作,开始是在学院里面受排斥的,这是不同于学院的写作,但是今天的学院已经完全接纳了福柯,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福柯占领了学院。
尤其是在美国的大学。学院接纳了福柯,但是学院永远无法模仿福柯,学院无法像福柯这样写作,他就像一个奇迹一般突然降临到大学里面,大学受了他很大的影响,但是大学永远达不到他的高度。
有血有肉的人:
“既不要怕活着,也不要怕死亡”
我要讲的第三点是,福柯的魅力在于他的人格。福柯这个人本身非常有意思。我只是简单说他几个特点,我所了解的几个特点:
福柯是1984年去世的。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主题是说真话,或许是巧合,“说真话”是他最后的讲座。实际上,“说真话”这三个字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要保持说真话是非常难的。福柯分析的是希腊人的“说真话”,我想,这或许也是福柯的自我要求,到底什么是说真话呢?“说真话”对福柯来讲有这么几个特点:
福柯为什么在他临死前讲这些问题呢?或许,他在暗中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是讲真话。福柯的写作,就是在讲真话,他没有写任何恭维性的东西,他一直是对权力进行分析,一直是向权力说不。
他不仅在理论上讨伐权力,在现实中,他一直处在社会运动的中心。他有好几次直面警察这个国家机器,同他们徒手战斗。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个战士。所以这个人本身是非常有意思的人。
最后我要讲一个小故事。我每次在课堂上讲福柯的时候,都会将这个故事讲给学生听。福柯在美国讲学的时候,每个礼拜四都是接待学生日。有一天一个学生去找他,敲响了福柯办公室的门,学生进来之后就坐在福柯的面前,忐忑不安,因为见到大师了,见到了当代的苏格拉底。
福柯一看,就知道这个学生是同性恋,因为福柯自己是同性恋。福柯让他放松下来,跟他慢慢聊天。讲了很长时间。下班的时候,两人一起去坐地铁。这个学生走在路上完全打开他的心扉,他开始跟福柯讲他内心一些焦虑,说他喜欢文学,喜欢艺术,但是他的父母希望他有一份正当的职业,比如说干律师或者搞金融,因为艺术家基本上属于那种没有前途的职业。
所以他很困惑,他想在哲学家这里找到答案,怎么办?福柯到了地铁口的时候,只是非常简单地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充满勇气,不要害怕——既不要怕活着,也不要怕死亡。然后福柯拍了拍他的肩膀,就下去坐地铁了。
我当时看到这个情节,我也非常感动:不要怕,既不要怕活着,也不要怕死亡。是的,有什么好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