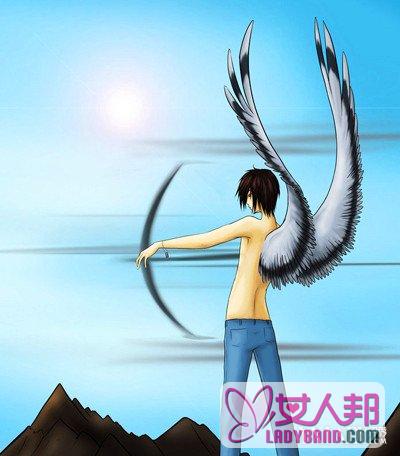朱天文暗恋侯孝贤 专访编剧朱天文:侯孝贤那些最美的影片 他都是用说的
“与其说时代在影响我们,不如说被吸收消化于我们内在的时间节奏里,我自有我的生命步伐。个体创作者与时代之间,我以为是冷却一点的好,若即若离,或至少‘热眼’旁观。”(图:作家朱天文已和侯孝贤合作了 30 余年,她说因为侯孝贤找不到其他“对手”,所以每次只好由她上场)
《刺客聂隐娘》的编剧共有四位,分别是朱天文、钟阿城、侯孝贤和谢海盟。居首的作家朱天文已与导演侯孝贤合作了超过 30 年。 朱天文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述过她担任侯孝贤编剧的缘起,那是 1982 年,她的短篇小说《小毕的故事》发表于《联合报》,侯孝贤透过导演陈坤厚来买改编版权,约在“明星咖啡馆”会谈。
朱天文对侯孝贤的第一印象是:“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个小鬼呀,很草莽气,就是从城隍庙里混出来的。”两人自《小毕的故事》开始合作,当时是陈坤厚做导演,朱天文、侯孝贤任编剧,之后的《风柜来的人》开启了侯孝贤任导演、朱天文任编剧的模式,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2010 年,朱天文来上海参加书展,透露侯孝贤的电影《刺客聂隐娘》的剧本已进展至“一稿”阶段,她还将为侯孝贤执笔比喻成“打球”:作为侯孝贤的一个敌手,发球、接球,陪他练习打球。
而现在已是五年后,朱天文回忆起来一阵唏嘘,当时所谓的“一稿”也只是“捕风捉影”,她告诉记者:“那一年十月,侯孝贤还去往日本奈良,按妻夫木聪给的档期先拍了他的回忆戏,把他跟妻子忽那汐里从相识、结婚到上遣唐船分别时妻为他舞一段莺舞的段落,都拍全了,本想留待日后剪辑时再看,结果自然是用不上了。
” 用不上的部分还有许多。朱天文说她作为编剧,关注的是思路的辩证,在她看来,《刺客聂隐娘》的核心问题是“凭什么可以杀人?”为此她努力建立诸般理由。但见到影片时,她所写的关于核心问题的几场重头戏全部被拿掉了,而侯孝贤的回应是“看着不像”、“没办法剪不进去”…… “我老觉得是个梦,几无实现的可能。
”朱天文在三十年前就听侯孝贤谈论聂隐娘的故事,之后隔几年就会重提,直到 2000 年才有了一点眉目,做了一份企划案找投资,而后又是搁置,待 2009 年才开始剧本讨论,剧本先后写了 38 个版本。
2012 年 9 月底开机,耗时三年。“如今拍成了,不出所料,剧本和电影,基本上是两部完全不同的片子。” “我身处文字的这方,对我来说,侯孝贤的影片最美的时候,都是在拍摄前的讨论阶段。
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彻底地爬梳他的想象世界的内部……但在拍摄时,总是会出现一些现实无法克服的问题,影片的最终呈现总是让我强烈地感觉它已经失去原本应有的活力。”在傅东(Jean-Michel Froden)那本关于侯孝贤的专著中,朱天文这样讲述她和侯孝贤的工作方式,她说:“那些侯孝贤最美的影片,他都是用说的。”
B=《外滩画报》 Z=朱天文
B:你会怎样形容你每次与侯孝贤导演合作的状态? Z:剧本讨论阶段,那是真正创作的时候最快乐。但多年来,我已世故到几近虚无的理解,由于现实条件限制,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影片拍摄永远是一次七折八扣的执行过程,最后看片我常常很失望。
B:唐传奇中的聂隐娘的故事只有千余字,从之前媒体报道而知电影中似乎“聂隐娘刺杀节度使田季安”这一主要故事线索是完全杜撰出来的。当时为何会想到以这个事件作为主要叙事线索呢? Z:这篇唐传奇小说写到的人物有“聂隐娘,魏博大将聂锋之女”,有“魏帅”,有“陈许节度使刘悟”,时间上有“贞元”,有“元和”,便根据这现有的路线找进去,按新旧《唐书》、《资治通鉴》,找出魏帅即当时的魏博藩镇节度使田季安。
小说里聂隐娘帮助陈许节度使对付魏帅的追杀,便发展成聂隐娘刺杀魏帅田季安。 B:嘉诚公主、嘉信公主、瑚姬、田兴、负镜少年和采药老者,这些人物从何而来?这些人物是剧本创作中陆续增加出来的吗? Z:负镜少年,背着铜镜的少年,在小说里叫“磨镜少年”,以磨镜即淬镜为业。
田兴在唐书里有被提到,他是田季安的堂叔,甚得民心;田季安想整他,他就假装中风,因此保住了性命;田季安一死,众人即推田兴继任魏博节度使,他完全是朝廷派,对长安很忠诚的。
嘉诚公主根据史书,下嫁田季安的父亲田绪,类似和番,是为了羁抚魏博;嘉诚收庶出的田季安为己子,田季安很敬畏她。至于把小说里的尼姑改为道姑,设定为嘉信公主与嘉诚公主成了双胞,以及田季安的宠妾瑚姬,还有跟负镜少年同行的采药老者,这三位是创作出来的人物。
B:作为侯孝贤导演的编剧,你们之间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Z:侯孝贤永远是发动者,他只能拍他的脑中物,那种很多剧本排队等着他读他选他拍的事,从来也没发生的,他就是他自己的编剧。
通常,他都是先有人即先有演员才接着有故事,他无法凭空去编织一个剧情。就说聂隐娘,是因为眼前有舒淇,才有想头,否则一切白搭。先是有很长时间的剧本讨论,差不多了侯导就把纸上作业扔给我,他迫不及待要去勘景勘现场。
没错,剧本是写给剧组去执行摄务用的。 B:《刺客聂隐娘》田野调查的逻辑脉络是怎样的? Z:田野调查只有一个方法:跑野马。凡有关于唐朝的史料,能看到的就尽量看,这类书包括讲官制的、驿站交通系统的、节气行事历的、各种文物画册……多到不行,只怕你懒不看。
事实上,侯导是 2008 年开始专注看资料的,从各史实年代中卡出一个足够放入《刺客聂隐娘》故事结构的空间,一年的单人作业;等到我跟海盟加入,便是把他手上的基础材料先看完才进入状况,一起剧本讨论。
B:你们编剧也一起勘景,唐代木结构建筑目前保留下来其实并不多,山西和奈良,你们都去看了吗? Z:你得去问我们的美术设计、服装设计黄文英,她那里东西可多了。
至于奈良,我 23 岁跟胡兰成老师去看过唐招提寺、法隆寺之后,每隔几年总会再去像拜访一个老朋友。 B:这次拍《刺客聂隐娘》,是如何让演员进入唐朝的时空的? Z:这次很难,侯导说了不知多少次,恨不得有一个时间机器回到唐朝。
侯导就像巫师,催眠演员进入唐的想象共同体。 B:你在《炎夏之都》的序言中也写过,“电影永远是导演的,编剧无份”。那时你从事电影编剧刚 4 年多,而现在你和侯孝贤导演合作了 30 余年,是什么原因让你愿意一次次为他的电影暂时搁下自己的写作? Z:如果将剧本讨论看作是侯导练球,那他必定需要一个能够陪打的;但他又找不到对手,就只能每次都由我上场了。
B:你最喜欢的自己的编剧作品有哪些? Z:《戏梦人生》、《南国再见,南国》、《刺客聂隐娘》。 B:你曾说《戏梦人生》是侯孝贤导演生涯中的一次巅峰,那时还未有《刺客聂隐娘》,现在《刺客聂隐娘》拍完了,它可能的位置是什么? Z:侯导上一部片子《红气球》是 2007 年拍的,8 年后才出《刺客聂隐娘》。
如果他准备未来再拍 10 年的话,我觉得拍这部电影就像做了一次大规模的盘整,预备再出发。
B:你觉得侯孝贤拍《刺客聂隐娘》对于当下有没有什么意义? Z: 以前侯导没说过,这次却说“现在没有人这样拍电影了” 。这部电影对于当下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它是一次展示,展示一种削去法的美,静谧,能量与素朴的善意。
对比我们闹哄哄的当下,它是另一个参照系统。 B:你曾形容,对于侯孝贤,你相当于一个“秘书”。工作之外呢?你们是怎样的一种朋友? Z:诤友。侯孝贤说我和朱天心手上拿着鞭子,我们姐妹好严厉的。
B:那侯孝贤在工作和私下是否差别还挺大的? Z:一个样,只是越老越心软。 B:编剧工作,对于你自己的写作是否有一些影响?比如在叙事上? Z:就创作而言,编剧工作于我是身外物,至少从结果来看。
我上一部长篇小说《巫言》,简直是零叙事。 B: 现在距当年侯孝贤、杨德昌等台湾导演拉开“台湾电影新浪潮”运动有 30 年左右了,时代的骤变对于你和侯孝贤导演的创作有影响吗?你是如何理解个体创作者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的? Z:与其说时代在影响我们,不如说被吸收消化于我们内在的时间节奏里,我自有我的生命步伐。个体创作者与时代之间,我以为是冷却一点的好,若即若离,或至少“热眼”旁观。










![【12星座谁会暗恋巨蟹座】[12星座谁会暗恋巨蟹座]12星座会暗恋哪个星座](https://pic.bilezu.com/upload/8/10/810322f92e8dabe0e41ad7c69f875f7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