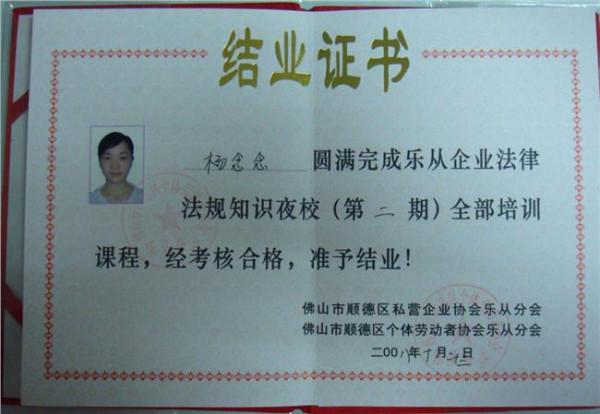梭罗名句 宋黎:功利的反面与功名的反面——大卫·梭罗的田园与陶渊明的田园
大卫·梭罗和陶渊明,虽然相隔千年文明史和万里太平洋,操不同语言有不同信仰,但这两个名字放在一起大多数人还是能立即找到之间的交集——两位都主动把自己的生命放低,低到了田园,再从田园里开出了明净的文学之花,联手为东西方文明拓出一片宁静澄明之境,千百年以后还能为奔走红尘中的后人提供心灵的滋养和慰藉。
很多现代作家也将二人共置笔端,视二者为一脉相承花开两朵,虽各表东西,但无论从精神内核和对世人的影响都如出一源。
在小资文化盛行的前几年,“带一本《瓦尔登湖》去马尔代夫的沙滩”,“在星巴克点一杯拿铁,摊开《瓦尔登湖》,窗外的雨,还在继续”……诸如这样的文字一时四起,更将《瓦尔登湖》的知名度推到似乎超越陶渊明的程度。
但是,一个大家可能不太愿意提及的事实是: 实际上真正发自内心欣赏喜欢《瓦尔登湖》的中国人为数不多,大多数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评价明显逊于其在本土收到的赞誉,甚至很多人表示“这本书很平淡、啰嗦”(当然,迫于“经典”二字的压力,这种评论往往不大容易以文字形式出现在印刷物中,大都是在私下交流中透露出来),北大孔庆东教授更是直白的说:“其实俺看这书写得颇一般,跟陶渊明比是天壤之别”(孔庆东《千夫所指》)。
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中国读者对梭罗的认可程度远不及陶渊明?
首当其冲的原因毫无疑问是翻译问题,尤其是对于《瓦尔登湖》这类主要靠文字走笔白描制造意境进而呈现思想、基本没有故事情节也缺乏推理、论说性观点的文集来说尤其如此,它的价值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字句的吸引力。英文原文中行云流水沁人心脾的句子翻译过来很多时候便成了一个文艺范的老奶奶自言自语的唠叨。
这种落差与译者的水平关系不大。再高明的译者,只要头顶着“忠于原著”的原则,就难免把翻译变成弃其神而存其形的劳动。翻译问题应该是共识,不必赘言,这里主要谈的是另外一个原因。
陶渊明和梭罗在精神取向上是一致的,都爱好自然崇尚自由,两人笔下的田园风物也都散发着同样清新朴素的宜人之风。但如果我们把目光慢慢移开,移向田园的对立面,会发现这两个田园的反面因为两人所处语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正如本文标题所示,陶渊明田园的对立面是“功名”二字,而梭罗田园的对立面是“功利”二字。这得从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即促使二人归隐的原因)来理解。
陶渊明归隐前所处的是封建的官僚社会,官场仕途的黑暗与压抑犹如一个肮脏的“樊笼”,禁锢着为追求功名而身陷其中的仕子,让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受到污染和挤压。在世俗功名与人格的保全之间,往往只能是一道单选题。
陶渊明在“误入尘网”浅尝了个中滋味后,毅然选择了“不为五斗米折腰”,退出了仕途追逐,逃禄而归耕。与陶渊明不同,大卫·梭罗生活在金钱至上的商业时代,整个社会被强大的逐利逻辑推动着前进,像一个飞速旋转的大转盘,让头脑被功利思想主宰的人们奔忙、迷失,心灵被转盘扬起的阵阵尘埃所遮蔽。
梭罗的归隐主要是出于对这种舍本逐末的生活方式的反感和厌恶,所以即便是归隐在自己的木屋内,梭罗还不时发出“为什么我们要生活得如此匆忙,这样浪费生命呢?”(《瓦尔登湖·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而活》)这样的感叹。
同样也因为如此,在《瓦尔登湖》(戴欢翻译版)的前言,译者借用Walter Harding的话说:《瓦尔登湖》“是向金钱社会讨伐的檄文”。
两位作家所处的环境不同,但如果要分一个高下好坏的话,我们还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梭罗生活的时代要明显优于陶渊明的时代。其优劣主要不在于生产力,而在于人的自由度。陶渊明所处的封建社会给他留下的生活选择,除了自己耕作以外,几乎就只有仕途这一条路;更可怕的是,这唯一的一条路却与他本人的精神追求与道德要求剧烈冲突,如果坚持仕途,就意味着放弃自我。
可以说,陶渊明的归隐是被社会逼上了绝路。而梭罗虽然不满商业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但是其人生发展的自由度却要开阔得多,事实上,梭罗在隐居前也当过教师(应该说是校长)、在自家的铅笔厂里面工作,如果本人愿意,他完全可以在享有高度人格自由的基础上自在惬意地经营自己的事业和生活,隐居并非是唯一的选择。
概括来说,陶渊明的归隐是为了守住自己的人格底线,是被环境所逼迫;而梭罗的归隐是为了“使他的行为与他自己的信仰协调”,是被理想所召唤。
有了上述对两个田园反面的了解,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孔庆东老师的“跟陶渊明比是天壤之别”论了(其实这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大家暗地里庆幸找到了有话语权的代言人)。
首先,社会处境的共通使得陶渊明作品更能暗合中国读者的心灵结构,更能引发共鸣和体认。
时移世易,千年以后中国政治环境与陶公所处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站高了看,我们似乎仍处在同一个轮回里,社会生活中体制性的禁锢仍旧林立,道德观和价值观依然时时受到挑战,保全人格和实现世俗成功之间往往还是难以两全,我们不过是从一个小的樊笼换到一个大的、设施升级的樊笼。
共通的生存环境让中国的读者在陶渊明的悲喜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找到更多值得回味和把玩的思想和情愫。于是我们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中听到自己的叹息;从“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读出自己仰慕但或许已经丧失的气节;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中找到了坚定自己价值观的勇气。
当然,西方的读者或许更欣赏的是《瓦尔登湖》中“无论人们的双腿如何勤奋努力都无法使人们的心灵更加靠近(no exertion of the legs can bring two minds much nearer to one another)”——这样的句子固然也能触动中国读者的心弦,但不是最容易被触动、最需要被触动的那根。
个体对自由的追求与社会体制高墙之间的碰撞是中国人心理中最需要被回应的声响。梭罗所处的时代由于没有这堵高墙的存在从而失去了碰撞所发出的声响,中国读者也就在这方面找不到回响,所以难以共鸣和认同。
其次,如前所述,陶渊明比梭罗所处的社会环境恶劣许多,陶渊明从中体会到的痛苦也深远得多(许多人认为陶渊明其实没有经受多大苦难,其十几年的仕途虽未飞黄腾达但也从未有过牢狱之灾、性命攸关的大难。这是事实,但是,陶渊明虽然没有经历太多个体苦难,但那个时代的群体苦难却是深重浩荡无孔不入的,作为大众的一份子,对敏感又有道德正义感的陶渊明来说,这种集体的苦难也会对他造成深深的痛苦)。
而痛苦被公认为是哲学的源泉(之一),从而使得陶渊明的作品较之《瓦尔登湖》更具哲理和深度。
可贵的是,这种来源于痛苦的哲理深度主要还不是直接作为呻吟和控诉反映在陶渊明的文字中,而是经过诗人的接纳和消化,化做了另一个方向的精神向度——超脱。例如,在从衣食无忧的官位退到温饱堪忧的田园里,巨大的落差没有催生出诗人的得失心,反而“忘怀得失,以此自终”;面对生死问题时,看惯官场生死无常的陶渊明也是“死去何所道,托体共山阿”;而我们耳熟能详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更是陶渊明本人闲适旷达形象的直接写照。
在《瓦尔登湖》中,我们很难见到这种对苦难的超越,而更多的是听见梭罗对世俗生活的不屑和愤懑。那是因为生活没有给与梭罗太深的痛苦,只给了他一些反感和不解。小的悲喜容易宣泄成愤懑,而大悲之后往往会带来大悟,痛苦的深度决定了作品的深度。我们可以这样比方:梭罗的田园是世俗生活的对面;而桃园明的田园不仅在世俗生活的对面,而且还在世俗生活的上面。
此外,由于陶渊明是被社会逼上了绝路,所以他的归隐显得更加坚决彻底,心无旁骛地全身心拥抱田园,直到终老。田园生活与诗人以及诗人的作品完美的融合,浑然天成。而归隐对于梭罗而言并非唯一的选择,而更像是带有实验性质的生活体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行为艺术。
梭罗希望通过此举来声张自己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同时也为迷茫的人们昭示一种更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存在,田园对于梭罗来说并不是他的归宿。梭罗的写作除了与自己心灵对话外,更多的是为了反衬出世俗生活种种的盲点和症结,少了陶渊明那种将自己彻底交付给山间水边的皈依感。梭罗本人仅仅隐居两年后便又重返文明社会的事实也为此提供了佐证。
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梭罗像陶渊明一样终老田园埋骨乡间,大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陶渊明的田园四周被黑暗的政治黑洞笼罩,再艰难也只能坚守,他是回不去的;万里之外,梭罗坐在小屋内,点燃了自己昨天刚劈好的白松木,借着火光遥想那繁华世事。虽然金钱的车轮撩起黄尘滚滚铜臭弥漫,但捏一捏鼻子,发两句牢骚,抬头看看星空,低头经营好自己的事业,这个世界也并不是那么不堪。
归根到底,他们各自田园的反面是不同的。你南山种豆,我湖畔伐薪,一样的生活,映衬在不同的背景下,还是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剪影。站到了对面,才能更好的看清楚正面。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关于二人明显厚此薄彼的对比仅仅是从一个中国读者的角度来阐述自己的理解,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必然存在高下之分,只能说明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血缘关系。我们拿着不同的管子窥见不同的豹纹。我敢肯定,如果美国的某个读者来写同一主题的话,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这也是我们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