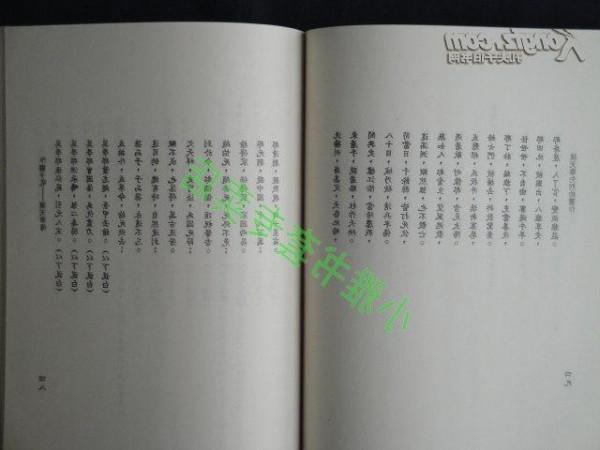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的修辞与学理
[少华按:这是本人最近发表在《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3期上的论文,原题《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的修辞与学理》。在这里删节刊登。这是我近年来在修辞分析基础上对这篇广为传诵的名文的一种尝试性的深度阐释。]
“少年中国”是梁启超在他的著名政论《少年中国说》中创造一个富有活力的修辞。这个生动的意象有利于提振中国人对于国家前途的信心,因此广为流传。本文通过对梁启超当年所接受的西方思想资源的考察,认为: “少年中国”这一创造性修辞的学理背景是当时他所接受的一种西方国家理论——国家有机体论。并由此探讨创造性语汇产生、传播的机制。
一、“少年中国说”的影响和本文的研究思路
《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一篇传播甚广的名文,被学者称为梁启超“新文体”的典型作品。(陈玉申,2003:132)这篇文章不仅以汪洋恣肆的文笔营造了鼓舞民族自信心的意境,推出了“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等传颂久远的励志名句,而且创造了“少年中国”这样一个崭新的意象。而在学术研究中,着眼于它的表达效率和论证逻辑,对于这篇文章,则有和其在大众传播中的效果相反的评价。
有学者认为“此文不但以思想新颖警辟取胜,且亦以文辞美取胜,然仍不脱对文言形式美追求和框子。但这是一种在平易畅达的基础上,熔冶古文、骈文、散文、韵文、雅言、俗语的自由放纵的文辞美,梁氏此类文可看作是我国古典文章审美特性的终结。”(程福宁,1996:178)但也有学者认为:“造成中国日趋腐朽的原因何在?创造少年中国的道路何在?不管正确与否,梁启超在文章里都没有论述清楚,全文只是泛泛而谈,为了说明少年人胜过老年人,把老年人贬得一无是处,甚至把老年人比为‘瘠牛’、‘鸦片烟’,完全成了社会废物,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文章中,一句话可以说清的意思,用七八句、十几句话,显得拖沓。”(李良荣,2002:34)
尽管从风格和逻辑的角度对此文有不同的评价,但百余年来,这篇文章创造的“少年中国”的修辞和意象却似乎超越了对一篇文章的评价,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这可能是因为它在那个中国积贫积弱时代为提振民族自信心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和语汇。所以,从传播史的角度看,这个新鲜的修辞和意象被创造出来,就得到了广泛传播。
比如,1906年春节期间(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四),《申报》发表论说《论今年之希望》,其中开篇提到“人当少年之时,前途之希望多”,文中又有“到至老大之国则奄奄一息,回顾已往之事,多阅一年历史,则多受一年之屈辱。”文末则言“可预决我少年中国之国民于今年前途之希望若是其多。”——这完全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语汇和观念。出版于1908 年的理想小说《新纪元》(第一回)描绘1999年的中国,其中说到:“这个少年新中国,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在201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一个叫做“少年中国”武术节目中,朗诵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片段。“少年中国”在网上遂成一“推荐热词”。
那么,这个修辞和意象是如何产生的呢?
本文假定,在观点传播中的创造性因素并非偶然产生,而是在相应的思想资源和词语资源的条件下,在具有创造力的人的头脑里产生。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和宣传鼓动家来说,他的思想资源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各种思想理论。他接触这些思想资源,主要是在流亡日本期间,(石云艳:2005:275)在编辑出版《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和为这些刊物写作期间。他在宣传鼓动的写作中的创造性表达所依赖的资源,也应该在这一时期他所接触到的思想资源之中,在他的广泛涉猎和学术研究之中。实际上,他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和宣传鼓动活动是融会在一起的。
本文试图将《少年中国说》放回到它所处的思想环境和传播环境之中,在这个环境中解释“少年中国”这个传播甚广的创造性意象产生的条件与资源,以此探索在大众传播中有生命力的创造性词语的产生机制。
二、“少年中国”的修辞与论证
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第四《〈清议报〉之性质》中列举本报文章时提到代表本报各种特点的一些文章,提及“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
由此可见,梁启超是把《少年中国说》当代文体创新的典型作品的,同时也是把它当作直接面对大众鼓动民气的作品的。与此相同功能的,还有《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其文本特点可资印证。这大致确定了“新文体”的基本特征和范围。也大致显示了新文体与鼓动民气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梁启超并非所有的文章都是“新文体”,而只是在鼓动民气的文章中尝试这种文体,因为这种新文体的风格,特别适合于鼓动民气。
这篇文章,原载1900年1月10日第35册《清议报》,属于典型的“报章文学”,有的文章学家称其为“新体古文的一个变种”(佐藤一郎,1996:267)“全文采用工整的对仗,重叠排比,层层推进,感情的奔驶犹如长江三峡之水,一泻千里,有强烈的感染力,读了催人泪下。”李良荣(2002:34页)指出它的核心观点是反驳日本人说中国是“老大帝国”的说法,而提出“少年中国”的观念。文章从“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展开议论和论证。但从逻辑上看,“国之老少”与“人之老少”并没有可比性。实际上,“老少”是指人的生命周期。“国之老少”只是一种拟人化的比喻。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应该从国家的文化历史资源和当代物质资源、制度资源,以及人民的创造力方面进行论证,不能只从“老少”这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单独推导出来。
对此,已有学者(单正平,2006:116)指出:“这个奇妙的‘返老还童’逻辑,当然不可能有真正的说服力。但梁启超借助他充满激情、具有‘魔力’的文字,确能使其无理的方案具有相当的感染力。”
实际上,“国之老少”这个修辞化的表达在认识上和逻辑上根本的局限性,正如鲍桑葵在评价思想史中人们将生物学知识用于社会理论和国家理论(社会进化论和国家有机体论)的局限一样,是“用比较低级的现象去阐明比较高级的现象”(鲍桑葵,1995:60)。
但是,梁启超不仅在“人之老少”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词汇铺排,即使是在论证“国之老少”时,也仍然按照人的生命周期,推出“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这样一个与当时人们的实际经验不能符合,但却鼓舞人心的结论。
那么,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老大”的标准是什么,“少年”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梁启超在文章中要回答的问题,也是这篇文章中议论性和论证性的内容。梁启超在文中第一次提出“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这个问题之后首先作了一个今昔对比:
“ 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煊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
以下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来论证这个“颓然老矣”。显然,这个标准是流行标准,它接近于人们的经验。但这正是梁启超所要否定的标准。果然,他接下来就提出新的判断标准:
“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
这其实是一个近代国家的标准。梁启超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清末的中国,自然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立之国”。由此推导出“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的结论。
在这种以抽象标准推理产生的结论之上,梁启超还为“少年中国”赋予了形象感,如:“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欧西、日本人谓我老大何也?”
这是梁启超把一套抽象的国家理论转换成一个形象化的修辞的技巧。但是,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他回避了国家的发展周期(如果有的话)与人的生命周期是不同的。一个数千年古国政治体制的“落后”本身,并不意味着未成年的人体所孕含的生机。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彼时的梁启超正如饥似渴地接受西方政治理论,尤其是国家理论,那么,这一切就可以理解了。实际上,即使是当代西政治学者,也有人认为,“事实上,国家是一种相对新近的政治组织形式创新。……国家开始形成于中世纪后期(约500-1350)。”(约翰?鲁尔克,2012:187)。当然,这明显是以西方历史为背景的标准。彼时的梁启超事实上也正是接受了西方的国家标准。
然而,从接受心理的角度说,谁的国家标准并非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篇鼓舞人心的文章,这样一个从西方国家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少年中国”的结论非常符合彼时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内心期待和受挫之后急于重振的自信心。
从思想资源的角度来说,梁启超之所以选择用人的生长周期来比喻国家的发展程度,并非偶然,也并非仅仅缘于修辞的传统,而是因为梁启超在当时接受了一套被称作国家有机体论的国家理论。“国家有机体说者,谓以科学上有机物之理,解说国家之本体及生活状态之学说也。其大旨谓国家以一种有机体,浑然成为个体而生活……据有机物而求其学者云者。” (稻田周之助,1913)
可以说,《少年中国说》的写作特色,就是学理与修辞的结合。或者说,为梁启超所创造的“少年中国”这个有着极大传播力的积极的意象本身,就是建立在学理上的一个修辞。其中的学理,就是国家有机体论;其中的修辞,就是把国家比喻为人体。其实,国家有机体论这个学理本身,就是修辞化的理论表达。“少年中国”之“说”,实际上是通过一套从学理到修辞的转换,包括通过一般人难以察觉的偷换概念,来完成了一个具有宣传鼓动功能的意向。因为,这篇文章面对的受众并非是学理探索的交流对象,而是更广泛的普通大众。
三、“少年中国说”的思想资源
在梁启超的早期作品中,也有一些对国家的比喻。如他在戊戌变法时期所作的《变法通议》(1896)中《论不变法之害》一篇,就把国家比喻为一座“更历千岁”的“巨厦”。这个喻体,选择的是“无机物”。
而如果把《少年中国说》放回到它发表的刊物《清议报》的思想环境中,就不难理解“少年中国”的修辞与国家有机体论的关联了。这主要是来自德国学者伯伦知理的影响。“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对他思想影响最深的要数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郑匡民,2003:281页)
《少年中国说》作为“本馆论说”刊载于1900年1月31日第三十五册《清议报》。而自《清议报》自1899年4月10日出版的第十一册起,便开始连载德国伯伦知理著《国家论》卷一。其中就有“国犹身也”、“国家者,国民之形体也”这样对国家的修辞。
有学者概括说:“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论,是将自然科学上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国家关系上,而将国家比成人体的一种理论”。(郑匡民,2003:260。《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
梁启超接受这种国家理论并非偶然,“伯伦知理的这种主张,能在限制皇权的同时又能对人民做出让步,同时也很容易集权力于中央,以便与帝国主义竞争,而这一切又都同梁启超的政治理想吻合,所以梁启超当时就很自然地接受了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伯伦知理的这一理论对梁启超的影响极深,它进入了梁启超思想基础的‘知层’,以致梁启超在很多文章中都继续坚持国家有机体论的观点。”(郑匡民,2003:261)
自然,除了伯伦知理的国家主义内涵与梁启超的政治理想比较接近之外,这种理论的修辞化表述,以及梁启超对这类修辞化表达特别敏感,则是梁启超在国家有机论的“基本修辞”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创造出“少年中国说”的一个原因。
而就在1899年4月1日的第十册,由梁启超所作的“本馆论说”《商会议》就有:“盖国也者,积民而成者也,积府州县乡埠而成者也,如人身合五官百骸而成。官骸各尽其职,效其力,则肤革充盈,人道乃备…”——把国家与人体完整地对应。考虑到作为刊物主编的梁启超与即将连载的伯伦知理的著作之间的关系,国家有机体论中的核心修辞与梁启超对它的运用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明显的。
此后,《清议报》第十五册连载的伯伦知理著《国家论》卷一第二章第五节写道:
“故国家者,非徒聚民人之谓也,非徒有制度府库之谓也,国家盖有机体也。”“人之造国家,亦如天之造一种有机体”。
国家有机论中的修辞化表达已非常明显。其间人的器官肢体与国家机构的对应关系同梁启超在《商会议》中的表达基本相同。
《清议报》第十七册连载的伯伦知理著《国家论》卷一第三章第三节有这样的表述:
“夫人类之生育,必有一定之期,可以卜其盛衰,而国家则不然。盖国家非天造之有机体也。然亦有与人类之生育相类者。国家幼稚之时,与国家势力强大之时,基性质固不同矣,及进至老境,则更得别种性质。昔时罗马人区分国之年龄为幼弱壮老四等,可谓善状也”
——从“成长周期”的角度将国家与人体对比,这不就是《少年中国说》的核心修辞吗?
也就是在此文中,呈现了对国家成长周期的判断标准:
“国家形状及事业,皆随国之年龄为变迁者也。其变迁之迹,就各国宪法之沿革观之,则了然矣。此种变迁,于第三卷详之。”
显然,这里已暗示出国家的“年龄”或“成长周期”与人体相异的判断标准——政治体制的成熟进步。这正是《少年中国说》的理论基础。
按日本学者稻田周之助(1913)梳理,“国家年龄说”也正在国家有机体说的体系之中:
“谓国家有幼年、少年、壮年及老年之四期。其幼时托于专制政治;较长则适于宗教政治;成年以后乃适于立宪政治;而晚年复归于专制。”
由此可以看到“少年中国说”中所谓“少年”的语源。但梁启超显然自己阐发了“少年”在“国家年龄说”中所没有的象征意义——充满无限生机的意义。
可以说,《少年中国说》中所体现的国家理论和修辞,早已经在伯伦知理的著作中形成了,并非梁启超的创造,但是,梁启超对于这样的理论及修辞中所孕含的鼓动人心的力量特别敏感。他发掘出了这种理论中积极的意义和鼓舞人心的价值,并用自己擅长的新文体表述了这样的理论,并从中提炼出了“少年中国”这样一个积极的意象和响亮的表达。这是梁启超的创造因素。
梁启超接受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非并偶然。在作于1902年的《论学术势力之左右世界》一文中,他在文中列举了影响世界历史的十位思想家及其思想,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即在其中,与哥白尼、达尔文、卢梭等并列,而梁启超曾专门著文介绍过的康德、斯宾诺莎则不在其中。梁启超还把伯伦知理与卢梭作比较,说“卢氏立于十八世纪,而为十九世纪之母;伯氏立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显然更重视伯伦知理国家学说的当代价值。在1901年写作的《康南海先生传》中,梁启超称自己“近者又专驰心于国家主义”,正反映了《少年中国说》写作时期梁启超的思想背景。《少年中国说》正是他所“心驰于”的国家主义的一种表达。
当然,用有机体乃到人体来比喻国家,并非始于伯伦知理。“从古代起,就有人把作为一个社会统一体‘成员’的个人同生物体的各个部分或器官相比。”(鲍桑葵,1995:60)
而亚里士多德(1996:7)谈到城邦的时候谈到:
“一切城邦既然都是这一生长过程的完成,也该是自然的产物”
“无论一个人或一匹马或一个家庭,当它生长完成以后,我们就见到了它的自然本性;每一自然事物生长的目的就在显明其本性。”
——显然,古希腊的政治学家就已经把包括城邦在内的社会组织比喻成有机体了。而且,在亚里士德多的这个表述中,在把政治组织城邦比喻成有机体的基础上,他也进一步谈到了组织的“生长”问题。而国家的“生长”问题也是《少年中国说》中比喻的核心。
在梁启超1903在《清议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译作《国家有机体说》一节中,他它按语中指出:
“此说不起于伯氏。希腊之柏拉图,亦常以身喻国家。伯氏前之德国学者,亦稍发之。但伯氏而始完备耳。国家既为有机体,则不成有机体者,不得为国家。中国则废疾痼疾之机体也,其不国亦宜。”
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个晚清中国,因为没有达到近代国家的政治制度标准,在《少年中国说》中被看作是充满生机的“少年”,而在其上述不引人注意的学术注解中,却被称作“废疾痼疾之机体”,相差如此之大。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有体论在作为判断具体国家的发展进程时,其选择的喻体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在《少年中国说》中,不仅有来自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论,还有一直影响着梁启超的进化论。当年,梁启超正是以进化论作为思想基础写出了《变法通议》。而他在流亡日本之后,则接受了把进化论推广到社会领域的“社会进化论”。
1900年6月7日出版的《清议报》四十七册开始连载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它在谈到国家制度的进化时写道:
“国家内部制度,虽既稍备,而盛衰隆替,时有变迁。其先为君主专制之世。次成战国扰乱之世。或为教权一统之世。或成法律一统之世。或成议论纷扰之世。或成道理一统之世。此皆社会自无而有,由小而大者也。凡社会之发生,使中途消灭则已。苟不消灭,其变迁之次第,必有如果以上所述者。指此全体,即谓社会进化。”
这种展开视野,以古今中外政治制度变迁作为标志的社会进步观念,显然契合于《少年中国说》中蕴含的国家进化理念。
其实,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也融合了社会有机体论。如在《清议报》第四十八册刊登的第一部第一章的标题即为:“社会因人类之聚合而协力分劳遂成为有生机之物”。
其第二节写道:
“有生机聚合者谓于同时同地聚合数物数部分,此物与彼物,此部分与彼部分,有互相牵涉者,譬如动物躯体中之耳目肺肝心胃肠脾等之聚合,草木之干枝根叶花实之聚合…”
这就与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一样,使用动物、植物作比喻来说明其抽象的“有生机聚合”。
而进一步,他明确指出:
“以各种人类而聚合之社会,则各部分之聚合,将为有生机之聚合乎,无生机之聚合乎?答之曰:此即有生机之聚合也。”
——显然,从逻辑的角度来看,“社会有机体论”包括着“国家有机体论”。因为国家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
此外,“少年中国说”并不仅仅是偶然产生的修辞现象,而是与梁启超的国家思想相关,还体现在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发表前后的其他学术文章中,都多次稳定地表达了曾在《少年中国说》中以修辞的形式表达的国家理念。
比如,1901年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虽作于《少年中国说》之后,但在学理上阐述了《少年中国说》以修辞表达的相同国家进化理念:
“世界之有完全国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曷为无完全国家,以其国家思想不完全也。今泰西人所称述之国家思想,果为完全乎?吾不敢知。虽然,以视前者,则其进化之迹粲然矣。”
“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
显然,这也是《少年中国说》所表达的国家进化观。只不过,《少年中国说》主要是以政治制度的进化作为判断国家成熟的国家标准的,而这篇《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则增加了一个“国家思想”作为判断国家的标准。
在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杂志上的《新中国未来记》的绪言中,有“国家人群,皆有机体之物”的表述。
1903年梁启超发表其翻译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其中一节即为《国家有机体说》。在此文中,梁启超用加按语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国家有机体论的理解和阐发。其中多有近于《少年中国说》的比喻。
比如,在原文“试即国家与寻常物相类之点而比较之”的第一点“精神与形体相联合”这句话的后面,梁启超加了一个按语:“国家自有其精神,自有其形体,与人无异。”
文中还有:“国家之为物,与彼无机之器械实异。器械虽有许多零件纽结而成,然非如国家之胛肢五官也。故器械不能生长发育,而国家能之。”
此句中“国家发育”的思想,正与《少年中国说》的基本理念相同。
在梁启超所处的那个时代里,一方面是“民族竞争”的国际关系;另一方面是国家思想变迁。重新确认国家的标准,确认中国是不是一个国家,是怎样一个国家,并不是一件没有来由的议题。据学者介绍,“1920年前后,在日本知识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几种偏颇的中国认识。如矢野仁一的“中国非国家论”、内藤湖南的“中国无政治论”(刘家鑫,2007: 70)所谓“中国无国家”这样一个认识,完全可以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理由,因为如果你侵略的对象并不是一个“国家”,也也就谈不到侵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明确地表达一个国家的意识,尤其是表现一个现代国家的意识,则是民族图存的武器。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值得肯定。它是现代国家意识的民间表达。
《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在“以身喻国”这个有着国家有机体论背景的修辞化表达的基础上,除了产生了“少年中国”这个创新性表达之外,还以“少年中国”和“中国少年”交替使用,并写出了“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等一系列激情洋溢、脍炙人口的排比句,以表达了“少年”与国家富强的关系,后世传播似乎尤广。表面上看,在文中,这一层议论似乎是从前半部分“少年”与“老年”的繁复对比中衍生出来的。其实另有文本之外的思想资源。
1900年12月12日)《清议报》第六十六册,其未“瀛海纵谈》栏目中有一篇《今日少年》写道:
布鲁德利有言曰:“国家他日之强弱存亡实握于今日少年辈之手。”吾读之不禁汗流浃背而震惕弗已焉。夫以今日积弱不堪之中国而欲使之复强,已就灭亡之中国而欲使之复存,肩其任者不其难哉!不其重哉!……少年其努力哉!努力于今日哉!
这正是《少年中国说》中于“少年”与“中国”关系表达的思想源泉。因为它们表达得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少年中国说》中并没有交代这样一个思想资源而已。
而梁启超在此后1901年所作的《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一文中写道:
“呜呼!老朽者不足道矣。今日以天下自任而为天下人所属望者,实惟中国之少年。我少年既以其所研究之新理新说公诸天下,将以一洗数千年之旧毒。”
——这样的表达,与《少年中国说》几乎相同。
四、“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一系列提振民族自信心作品的代表
[删节]
结语:
评论作为人类认识的形态,不仅是传播观点的载体,更是创造观念的载体。即,评论的写作往往是一种新知识的生产过程。尽管我们所看到的大量的、更多的评论作品其实只是在传播少数被创造出的新的观念——包括有利于某种传播的观念的创造性表达。关注评论中的创造性因素,关注那些出现于评论中的那些新的观念和新的创造性表达,探索它们产生的原因和生产机制和条件应当是评论研究的一个重点。
“少年中国说”就是梁启超创造的观念及其新颖的修辞形象。“少年中国”发当时的不胫而走,“少年强则中国强”等语句的至今传播和流衍,都反映了这种创造性知识的生命力。他之所以能够创造这个概念,与他所接受先进的国家理论有关,也与他作为一个政论家把理论观点转化为大众传播的表达形式的能力有关。
引用文献:
陈玉申(2003).《晚清报业史》.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程福宁(1996).《中国文章史要略》.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李良荣(2002).《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石云艳(2005). 《梁启超与日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佐藤一郎(1996).《中国文章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单正平(2006). 《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英]鲍桑葵(1995).《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日]稻田周之助(1913). 《国家有机体说之概要及其批评》.(王倬译).《法政杂志》,(3),67-74.
约翰?鲁尔克(2012).《世界舞台上的政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1996).《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刘家鑫(2007).《日本近代知识分子的中国观》.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