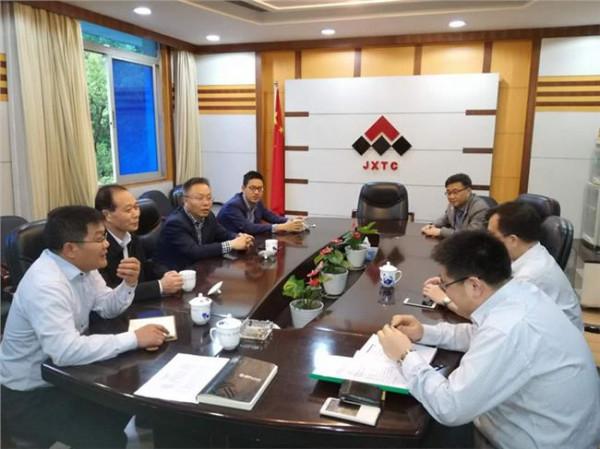谭平山辛亥改革 审视晚清新政与辛亥革命 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
自打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问世以来,旧制度在变革中更易引发革命,在近年的学界,成了一种流行论点。美国政治学者斯考切波(Skocpol,T)的有关俄国、中国革命的宏观论述,更是强化了这种观点。中国的辛亥革命,已经成了一个改革引发革命的典型案例。
[①]似乎改革成了旧体制迫在眉睫的催命符,不改还好,一改,死得更快。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就是,不改是等死,改是找死。宁肯等死,不要找死。的确,辛亥革命似乎很能印证这个观点,这场革命,的确发生在清朝最后,也是最认真的一场改革过程中,打响第一枪的新军士兵,本身也是改革的产物。
多少年来,对于中外的研究者而言,一个流行的观点就是,新政的改革,激化了原有的社会矛盾,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因而引发了革命。
客气一点的说是操作不当,不客气的干脆等于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改革的条件,一改必死。其中,新政诸项改革中,最令人争议的就是废科举,在许多学者看来,这项改掉了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制度的改革,不仅打掉了士子们上升的渠道,而且切断了民间精英跟朝廷的联系。也导致了大批士子没有出路,倾向革命。所以说,革命发生,土崩瓦解,势所必然。
然而,新政真的造成了清朝统治的危机,造成了革命的形势吗?如果真的是改革激成了革命,那么,清末新政有那一项改革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弹,造成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呢?新政期间,所有跟新政有关的民变,比如抗捐抗税,抵制清查户口丈量土地,都是零星的,小规模的。
连废科举,都波澜不惊。以至于当时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莫理循乐观地说:“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1905年9月2日皇帝敕令从1906年开始废科举——注释),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②]原来一直认为是专门针对废科举的民间骚动,山西的干草会的所谓“烧先生,打学堂”之举,现在发现其实好些只是平常的吃大户行为。跟新政没有任何关系。
所谓的打烧学堂,只是揭帖传单上的宣传。[③]这一时期发生在江苏宜兴和浙江慈溪,上虞和余姚等地打砸学堂事件,根据当时的报道,大抵由于经济纠纷。[④]按道理,改革举措,涉及哪个人群,哪个人群受损,就容易引发冲突。
军事改革,面临被裁撤、降等威胁的旧军,出现过哗变和骚乱吗?没有。行政改革,那些被裁并的机构人员闹过事吗?也没有。废科举,事关千万士子的前程,真正起来闹事的人,也是凤毛麟角。严格来讲,新政举措中,真正引发激烈的民间反弹和抵制的,其实是禁烟。
当时的朝廷,下决心在几年内让中国禁绝鸦片,从铲罂粟,到禁绝交易,多头入手,力度很大。跟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禁烟举措一样,中国的禁烟,也在很多地方都引发了民变。
1910年春,山西山西文水、交城民众抵制铲烟苗,跟官府发生冲突。后来山西巡抚派新军镇压,死伤过百,成为轰动一时的“文交惨案”。[⑤]1911年春天,在温州也发生了铲烟委员下乡铲烟,连委员并随从七八人一同被乡民打死的事件。
温州事件跟文交事件一样,下乡铲烟的专员,都带有武装,配置新式洋枪,但是,却都遭遇乡民激烈的武装抵抗,规模达到成百上千人。[⑥]这样的骚乱和民变,在整个新政期间,算是规模最大了。
然而,这样的民众骚动,其实跟新政的改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什么时代,只要禁烟,就会有这样的反抗和抵制。在外国学者看来,中国那一时期的禁烟,是卓有成效的。只是到了民国之后,才使得清政府的努力前功尽弃。[⑦]
如果说新政的改革,把人们的胃口吊了起来,形成欲壑难填的求新欲望,倒也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新政到1911年,满打满算,不足9年,开民智的效果,还不明显。西方的观念,即使在比较开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只是有限的流行。
士绅们比较急切的改革呼声,无非是赶快立宪。他们连模仿日本和德国的钦定宪法大纲,都没有进一步修改的欲望。在武昌起义之前,立宪和革命,一直是在两个轨道上行走。如果不是新上台的满人少年亲贵肆无忌惮地收权得罪了人,主张立宪的人,并没有革命的冲动。
虽然报纸上时常可见文人们对新政的讥讽,披露新政出的诸如食洋不化的笑话。但总体上,新政的面貌给人印象还是不错的。上面提到的莫理循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新政给北京带来了新的面貌。“北京有了碎石子铺的马路,有几好的警察,有良好的秩序,有马车,有外国式的住房,有电话和电灯,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
”而且,新办的警政,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莫理循称赞道:“他们控制的街头交通令人赞佩。各城门不再出现堵塞现象,人人都必须循序而行不准许向前猛冲猛撞。
即便是由德国兵驾着的笨重四轮运货马车也不准破坏马路规章。有一个讨厌的士兵装腔作势不肯服从指挥并且拔除他的刺刀来,维持治安的警察便吹起警哨把这个兵逮了起来,押到附近的警察所处。
那个兵在当天晚些时候才由一名德国军官从那里营救出去。”[⑧]得到同样印象还有来自苏格兰的传教士医生杜格尔德·克里斯蒂,他多年一直在奉天行医,在他的眼里,新政期间,奉天一片阳光,鸦片在禁绝,学校在兴办,几位总督都挤出钱来支持他开办医院。
雨天泥泞不堪,旱天尘土飞扬的奉天(新政前的北京也是一样。——笔者注),现在兴建起了碎石子路。街上开始出现了路灯,几年后,路灯变成了电灯。
随着道路的改善,“在大街上出现了数百辆黄包车,俄式无盖四轮马车已经非常普遍,官员们出行则乘坐国外封闭的四轮马车。”警察也来了,“小小的蓝色岗亭出现在街角”,警察开始指挥交通。奉天甚至组建了卫生委员会,颁布了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城市卫生方面的法律。[⑨]不仅城市有了新面貌,开展了地方自治的乡村,治安状况也得到了改善。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研究,都不能否认,跟新政前后相比,新政时期是社会秩序最好的一段。
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也很说明问题。新政时期,是一个民族资本投资的小高潮。从1903年到1911年,1903年,新增企业9家,资本599280元。1904年,企业23家,资本5222970元,1905年,企业54家,资本14813391元,1906年,企业64家,资本21278449元,1907年,企业50家,资本14573047元,1908年,企业52家,资本22527338元。
1909年,企业29家,资本9947254元,1910年,企业25家,资本4944740元,1911年,企业14家,资本2290500元。
[⑩]就此可以看出,在1903年到1909年这个新政比较健康发展的时间区段内,企业和资本的增加是相当快的。
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应该说,在支付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的前提下,作为国家主要收入的关税和盐税,已经被抵押掉了,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窘。但是,在1903年国家岁入1亿的基础上,1908年,国家年财政收入已经到达2·6321亿两,如果加上中央各衙门的收入0·3801亿,全国的财政收入则达到3·0122亿。
[11]不错,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赤字,尤其最后三年赤字比例比较高,但也没有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成立资政院之后,国家有了预算,预算需要经资政院审议通过。1911年(宣统三年)的预算,原来岁入为296961909两,岁出381357175两,赤字84395266两。
但经资政院的审议,岁入增加为301910294两,岁出降为298444360两,从赤字,变成略有盈余。[12]不仅中央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地方财政也相当宽裕,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结余。多的达到上千万两,少的也有几百万两。辛亥革命后民军的扩充,大部分用的是这个钱。
这一时期财政收入的增加,固然有加税的因素。新政期间,的确开征了一些跟新政有关的捐税,比如警务和教育的附加。但也有现代方法的财务整顿的功劳,比如肃亲王善耆兼任北京崇文门税监,采用现代会计制度,严禁关员勒索,但增加部分,年终提奖。
最后在短时间内,税收增加了两倍。[13]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吏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以往税收过程中的跑冒滴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而我们知道,传统税收最大的漏洞,恰在于中途的损耗,经手人的贪渎。
虽然说,到了清末,清朝的官僚机器,已经锈蚀,吏治的腐败依然根深蒂固,但是,由于新政及大地激发了汉人士绅和绅商的积极性,各地的士绅和绅商,通过地方自治以及办学,兴办各种社会团体的途径,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新政。
对于地方官员的不法行为,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途径走御史门路弹劾,更可以通过斥诸媒体,全国通电,示威请愿等形式表达抗议。新政时期抵制美货,收回利权和立宪请愿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显示了士绅绅商的实力和威力。
新政时期推行的地方自治,以及预备立宪,给了士绅和绅商参与改革的正式通道,也反过来极大地制约了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与此同时,自1903年苏报案之后,朝廷的媒体政策逐渐开放,大量的民营报纸问世。
少数具有革命倾向的报纸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民营报纸,也多半以与官府为难为事业。凡是嗅到官员的贪腐和不法,一定大张鞑伐,毫不容情。在这种特别的情形下,一方面是官员落马的多了。据统计,仅1909和1910两年,经摄政王载沣批准革职的大小官员,就达千人以上。
[14]另一方面也不能不说,这一时期的吏治状况,是有所好转的。在媒体和士绅天天盯着,痛加批评的情况下,至少不可能变坏。吏治好转,官员贪腐减少,民众的负担就轻,所以,尽管新政增加了许多新税,但民众的反弹却不强烈。
后来的革命,实际上是社会中上层对统治者不满的爆发,而非民众活不下去的造反。革命,跟广大的农民基本没有关系。由始至终,农民连响应革命都兴趣缺缺。
当然,废科举的确很有问题。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选官制度。以考试选官,原本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就目前来看,依然是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是,在古代的中国,这个制度不幸地跟教育制度捆绑在了一起,使得学校教育,基本上以科举为导向,到了明清两代,官学系统,居然成了科举的一个台阶,基本上丧失了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
而且连带着把民间的私学体系,也跟科举联系起来。虽然说进私塾读书的人,未必都要考科举,但其中学的好的,肯定是以科举为目标的。
这样一来,整个学校体系,所教的内容,基本上被科举左右了。显然,这种现象,是导致中国社会其他的技能教育缺失,只能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一个重要原因。间接地,也跟近代科学技术难以在中国发端,不无关系。



















![>王奇体育 [新华访谈]王奇:足球改革倒逼中国体育的改革](https://pic.bilezu.com/upload/2/91/291a6ae273004a1f7ac8bc38f1eb4dd8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