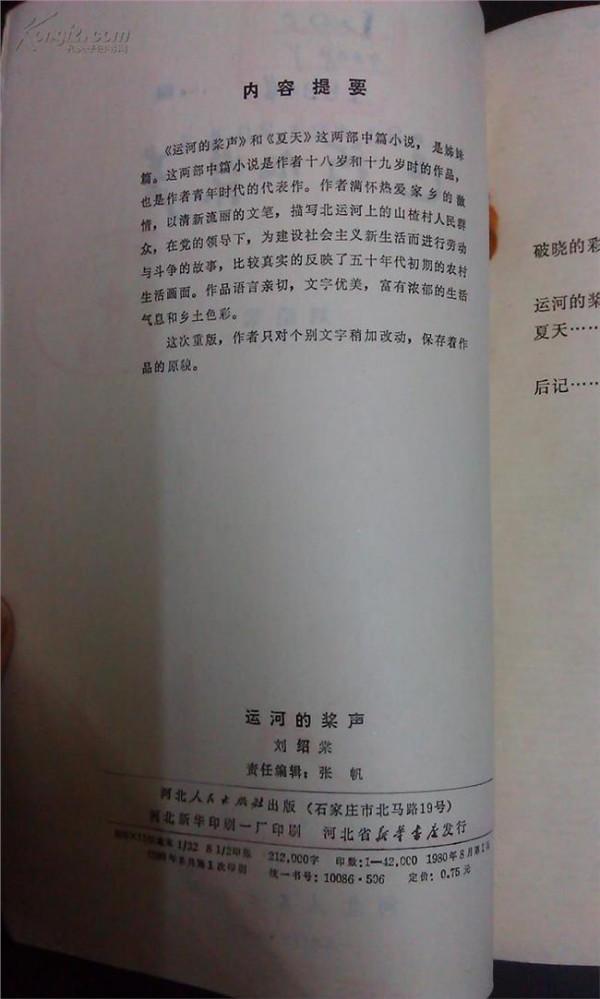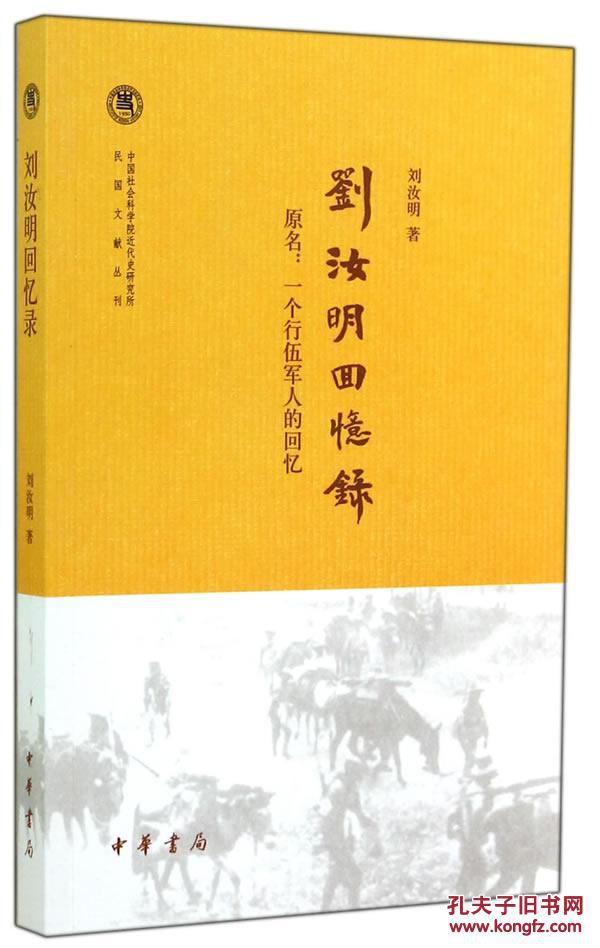刘仲敬出国 刘仲敬 :未来中国没有什么出路
刘:胡适学问浅,踩出了几个脚印,大部分时间他在从事社会活动。他选的那个方向是对的。他有一种英国人所谓“健全直觉”――大致方向断准的,但具体怎么做我也不甚明瞭。
民国真正起重要作用的恐怕不是胡适这类在渐渐衰败的舞台上奕奕生辉的角色,可能是一些外国人或者跟外国人接触密切的人,像顾维钧、李大钊。
这两位都起到很大作用,而且恰好是一正一反对称的。顾维钧是尽可能把他为之服务的政府一步一步引到国际社会中去,他做的是慢工出细活、缓慢积累的事,当然他那一系后来执掌国民党时实际上跟北洋时代相比是失势了、降格了,他没有足够时间去完成它。如果北洋时期的外交政策能够延续,抗日战争大概是不会爆发的。等顾退到台湾,舞台基本上就消失了,他代表的仅仅是一种失去的可能性。
李大钊正好相反,是尽可能破坏这个主流――他在北洋时代主要跟着章士钊这些政法系的人,反对国会、反对国民党,尽可能走国家主义路线。等到他的政治主人倒台,他也不肯退出政界安心去教书,转投苏联门下,又给冯玉祥当策士,搞破坏条约体系的事。“三一八事件”的实质就是企图废除《辛丑条约》的攻击,最终通过卢沟桥事变实现。苏联通过国民党劫持段祺瑞搞革命外交,然后通过共产党劫持国民党搞革命外交,手法完全一致,结果都是中国充当苏联的人肉盾牌,打破列强对苏联的外交封锁线。李大钊在第一阶段的作用,就相当于张闻天在第二阶段。从列强、尤其是日本的角度看,中国就是狂犬病人,已经被病毒侵染,不打死就会咬人。日本每一次谈判,关键就是要求中国肃清内部颠覆分子,不然谈判成功以后,中国很快就会毁约,完全是白费功夫。
黎巴嫩的情况就是这样。叙利亚不敢打以色列,就通过真主党劫持黎巴嫩政府,强迫黎巴嫩抗战。以色列的报复只会落在黎巴嫩头上,落不到叙利亚境内,因为叙利亚在法律上没有参加抗战。如果黎巴嫩政府想跟以色列谈判,真主党就在内部闹事。黎巴嫩政府如果镇压真主党,就会挨叙利亚的打。只要胡志明小道通向境外,黎巴嫩再怎么镇压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黎巴嫩政府两头得罪不起,只能苦苦哀求国际社会干涉,列强大部分时间又懒得理你。你把黎巴嫩换成中国,以色列换成日本,叙利亚换成苏联,就明白当时的形势了。中国横竖都是死路一条,李大钊就是中国的纳斯鲁拉。黎巴嫩人效忠叙利亚,比效忠本国政府更加有利可图。
李:每次听你一拐就拐到世界史部分,我总是存个档,等具备同样的知识了,再来咀嚼、检验。还有,每次看到你对孙中山的旁敲侧击,我会停下来想一想――说说他吧。
刘:如果把他视为国父,或者国民党的一位政治领袖,那么他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负面的。但如果把他当作一个个人,一个实验者,一个原本没有多少学问也没有多少思想的人,因为被时代裹胁,不断地承担着他自己没有能力承担的使命,那你就会比较同情他了。
李:盛宣怀呢?
刘:盛宣怀是一个典型的官商,像历史上的桑弘羊或西门庆。他虽是资本家,但却不是西方自治施政党派意义上的资本家。他真正懂得的艺术是搞官场,搞政策,就是经营国家权利。只不过从前的官商,盘子比较小,只能搞搞盐运、漕运;近代西方势力进来以后,则可以插手航运、铁路这些更加高大上的项目。但是盛宣怀的思路仍然是传统的国家资本主义思路。这种思路的前提是剥削、打散没有政治组织力和抵抗力的独立商人和消费者,实际上就是掠夺,搞背靠国家的垄断经营。这是一条死路,它会制造出一些埃及式的散沙型市民,不会产生负责任的、有自治能力的社会团体。
这有点像当年英国的艾塞克斯伯爵。艾塞克斯伯爵这种人,没有手艺,也没有祖传的生意,但他是国家大臣。他找到女王陛下,请她把葡萄酒的专卖权赐给他。这样一来,从前那些种葡萄的农民,生产葡萄酒的工人,卖葡萄酒的商人都将面临倒闭。这样搞垄断贸易,对资本主义肯定是不利的。所以国会和伦敦市议会强烈要求废除垄断贸易,杜绝把某一个行业经营权交给国王的宠臣。其中有位议员向伊丽莎白女王抗议说:您为什么不把面包经营权也赏给他们?
这就是英国国会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公案“面包不在内吗?”当然女王算是比较开明,她亲自向国会道歉,说以后我再也不这么干了;议会成员也就见好就收,等于说双方达成妥协,事情到此为止。这在《艾塞克斯伯爵传记》和《伊丽莎白女王传记》里都可以找到。
李:读《民国纪事本末》的时候,我蛮感慨:亏得这部书是用你所谓的“民初体”写就,否则估计是看不到的。很多段落精彩,要自己去品的。但有些,还是要请你讲讲开,比方这一段,跟上面的话题有关:“广州商团若能尽歼党军及苏俄顾问,送孙、蒋二公回上海租界,则江东本部绝不至糜烂。”
刘:广州商团本来是最接近欧洲式自治的,跟伦敦商会很像,只是不如它强大。资本主义应该如此,广州市也好伦敦市也好,本地有产阶级就该组织自己的团体,选举出自己的议员,维护自己的利益。当然我们做生意会挣到钱,国王或者是中央政府肯定会也看在眼里,想着要捞一笔。捞一笔有许多名目,要打仗,要去别的地方争霸,反正都是为了本国人民好,理由都正当。但是你如果让国王或中央政府得逞的话,就会产生出一个法兰西或者西班牙这样的绝对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就发展不起来了。所以伦敦、广州的商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反对政府杀肥猪,这样的做法是非常进步,非常宝贵的。
孙文本没有实力把广州商团镇压下去,他是靠着黄埔军和苏联的力量摆平了他们,在广州实现了专制统治,相当于詹姆斯二世国王把伦敦市的商团给镇压了――结果一样,就是两地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掐。孙文以广东为根据地,国民党才能够占据江南,在东南五省建立自己的权力机构;然后蒋介石又把上海当成奶牛来挤,依靠上海来武装自己,实现全国的中央集权;再然后蒋撕毁条约,结果就是爆发中日战争,中日战争就是以上海和东南部为主要战场,战争的结果是把共产党送上中国政治的中心舞台。这一系列结果草蛇灰线,苏联始终是幕后的操盘手,而国民党、共产党始终是在起破坏性的作用。他们就是今天黎巴嫩的真主党、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共和国,以本国反政府武装的名义,充当邻国破坏国际秩序的代理人。关键就在于:如果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那最好一开头就赶紧止步,如果长的是一棵毒草,还没长大趁早拔掉,这样代价最小。
塔利班刚刚起家、只有几十个人的时候,把它做掉是很容易的事情。孙文在广州搞的军政府,力量是很薄弱的,商团凭那点雇佣兵本可以平起平坐打一下,当时英国如果给力一点,或者商团的领导更强势一点,说不定就把孙灭掉了,灭掉之后中国就会长期处在各路军阀的统治之下,只要条约体系不破坏,那种前途肯定比国民党和共产党统治中国要好得多,后来一系列最坏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英国当时的消极态度跟奥巴马不肯干涉叙利亚的逻辑是一样的,那些破地方不值得牺牲本国军人。否则,伊斯兰国根本没有出现的机会。问题不是在于帝国主义侵略,而是在于帝国主义不肯侵略。如果不要帝国主义,那么哈里发是正常的、黄巢张献忠也是正常的。列宁主义国家的死亡率还没有达到张献忠的水准,就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李:商团和政府,在民国的时候基本上是一个什么关系?
刘:勒索和被勒索的关系吧。比如说张勋在南京,把地方上商人召来筹款,如果筹不齐,他拔出枪来往桌子上一拍:我们要抢了。这样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发生,在不同的地方发生,商团始终是被勒索的。但是另一方面商团也得到了一定的自由,他们等于是用钱交换来自我管理的权利,这权利非常宝贵。
在欧洲,一开始商人们也是被勒索的,要花巨款向国王或者领主买特级权,也就是自治权。这笔钱送给公爵或是国王,拜托就不要来管我们了,我们每年再供奉您另一笔。但是商人挣到钱以后,国王和公爵还是看不顺眼,想要更多一点,于是双方又开始讨价还价,谈不成的话,就会打起来,像勃艮第公爵和根特市民来来回回打很多趟,伦敦历代国王为了钱的事跟商团不知吵过多少次,最后总能找到一个暂时的平衡点。这样慢慢一点一点积累经验,几百年过去,马克思所谓的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级就会慢慢变得足够强大。如果国王索欲无度,干脆连你国王一起推翻,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
广州商团跟孙中山发生的关系,就是南京商团跟张勋发生的关系――自治权已经到手,但是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强大;你拿着枪杆子来敲诈勒索,没有办法,还得敷衍你。关键时间太短,几十年就完了,如果也像欧洲一样有个几百年的积累,说不定广州也会像伦敦和阿姆斯特丹那样变成一个自治单元,那样发展下去,中国的前途可能会透出另一种光亮。
李:谈谈民国时期你喜欢的知识分子吧,像昨天我们已经提到的章太炎、陈寅恪、傅斯年……那些群像,那些个性。
刘:能让知识分子发挥个性的往往是乱世,像魏晋、明末,一个稳定的社会很难由着你培养和发挥个性,只有在解体的混乱中,才能让人特立独行,否则肯定要迁就共同体。
章太炎时人称章疯子,说的多是些夸张的、放任使气的话,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判断力是很强的。在他,只求发泄,不需要负任何责任。
傅斯年的性格是革命者,但他的身体条件让他不适合做一个革命者,所以他最后还是一个清流。在学术上,他赶上一个垦荒的时代,开辟了新领域,但未及深入挖掘――这些工作由后人来做,当然后人不可能像他那样出名,因为纯粹技术性的工作总是乏味的。从西方学术的角度看,他微不足道,但从中国学术的角度看,是开创性的大人物。
陈寅恪在他自己心目中,应该是一个失败者和投降者。他总把自己看成是钱谦益那类人――明亡之后,孤独地留在另一个时代里,属于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陈寅恪怀着的也是一种前朝遗民的心态,这种心态给了他一种透视力,就是我先前说的情景模拟的方法,将自己代入,以古典和今典相互映照。
你看他那些中古史,用阶层分析的方法来做,不纯是靠考据,背后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描写的那些门第世家,差不多就是陈宝箴作为同光遗老的一个折射。
他认为李党牛党的区别就是门第家风的区别,旧有的、气味相投的世家结成了李党;新晋的那批出身低贱、浮薄的、没有固定道德操守的结成牛党,这就是他本人在清末民初看到的一些社会现象的反射:新旧沉浮之间,比较严谨的、坚守旧道德的社会集团正在被淘汰,新兴的、不大守规矩的人上来了。
他用这副眼镜去透视中古史,他立下的这个范式又约束着后来的人。严格说来,陈寅恪的考据不是很精密的――主观性比较强,以今典套古典――现在搞中古史的人比他精密多了,但他的范式站住脚了。范式(分析框架)往往比考据(材料)重要,像马克思重要在哪里,就是提供了一套分析框架,形成了一个传统。
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过什么感觉?
刘:作者不大能理解陈的那种遗老心态。另外,陈寅恪是传统士人,也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世故,尤其他对政治人物的言说,许多是客套,不能句句当真。他真实的想法要从那些比较隐秘的地方获得,我推测他在民国、共和国,真实的自我感觉就是:贰臣。但他又软弱无力。他做学问的能力强大,但他根本没把那个当回事,他是一个整体性的士大夫,认为自己负有匡正国家的责任,不是写写文章就算数的。而他在这方面是完全失败的,所以他在骨子里有点瞧不起自己。
外界评价和自我评价往往是两回事。基督教有个说法:品行最好的人往往觉得自己是罪人,因为他对自己要求高。反之,也成立。
李:能不能从同时代里找出一两位这样的反面呢?
刘:郭沫若。章士钊。
李:军阀谱系里圈点几位?
刘:张作霖的奉天堡垒后面,是王永江给他打造的一个财政机制。张和正在成熟的奉天士绅之间需要一个联系的枢纽,王永江充当了这个中间人。但张并不能充分理解他的历史角色,他本该做一个虚君共和的军事领袖,保持东三省的财政,保境安民,平衡好日本和俄国的关系,让小鸡慢慢孵出来。但他好大喜功,一而再再而三地入关,把王永江替他积累下的财富消耗殆尽,然后“九一八事变”爆发。
一个领导人必须克制很多诱惑才能懂得有所不为,像伊丽莎白女王,明明也可以调动足够的资源,但她总是尽可能地避免打仗。她说,如果打仗人人都可以获利,唯独王室是吃亏的,所以尽可能休养生息。太渴望那种辉煌的表演,那种戏剧性的时刻,就会导致短暂的挥霍而把历史的灾难留给后人。
一个好的领导人不应该是虚荣心太强的人,最好是像柯立芝或哈丁那样的人,想的不是留名青史,而是把美国历代留下来的那些宝贵传统守护起来传下去,藏富于民。像江苏督军李纯,从文人、从武夫的角度看,他都平平,但若从政治德行上讲,他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他随随便便也像张勋那样弄些政治上的表演,那么江苏就会被他毁掉。给他一篮子鸡蛋,他就稳稳当当在那里孵小鸡。如果蒋介石有他一半老沉,恐怕现在还是国民党的天下。
李:在民国的银河系里,有没有接近土豪的人物?
刘:有,但都不太有名。比如说,在李纯当督军时的江苏省议会的议员,那是一批比较理想的土豪人选。李纯虽也是个军阀,但他没有张作霖他们那些重大野心,能在江苏当一把手他已经很满足了。江苏富裕,但他并不想扩军备战,去征服其它省份,所以他愿意跟省议会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让税收和财政保持原有的小规模,让江苏省议员去发展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而省议员在搞资本主义过程中表现得很理性,很有政治德性,跟欧洲差不多。
有一件事情可以佐证:江苏当时发生过纺织业纠纷,因为新式纺织业的引进,原有的小纺织业主竞争不过,生路快要断绝,所以跑到议会去闹事,殴打议员;但是尽管如此,议会重新召开时,仍然做出比较公正的决断,让大家都有条活路。
当时实际上是存在一个默契式的分权,李纯不到外面去搞扩张,但是他任命的政府官员,议会都承认的,你搞你政治维新,搞你的美差、肥差,随便,但拿到你自己的那份利益之后,就不要再要求别的东西了,具体的事务其实是由地方士绅自己来管理的。
李:我记得以前看到过一些资料,民初江苏省的议员多半能说一口流利英语,有西学底子,而且都是好出身,是这样一些人是吧?
刘:对。具体是谁你要去查了,因为他们在历史上不是什么知名人物,历史上留名的要么是军阀,要么是游士,但是这两类人物其实都不是什么正面人物,如果从欧洲的观点来看,他们都不是土豪,不是社会建设者,而是汲取者和消费者。你如果要名字的话,最有名的就是南通张季直,但是正因为他是最有名的,所以他身上多少沾染一些文人气或者是挥霍者气,真正比他更有建设性的是那些不如他有名,也没有太大野心,全心全意扎根在地方上,只管他们自己经营的工厂,或者是他们在议会中是比较小的人物,是那些比较土,他们才是真正的建设者。
土豪的要害就在一个土字,他的势力离不开乡土和乡邻。他有固定的归属,因此是社会的稳定力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就是土豪衰败灭亡的历史,这一进程其实就是传统中国的消失。
李:梁廷枬当年编了三卷《合众国说》(第一套介绍美国国情的专著),再看当时士大夫的日记笔记,都不难找到对代议制的情有独钟。从郭嵩焘、薛福臣,到后来的杨度、梁启超、张謇等等,自不必说。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有着千年君主制传统的国家里,有那么些士大夫会喜欢议会制度?
刘:这批喜欢议会制的人,用现代话说就是语言叫清流议政,其实他们真正喜欢的是三代上古,喜欢是尧舜时期的中国。在他们看来,西欧,尤其是英国有点像是尧舜时代,君民共治;孔子时代,也是天子和诸侯、士大夫共治的情形,不像是秦代大一统之后君主独治。三代上古一向是儒家的理想,议会制等于是激活他们原有的一部分资源,其实这个直觉也是准的。
李:我有同感。想想(三代)那个时候在东南沿海,差不多有2000多个诸候,相当于2000多个村长,吃完晚饭,跑出去跟老百姓拉拉家常,说说话,当然君民不隔。君民不隔本是儒家理想,他们喜欢的其实是三代之治是吧?
刘:他们想的是春秋时代原始儒家,春秋时代其实中国也就处在相当于西欧封建的历史阶段,所以孔孟的原始思想你很多你可以套得上封建欧洲晚期欧洲思想,这很自然,因为照斯宾格勒的说法,他们是属于同一个历史季候。但是秦政以后不一样了,汉代儒家还比较坚持先前的理想,就是他根本上是反对大一统帝国的,但是以后的儒家越往后就越来越不得不迁就即成的事实,慢慢就搀杂别的成分进去了,所以你如果让孔子复活的话,他可能不会承认汉代以后的儒家还算是他的门徒,他可能觉得这些人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与其说是儒家,还不如说是杂家呢。所以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后期的儒家跟专制制度相互适应以后,等于已经变质了,丧失了自己的原初意义。欧洲呢,因为历史相对较短,还没有发展到秦始皇那个阶段,所以它跟早期的儒家精神上是比较相通的。
李:我大致听出些味道了。如果说,昨天我们谈的关键词之一是“封建时代”,那么今天的关键词是“自治”,而它们又是相通的。这是不是你对未来中国可能之路的一种暗示――好比你说的阴沟里的钥匙?
刘:未来中国其实没有什么出路。假如伊斯兰国已经巩固了几十年,利凡特已经不在国际体系的保护和约束之下,最合理的假设就是它没有未来。列宁主义是一台割草机,不能允许草坪上出现灌木、更不用说大树。这个社会不能允许资本积累,更不允许组织资源的积累。资本不是流向海外,就是中央汲取。具备社会凝结核潜质的精英不是被吸收到中央,就是流向海外。越接近地方和基层,就越只剩下最贫困、愚昧、无力自卫的散沙和最黑社会化的官员。就算社会空隙当中产生某些资源,也很难避免吴英和刘汉那种冲突。谁胜谁负、谁是谁非并不重要,因为冲突是结构性的,结果总是指向社会解体的方向。在这种社会中经营共同体,成本高而风险大,不如直接到海外建立自治社团。在这种社会中经营体制内建设,成功反而会增加身败名裂的危险。
假定从上海到重庆、从大连到北海,存在一系列汉萨同盟式的自治市镇,能够争取海上强国的政治保护,拥有五六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政治自由是可能的。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存在。只存在完全相反的格局。荷兰的资源流入莫斯科沙皇的手中,用于永无止境的高加索战争。
这种格局犹如将冰激凌运往沙漠,大部分都在路上融化。荷兰毁了自己的机会,高加索并不会因此得救。由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冲突趋于紧张化、长期化,指望汲取力度缩小是不大现实的。
从1925年、1936年、1978年到现在,机会窗口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小、更低。汲取的唯一明显后果就是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官僚国家和日益进攻性的外交政策,从而造成了必须进一步强化汲取的理由。根据历史经验,只有在财政无法维持的时间节点,游戏规则才会改变。
然而,由于中国并不存在哪怕是广州商团这样脆弱的自治组织。博弈的结果很可能不是规则的建立,而是社会秩序的崩溃。在这场假设的崩溃以后,沿海地区将会面临一个可以重新选择命运的窗口期。如果这些地区能够放弃太大的野心,满足于切实可行的小目标,就能为自己争取比民国时代更好的前途。
在可以预计的未来,将经济资源和组织资源留在国内发展,对个人而言不是最佳选择。同样的资源和时间,足以使他在海外取得更大的成绩。如果有人一定要这样做,就必须有利害关系以外的其他动机。对于根本没有资源可以利用的人,其实本来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必须自己发展这些资源,自己保护自己,面对其间无法预计的风险。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三者当中,组织资源成本最高、风险最大,知识资源成本最低、风险最小。在社会日益内卷化的情况下,最后一种资源的拥有者维持较低水平延续的可能性最高。然而,这种延续可能没有什么意义。如果有什么价值,最确定的价值大概就是方便当事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