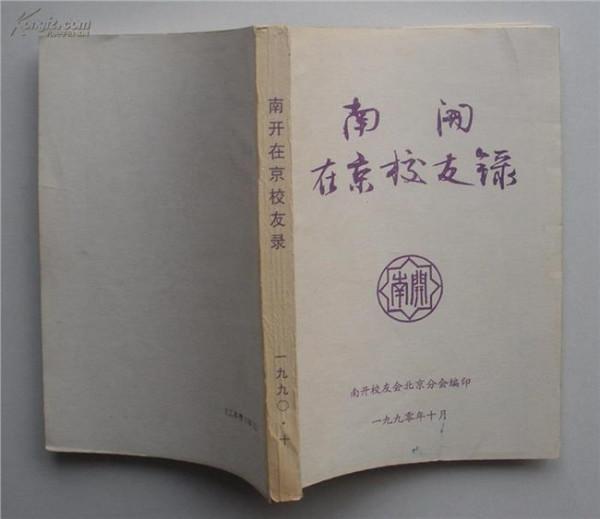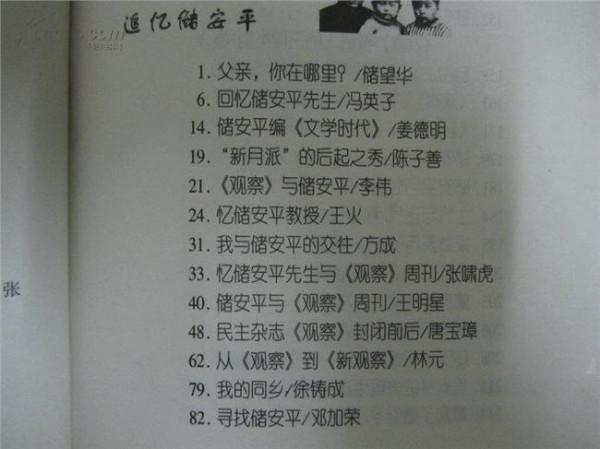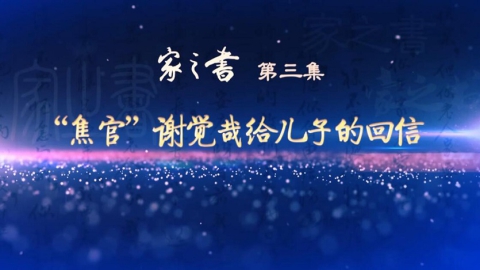谢泳钱钟书 谢泳:评钱钟书打架事件
最近,许多朋友通过电话和网上与我交谈,我们读了《南方周末》(11月19日)上杨绛先生的文章《从“掺沙子”到“流亡”》,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岁月里,我们必须对曾经发生过的历史做一些文化上的清理:人心为什么会坏到那样的地步?道德和尊严为什么会消失的一无所有?为什么总是坏人得志?为什么总是什么最好我们不要什么?什么最坏我们选择什么? 杨绛先生这篇文章说得并不是什么大事,而是一件生活小事,但这件小事在一定程度上却有象征意义,它象征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时代的普遍生存状态。
文化大革命时期,有一项革命措施,让“革命群众”住进“资产阶级权威”的家里去。
名为“革命”,其实就是在物质上剥夺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这就是大陆上所谓的“掺沙子”。 杨绛先生写了1969年5月间,她和钱钟书是如何面对那些“革命群众”分掉他们原有的两间住房的。
在这过程中,他们不仅经历了物质上的痛苦,要把自己的四间房分给“革命男女”两间。那是一个斯文扫地的年代,知识分子除了沉默,再没有其它表示抗议的办法。
更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那对“革命男女”分掉了钱钟书家的房子以后,更在精神和人格上对钱先生一家进行了摧残。杨绛先生写了这样一件事: 钟书下放干校以后,我下放干校前夕,女婿得一因“五·一六”案含冤自杀。
这件事,我打算等我自己下干校后,亲自一点一滴告诉钟书,免得他经受不起。当时吴世昌先生和钟书同在干校,而他的夫人严伯升和钱瑷是同事。
我怕消息走漏,求严伯升帮助我们保密,她非常同情。革命女子想必知道了我们隐瞒。我下干校后,钱瑷一人在家里,她在厨房里当面质问:“你爱人‘下干校’啦?钱瑷说:“他已经去世了。”随后,钱瑷听到他们屋里哈哈大笑。
这是我们事后才知道的。 杨绛先生的这篇文章,比他八十年代的《干校六记》《洗澡》,更让我们感到一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的伤害达到了何种程度。
如果说《干校六记》和《洗澡》写出了对知识分子群体被改造的共同感受,那么,这篇文章却是一个知识分子独特的个人体验。如果说下放干校是对知识分子的集体流放,事后回想,也许多少还有一些悲壮感,在《干校六记》中,我们常能感到在那样的环境里,那些被集体流放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尊严,他们还能有一些苦中作乐的黑色幽默,到了杨先生现在这篇文章,知识分子除了屈辱,实在别无生路了。
一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精神到了如此地步,知识分子,用杨先生的话说,除了“流亡”还能再有其它什么选择呢? 杨先生说:“打人,踹人,以至咬人,都是不光彩的事,都是我们决不愿意做的事,而我们都做了——我们做了不愿回味的事。
这件事,尽管我们在别人问起时,不免要说个大略,我们私下里却是绝口不再谈论或讲究,因为我们三人彼此间都很知心。”当我们看到钱家母女三人,在无奈之下,决定出走时,心里涌起的不是愤怒,反而是一种悲凉,一个时代把如此善良的知识分子,逼到了这种地步,这个时代除了下流、无耻,还能再有什么呢?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常常想到钱钟书先生,为什么那么幽默的学者,最后变成了一个极少说话的人,那样的耻辱不可能不在钱先生心中留下痕迹,但那样的耻辱,让钱先生如何说呢?钱先生去世后,遗嘱不开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只要二三亲友送送。
这里不光有钱先生的人格和境界,更有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评价。
我曾在一篇《谁的境界高?》的小文中做过一个推测,我以为这是钱先生不愿意再和共产党打交道的一种心理,对这个推测,我至今还认为可以成立。看了杨先生的文章,我更觉得钱先生的选择是有他的道理的。沈从文去世时,有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沈先生说:“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不是心灵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像钱先生、沈先生这样的读书人,会那样说话吗? 杨先生真是文章高手,她的这篇散文,我以为代表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最高水平,通篇文章除了冷峻的叙述,极少议论,偶有一些议论,也都是用非常平静的话语道出。
当钱家三人被逼到无法生存时,杨先生这样写: “钱瑷忽然说:‘咱们逃走吧’。
” “逃走?逃哪儿去?有路可逃,还逃吗?” 这样的文字是带血的,它让我们感受的不是个人的一时耻辱,而是一个时代的耻辱。
中国这五十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对文化的彻底毁灭。从四九年以后,把知识分子的尊严和体面全部打掉,在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让知识分子“脱裤子、割尾巴”,让无知的流氓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欺负得无法生存。
那时知识分子被逼得一说就是“我出身不好”,好象无业游民、地痞无赖都成了“好出身”,一个时代的普遍文化精神到了这种地步,知识分子还有什么活路呢?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多少年以后,有个右派的孩子对一位前辈说:“我出身不好,过去连考大学的资格都没有”。
这位前辈对他说:“你以后不要再说自己出身不好。你的出身很好!你家世代读书,薄有田产。这有什么不好?难道为匪为盗才是好出身?真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是可以说一说了,但被伤害过的心灵想要在短时间内苏醒过来,也是不太可能的。
杨先生这篇文章,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就是她没有把笔下那两个“革命男女”的真名实姓写出来,在杨先生,这是她的的恕道,我们可以理解。
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有知情的当年学部文学研究所的同人,把那两个“革命男女”的真名实姓告诉天下的人,让我们的后代也能知道,曾经有一个时代,人心坏到了那样的地步!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于太原 林非被钱钟书毒打真相 2009-09-13 原作者:肖凤 1973年12月7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
那一天,我的丈夫林非被一根大棒毒打,我自己的手指也被咬得鲜血淋漓。
那男人殴打时用力极很,手中的大棒当即断成两截。那时正值隆冬季节,林非身穿棉袄,挡住大棒的右臂还被打肿和打破,鲜血淤积,漆黑一片,让我深感恐惧而又心疼不止。 我连忙领着林非去医院看病,接诊的医生一边替他敷药包扎,一边惊叹打人者的心狠手辣,还开列了诊断的证明书,嘱咐我们好好防备打人者的继续行凶。
我搀扶着林非从医院回家,走进大门就瞧见公用的走廊里,堆积着许多霉烂的垃圾――吃剩的鸡骨头、长绿毛的橘子皮、碎布条、碎纸片,而打人和咬人的这对夫妇已经走掉了。
第二天,在林非单位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宣队,训斥林非怎么敢跟×××吵架,说是他那声势显赫的同学,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位高官将会来干预,威胁说要遣送林非去北大荒继续劳动锻炼,还派人上我教书的学校,找到了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要他来压制我。
这位领导是老革命,刚从“牛鬼蛇神”的队伍中解放出来,他在我教书的学校里工作了十几年,对我十分了解,一听就知道他们说的不是真话,就把他们打发走了。
此时,我们刚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回来不久,与离别了许久的年幼的儿子团聚,日夜都提心吊胆地害怕林非又被赶到更遥远的地方去,觉得他们的用心真是狠毒,却也只好找出家中所有积蓄的零钱,替林非买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好抵御那儿冰天雪地的严寒气候。
我整天忧愁地思忖着打人者的阴险,想用这么大的后台来压垮和摧毁我们。林非曾在五七干校患过一场大病,为了护理他的身体,并且减轻他精神上的压力,我打算跟他一起前往,可是儿子又太幼小,不能让稚嫩的生命随同我们去受罪,得保护他很好地长大成人,商量的结果是林非先走,我和儿子等一等再说。
幸亏那位当时的高官与我们素不相识,无仇无怨,所以并未听信一面之词,将林非置于死地。 我们好不容易地熬过了十年浩劫的岁月,更何况林非早在肃反运动中就被指责为立场右倾,反右运动中又被指责为犯有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曾在公开的会议上受到过批判,面对着这样坎坷的遭遇,他从“文革”开始后,就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遥的态度,却还被“造反派”不依不饶地在长篇大字报上称为“漏网右派”,常常处于胆战心惊的恐惧之中。
好不容易难熬的岁月终于过去了,有关的处分也都获得了公正的纠正。我们多么想安安静静地度日,高高兴兴地工作,可是咬人者不断地通过口头和文字的谣言,再三地进行人身攻击,现在又在一张报纸上大肆说谎,所以我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林非被打的真相公诸于众,相信善良和公正的读者朋友们会作出自己判断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8年春天,我怀孕了。我的婆母知道消息后,放下了由她照看的三个外孙,千里迢迢地从上海来到北京,准备迎接将要诞生的婴儿。
因为林非是她老人家最小和最疼爱的儿子,所以也十分慈爱地照顾着我。我们三人挤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能放下一张大床、一张小床和一个书桌之外,几乎就没有空地了。
我们躲在狭仄的空间里,却也享受着亲情的温馨。这一年冬天,我的儿子降生,小屋里又增添了一个新人,在拥挤的屋子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满屋子都拴上了晾尿布的绳子,上面悬挂着洗过的尿布,竟像是万国旗一样。
有一天,一位在林非单位里担任“革委会”主任的文学批评家,骑着自行车来我家看望,竟腾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 当时几代同堂住在一间屋子里,是众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我们还曾经跟另外三对夫妇同住在一个单元里面,和谐地相处得像朋友一般,有的邻居至今依旧相互来往。
这位文学批评家跟我们是同代人,心灵很容易相通,看着我们如此窘迫的处境,就动了恻隐之心。当时正值“文革”的“斗批改”阶段,整个单位都调整住房,因此也决定分配两间住房让我们搬家。
林非有一位后来大名鼎鼎却又流亡国外的同事,就是跟我们一起搬进这座楼房的。 我原来犹豫着不想搬迁到陌生的地方去,但是当时的处境实在太困难了,一是我的产假只有56天,又正值“清理阶级队伍”期间,绝不允许请假,不满两个月的儿子白天只能交给婆母照料,她老人家已经是将届古稀的高龄,真于心不忍,却又毫无办法,只能晚上下班后自己带着儿子,请老人家休息。
二是在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高潮中间,婆母的女婿也就是我们的姐夫,忽然被诬陷为“叛徒”,隔离审查,不许回家。其实他只是上海一座大型工厂的总工程师,老实巴交,什么问题也没有的。姐姐是小学校长,每天都早出晚归,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无人照管,她精神压力又很大,频频来信,述说困难,希望母亲早些南归。
三是居委会一个戴红袖章的老”红卫兵“,常常上我们原来的住处敲门,逼迫报了临时户口的婆母离开北京。
林非和我又必须天天上班,在这万般无奈的紧急关头,我的女友介绍了一位家住郊区的农村大嫂,与我们见面相识,说是如果聘请她帮助我们照顾小孩,我的婆母就得以回到上海慰藉她受难的女儿,这也许是解决困境的唯一办法。
这位善良的农民大嫂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绝对不能与我们夫妇共居一室,这个要求自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于是我不想搬迁也只得搬迁了。咬人者说我的婆母是为了分配住房才赶来充数的,这纯粹是造谣。我慈祥的婆母已经宁静地安息于九泉底下,不会再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伤害了。
在我们搬迁之后,开始时还相安无事,也曾稍稍地点头和说一两句寒暄的话语。咬人者是很讲究保养自己的,吃鸡蛋只吃丹青而不吃蛋黄,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黄和西瓜的外圈赏给我们,都被我严肃地拒绝了。
因为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来之食”。 她偶或露面的女婿,听说是北京某著名大学赫赫有名的“造反派”二把手,可是在当时风云突变的“文革”狂潮中,该所大学的“造反派”一把手忽然失宠于“中央文革”的“旗手”,他忍受不了岳母家中种种阴沉和发怒的颜色,竟悬挂在大学校园里一棵老树桠上自杀了。
我们本来是丝毫也不知晓的,自己正面临着种种压力,已经感到焦头烂额,身心交瘁,哪有闲暇去过问人家的事情,这还是听到住在旁边单元里一位红学大师的夫人匆匆说起的。
从此以后,咬人者和她的丈夫确实显得有些焦躁,当情绪分外低沉时,就跑进我们的住房,不由分说地抱走我心爱的儿子,放在他们屋子里当作开心取乐的玩具。
她根本无视我的人格,无视我作为母亲的存在。在她的心目中,别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几等,供她颐指气使地嘲讽和戏弄,包括我幼小的儿子在内,一概都是如此。
她这种霸道的态度,和对我儿子的人格的漠视,实在伤透了我的心,使我意气难平。而当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似乎也感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来她丈夫如此凶恶地猛击大棒,更是证明了这一点,看来被殴打和咬噬的命运,从开始时就笼罩于我们的头顶了。
我和林非在几年前奉命去干校时,怕儿子过于幼小,还不适宜去“经风雨,见世面”,只好把儿子托付给那位忠厚和质朴的农村大嫂,并且把两人每个月工资的极大部分都留给了她,她也尽心尽力地带领着我的儿子,跟我儿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可是我们几年来耗尽了原来就是极为低微的工资,经济情况显得十分拮据,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能力供养一个保姆了。
这位善良的农村大嫂非常理解我们经济上的困难,她也愿意另找一家经济收入比我们高的住户去帮工,于是她就和我们很友好地分手了。 我上班的学校,离家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每天赶公共汽车早出晚归,有时就把儿子带在身边。
那时候常常要跟学生一起去郊区农村“开门办学”,只好也带着年幼的儿子,和几个女同学睡在老乡家里的土炕上。又教书,又下地,又带着儿子,回家后真是感到劳累不堪。
那时候大家都还没有见过洗衣机,正好院子里有一位帮助人们洗衣服的农村大嫂,大家都称呼她为“余嫂”,我也请余嫂帮助洗衣服。1973年12月7日,适逢我刚从郊区农村返京,就请余嫂替我洗洗从农村带回来的衣服,因为几天之后还得带着儿子下乡,时间很紧张,让余嫂赶快洗起来。
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坚持要余嫂先给她洗,她的时间比我充裕得多了,为什么要如此着急,于是就争论起来了。在双方的情绪都很激动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双臂要抓住我的脸庞,我长得比她高,赶紧向后仰起头,并且伸出双手挡住她,没想到她竟用自己双手紧紧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飞快地塞进嘴里狠命咬了一口,当时抽出来就鲜血迸流。
她这个当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没有来得及躲闪。
中国有句老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连大字不识半个更画不成圆圈的阿Q都懂得这个道理,想不到她竟会如此行事。俗话说食指连心,我疼痛得大叫起来,林非从房间里奔了出来,想要解救我。
咬人者的丈夫也从他的房间里奔了出来,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棒,朝着林非就残忍地抡了下来,咬人者自己也承认,如果不是林非赶紧伸手挡住木棒,打中头颅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咬人者诬称我们将她提起又摔下了不知有多少次,请问我们哪里有这种大力士般的力气?造谣造得实在太荒唐了。
而且既然已经跌得晕头晕脑,怎么又能够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认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还要可恶地造谣,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
在此次冲突中,我们自始至终都是只动口没动手,咬人者和打人者则是又叫骂又动手。他们的表演和所作所为,让我看清了他们本来的面目。面对着她的造谣生事,我深深地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了。
这咬人者确实是造谣、攻击和欺负别人的能手,她曾散布过侮辱一位已故著名哲学家人格的流言,那位学者的女儿(一位著名女作家)就曾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驳。还有一位外国文学教授由于讲述了在她家里,听说过她丈夫攻击自己老师的一则谣言,她就威逼这位教授写出书面文字,保证从未听说过此事。
她还散布过自己丈夫的几位年轻同事,“拿我们的钱不还”,后来连她丈夫都否认这谣言说,“一切以我说的为准”,可见造谣的伎俩是如何的轻率与离奇。
为了澄清咬人者发表的造谣诬陷的文字,我只好放下手里正在撰写的稿子,将二十六年前的那件事实真相写出来公诸于众。我对自己写的文字负责到底。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咬人者再度造谣,作为被咬者的我,一定要再次澄清事实的真相。
林非单位里有几位充满正义感的同事,先后打来了电话,要我们必须反驳恶意的谣言。我庆幸自己终于生活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时代,这是新时期给予每个公民的权利,现在已经不是只许咬人者造谣,而不允许被咬者说明事实真相的时代了。
我尊敬所有善良和公正的同胞,但是对于一向造谣、攻击和迫害我们的咬人者,是愿意奉陪到底的。 刊载于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2期。















![钱瑗和杨伟成 钱瑗[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https://pic.bilezu.com/upload/3/42/3425c64764ac784a1ff129a6953b1ca4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