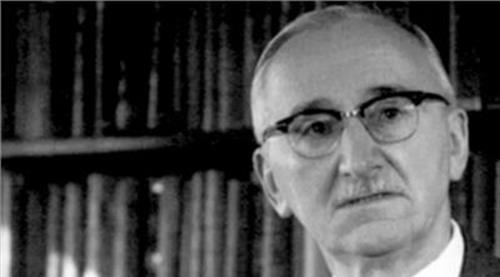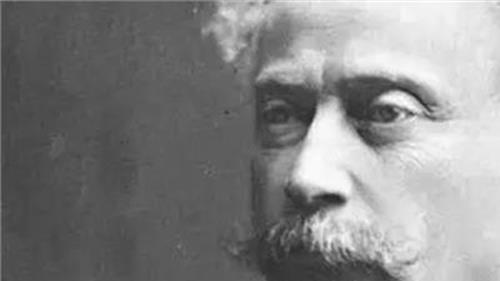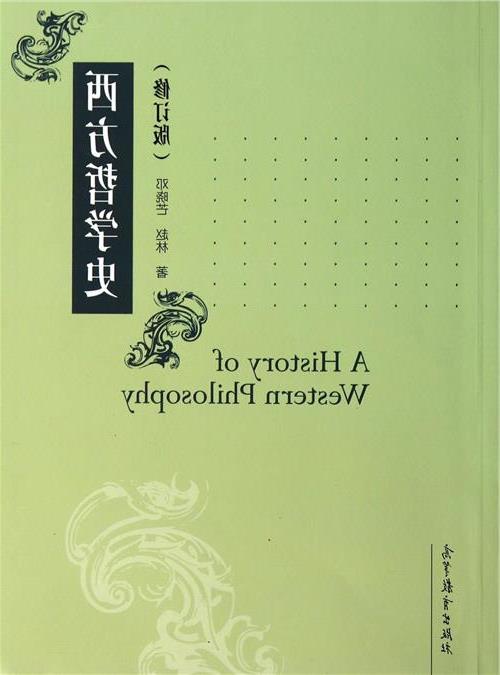邓晓芒去湖北大学 邓晓芒:我的大学在底层
长江商报消息 上周日,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在湖北省图书馆进行了一场讲座,题目是《我的大学》。颇为特别的是,邓晓芒并未读过大学本科,初中毕业以后,就下放到湖南农村,务农长达十年之久,回城之后,又干了五年的土工和搬运工。然而,正是这些经历触发了他的思考,使他对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产生了兴趣,使他不断阅读书籍,并最终走上哲学之路。

他说,我前三十年的经历跌宕起伏,在农村度过了十年,在城市又过了五年的搬运工、土工生活,我的大学和底层分不开。每当我在理论上陷入困惑时,我都要回到底层,回到现实去寻找力量,重塑我的信心,因为那就是我的母校。

讲座中,邓晓芒的一些经历和思考朴实厚重,或许会对读者有所启发,特将其讲座的部分内容刊发如下。本报记者 谢方 采写
两次理想主义献身的失败
后来想起来,那是一段可怕的时期,那个时候的堕落如果就那样下去……有很多人后来一直就这么下去了。后来经过了一段之后,我想不能这样下去,虽然我们的理想破灭了,但是人活在世上总应该活得像个人,总应该有些真正的值得追求的东西,不然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义。

所以到了1969年,我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历程,虽然很短,但是眼花缭乱,有人问我的经历,我想我就是那一段有些经历。这段生活经历主要就是两次理想主义的献身,都错了。一次是满怀热情、理想的上山下乡,破灭了;还有一个是“文革”,当年满腔热情,最后竟然挨斗挨批。
后来反思了。一个人可以错一次两次,但不能错第三次。我觉得自己有两大方面是很缺乏的:一是缺乏对中国国情真正的了解,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包括这些思想的发生,都是由于中国的国情,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导致的,觉得我们应该多多了解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农村,虽然我们下放到农村来了,但是我们还生活在知青圈子里头,虽然劳动跟他们在一起,但并没有真正体会他们的生活。
第二是觉得自己的理论水平太低,不能够自己独立分析任何问题,什么东西都看上面怎么宣传,自己没有头脑,一听到什么就脑子发热。所以我当时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那样的人:能够自己决定自己要干的事情,而且有理有据,有独立主见,能够有预见性,有判断力,能行动,那才算得上一个男子汉。
当时我们才二十出头,当时觉得自己应该成为那种人,向那个目标奋斗。
你有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启蒙了
我前三十年生活在动荡中,包括家庭遭难,被赶到湖南师范学院半山腰的两间房子,十来个人挤在两间房子,后来被下放。后三十年,很平静,就是老老实实地教书写东西做研究。
这是回顾我的历程。这个历程我叫做“我的大学”,它基本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曾经说过这样一个观点,“文革”当然是一个蒙昧的、狂热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自我启蒙的时代,所有的幻想都消灭后,你有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启蒙了。
我的大学也就是在底层,在这个大学里,我主要学了两件事,一个是学习人性,一个是学习认识自我,这两件事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在人间,我深深体会到在原则上,人与人都是相通的,只要你设身处地。而在体会别人之前,你是不可能认识自我的。我们经常说,“反身而诚”,没这么简单,你不体会别人,是认识不了自我的。
要认识别人必须在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体验生活,装模作样地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搞完了又回到办公室里写东西。必须是,你的命运与农民结合在一起。当时有知青感叹,再过二十年,我们就跟我们看到的老大爷一样,弯着腰驼着背在田里扯猪草,就是这样,我们的前途就是这样了,在农村干一辈子。这就是命运结合在一起,你就是一个农民,这样你才能真正了解农民。
也就是这种生活才能促使你体会别人。农民就是这样的,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年纪大的过完余生、不发生意外就不错了,这种生活之中,一切都是很平常的,没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这样一种期许,只有做好准备当一辈子农民,我当时已经做好了准备,在乡下盖个屋子,娶个老婆。有很多知青已经盖了屋,取了老婆,然后又离开了。
今天,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应该特别关注中国时代精神的新动向——打工一族城市化和农村翻天覆地的变革。以前梁启超等讲过,我们现在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主要是指中国的社会地位,三千年以来从来没这么低。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深入到根本的地方,也没条件,物质基础当年并没有变,只是在思想层面和文化层面有一些知识精英先知先觉,他们感到中国文化要改变了,有一个强大的西方文明,它是可以与中国文化相抗衡,甚至更强势。
而今天是从底子上彻底翻过来了,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国情就是自然经济已经没有了。五四时还有,虽然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但国民经济还是自然经济,所以五四青年闹过之后怎么办呢,回归传统。鲁迅写了篇文章《在酒楼上》,主人公吕纬甫曾经是个五四青年,热血积极。运动过后,回到乡下教《三字经》。鲁迅当年也是眼前一抹黑,完全看不到任何出路,为什么没有出路呢?因为经济基础没变,几个知识分子在那里嚷嚷,之后又回归老样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也是这个样子,“文革”也是这样的,“文革”自然经济仍然不变,还是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搞了一阵子又销声匿迹。
真正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到二十一世纪,才真正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经济全部翻过来了。现在到农村去种田,完全市场经济,种子、化肥到销路,全部都靠市场,推向市场,才能进行,哪里还有自然经济呢,几亿农民进城打工,壮劳力都走了,国家的新生力量全到了城市。还有一些残余,一些老人在某个角落里,还在搞自给自足。
为进城打工者提供思想支撑
我对这一新情况是高度关注的,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的所有研究,都是为打工仔打工妹们的思想做论证的。他们遇到极大的困惑,遇到了危机,他们从农村带来的乡土观念,自然经济的那套观念,到了城市完全不适用,没有道德底线,什么都干,只要能活。
可以理解,但是他们急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价值体系,来适应已经彻底改变了的中国的国情。我认为这一套新的观念就是西方的普适价值,西方古典哲学时代已经形成了的。西方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形成的一套普适价值观念,这套观念能够使他们转变观念,适应现代生活。当然这套东西在西方受到批判,这是因为西方已经现代化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应该引进,让广大老百姓有新的生活方式,有新的观念,能够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维权,要为他们提供理论工具,将来当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到某一步的,这些东西必然是有大用的时候,现在看来好像是天马行空,不切实际。但要做准备。这一次,不能再像前面两次一样,在表面上滑来滑去。
我提出,十八大以后,中国正面临第三次启蒙,这一次应该比前两次启蒙更深入,因为我们立足于现实,我们是眼看着现实生活出现了问题,提出一种救治之法,所以这次启蒙应该是落到实处的启蒙。不是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告诉老百姓,你们应该这么想应该那么想,而是从后面给老百姓支持,老百姓要打官司、维权,上面几句话就把他们打消了。老百姓如果有了理论上的支撑,就可以义正言辞地反驳回去。这是我所要做的工作。
我认为,为打工者呐喊,为底层呐喊,我做的事这样一种工作,它是符合中国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的。
邓晓芒,1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市人,1982年武大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毕业后长期在武汉大学任教。专攻德国哲学,亦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积极展开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2009年12月,改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